《先秦散文·墨子·非命下》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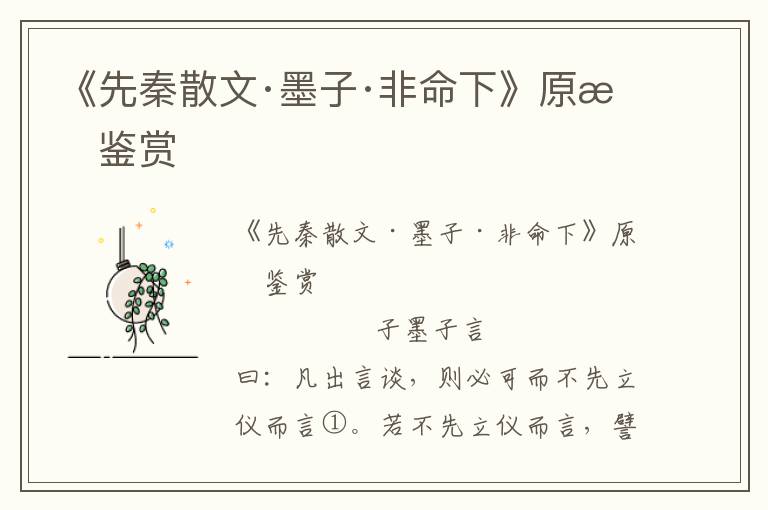
《先秦散文·墨子·非命下》原文鑒賞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①。若不先立儀而言,譬比猶運(yùn)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②,吾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眾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fā)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shí),曰必務(wù)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dāng)此之時(shí),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shí),曰,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yù)令問于天下③。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shù),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yù),遂得光譽(yù)令問于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
然今夫有“命”者,不識(shí)昔也三代之圣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④。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驅(qū)馳田獵畢弋⑤,內(nèi)湛于酒樂⑥,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⑦,吾聽治不強(qiáng),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成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cái)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饑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qiáng),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shù)之⑧,此皆疑眾遲樸⑨。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后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⑩:“允不著(11),惟天民不而葆(12)。既防兇心(13),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14): “我聞?dòng)邢娜顺C天命于下,帝式是增(15),用爽厥師(16)。”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昔者桀執(zhí)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發(fā)曰(17):“惡乎君子!天有顯德(18),其行甚章。為鑒不遠(yuǎn),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19)。惟我有周,受之大帝(20)。”昔紂執(zhí)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fā)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箭之篇以尚(21),皆無之,將何若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xué)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22),而利其唇吻也(23),中實(shí)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qiáng)必治,不強(qiáng)必亂;強(qiáng)必寧,不強(qiáng)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nèi)治官府,外斂關(guān)市山林澤染之利,以實(shí)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qiáng)必貴,不強(qiáng)必賤;強(qiáng)必榮,不強(qiáng)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nóng)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qiáng)乎耕稼樹藝,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qiáng)必富,不強(qiáng)必貧;強(qiáng)必飽,不強(qiáng)必饑,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qiáng)乎紡績織衽,多治麻統(tǒng)葛緒(24),捆布繡,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qiáng)必富,不強(qiáng)必貧;強(qiáng)必暖,不強(qiáng)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匱若信有命而致行之(25),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nóng)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nóng)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急乎紡績織紉(26),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cái),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27);下以持養(yǎng)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損其國家(28),傾覆其社稷者,此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shí)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當(dāng)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qiáng)非也, 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shù),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qiáng)非者,此也。
【注釋】 ①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應(yīng)為“不可不先立儀而言”。儀:儀法、規(guī)矩。 ②鈞:古代制陶器用的一個(gè)轉(zhuǎn)輪。朝夕:即日規(guī),是古代利用日影以測定時(shí)間的一種儀器。 ③令問:同令聞,好名聲。 ④而:能。 ⑤畢:古時(shí)用于捕獵的帶柄的網(wǎng)。弋:用系繩的箭發(fā)射。 ⑥湛:同沈,沈湎。 ⑦罷:同疲,軟弱。 ⑧術(shù):同述,即復(fù)述有命的說法。 ⑨遲樸:應(yīng)為“遇樸”。遇:通愚,即愚弄。 ⑩總德:上古逸書的篇名。 (11)允不著:果真對天不恭順。允:信、真:著;應(yīng)為“若”,順。 (12)而:能。葆:同保。 (13)防:通方,比同。 (14)仲虺之告:逸《書》篇名。仲虺:商湯的左相。告:同誥。 (15)式:通用,因而。增:同憎,厭惡。 (16)爽:當(dāng)是“喪”之誤。 (17)去發(fā):當(dāng)是“太子發(fā)”之誤(從孫星衍說)周武王名發(fā),原是文王的太子。這里當(dāng)指《太誓》的上篇,因以“太子發(fā)上祭于畢”發(fā)端而名之。 (18)有:同右,輔佐。 (19)祝降其喪:謂天絕紂王之命,降予喪亡以示懲罰。祝:斷。 (20)大帝:應(yīng)為“大商”,商朝。 (21)十簡:同什簡,指書籍。以尚:之上。 (22)惟舌:應(yīng)為“喉舌”(從王引之說)。 (23)唇吻:指嘴巴。(24)麻��:即麻絲(從王引之說)。(liu音劉)。 (25)蕢若:蕢同籍。藉若,即假若。 (26)急乎:應(yīng)為“怠乎”,懶于。 (27)不使:認(rèn)為不順從。使:當(dāng)作從。 (28)共損:共,當(dāng)是失之誤:失損,即喪失。
【今譯】 墨子說:凡是要發(fā)表言論,就不可以不先立下一個(gè)準(zhǔn)則,然后再講。如果不先立下一個(gè)準(zhǔn)則就講,就好比在制陶工的轉(zhuǎn)輪上安置日規(guī)一樣,我認(rèn)為雖然有測定時(shí)間的日規(guī),其結(jié)果必然無法靠它來測定出準(zhǔn)確的時(shí)間。因此判定言論是否合理,也有三條準(zhǔn)則。是哪三條準(zhǔn)則呢?第一是考求史實(shí),第二是審察本原,第三是付之于實(shí)際。何從考求史實(shí)呢?就是考求古代圣王的事跡。何從去審察本原呢?就是要審察人們耳目所見的實(shí)情。如何去付之于實(shí)際呢?就是具體運(yùn)用到對國家、百姓的治理方面,看它的實(shí)際效果。這就是判定言論是否合理的三條準(zhǔn)則。
所以從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當(dāng)他們治理天下的時(shí)候,就說:務(wù)必要推崇孝子,以勉勵(lì)人們都敬事雙親,務(wù)必要尊重賢良的人,以引導(dǎo)人們從善。因此施政教化,重在賞善罰惡。認(rèn)為只要這樣去做,天下的混亂局勢,就可以得到治理,國家的危險(xiǎn)情形,就可以安定。如果認(rèn)為這話不對,那么試看從前夏桀統(tǒng)治下的動(dòng)亂,到了商湯就治理好了;商紂王統(tǒng)治下的動(dòng)亂,到了周武王就治理好了。在那個(gè)時(shí)候,社會(huì)沒有改變,人民也沒有改變,只是統(tǒng)治者改變了政治措施,民風(fēng)也就隨之而改變。在桀、紂的統(tǒng)治下,天下就動(dòng)亂;在湯武的統(tǒng)治下,天下就太平。天下之所以太平,是由于湯、武的力量;天下之所以動(dòng)亂,是由于桀、紂的罪過。這樣看來,安危和治亂的關(guān)鍵,在于統(tǒng)治者的政治措施,哪里有什么“天命”的主宰呢?所以,從前的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當(dāng)他們施政于天下時(shí),都說:一定要使饑餓的人有飯吃,使受凍的人有衣穿,使勞苦的人得到休息,使動(dòng)亂的局勢得到治理,他們因此而能揚(yáng)美名于天下,怎么可以說這是“天命”呢?這確實(shí)是因?yàn)樗麄兊呐Π?現(xiàn)在的賢人君子,尊重賢才,又努力研究施政的經(jīng)驗(yàn),所以在上能得到王公大人的獎(jiǎng)賞,在下能得到眾百姓的稱贊,他們因此而能揚(yáng)美名于天下,這難道也是因?yàn)橛小疤烀眴?這也是因?yàn)樗麄兊呐Π?
但是,現(xiàn)在堅(jiān)持有“天命”的人,他們的觀點(diǎn)不知道是根據(jù)從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賢士呢?還是根據(jù)從前夏商周三代的暴君壞人?如果從他們的說法來看,就一定不是出于從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賢士,而一定是出自暴君壞人。現(xiàn)在,那些認(rèn)為有天命存在的人,就好比從前夏商周三代的暴君夏桀、商紂王、周幽王、周厲王,他們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能抑制自己對于聲色的貪求,而是隨心所欲,在外馳騁捕獵,在內(nèi)則沈湎于飲酒作樂,不顧他們國家百姓的政事,總做無益的事情,殘害百姓,違背民心,于是喪失了他們的國家。他們對此的說法,不是指出自己的軟弱無能。治理不力,而必定說自己命里注定要喪失國家。即使從前夏商周三代的一般無能的、不好的人,情況也是這樣。他們不能很好地事奉雙親和君長,厭惡恭敬謙虛,喜歡傲慢無禮,貪圖吃喝,懶于做事,以致衣食財(cái)用不足,所以有身受饑寒凍餓的憂患。他們對此的說法不是指出自己的軟弱無能,做事不勤勉,必定說:我命里注定了要受窮。從前夏商周三代不老實(shí)的人,也是這樣。
從前的暴君造出了命運(yùn)前定的說法,一般平民又將它進(jìn)一步演述,去欺騙那些忠厚老實(shí)的人。前代圣王早已擔(dān)心到這一點(diǎn),所以寫在竹簡和素帛上,刻在金石上,雕鏤在盤孟上,留傳給后代子孫。有人問:記載在什么書上呢?夏禹的《總德》上就曾說:“若真對天不恭順,那么天和人民都不能保護(hù)他。既然有了險(xiǎn)惡之心,天就會(huì)給予懲罰。不重視自己德行的修養(yǎng),天命怎么能保護(hù)他呢?”《仲虺之誥》上說。“我聽說夏桀矯稱受命于天,借此來統(tǒng)治黎民百姓,天帝于是憎惡他,使他喪失了民眾。”他把本來不存在的天命謊稱為是存在的,所以說是“矯稱天命”,如果“天命”確實(shí)存在,他說是有,哪里談得上是“矯稱天命”呢?從前夏桀堅(jiān)持“天命論”來實(shí)行他的統(tǒng)治,商湯就作了《仲虺之誥》來反對他,《太誓》上《太子發(fā)》篇曾說:“啊,君子!上天保佑有明德的人,這事非常明顯。可作為借鑒的并不遙遠(yuǎn),就在殷紂王的時(shí)代。他說人有‘天命’,認(rèn)為敬天沒有必要,祭祀沒有好處,貪暴沒有妨害。上帝因此不贊助他,使他的九州之地都喪失了;上帝認(rèn)為他不順從,因而斷絕了他的性命,降下喪亡的懲罰。而我們周朝,則繼承了商朝的大命。”從前商紂王堅(jiān)持“天命”論來實(shí)行他的統(tǒng)治,周武王就寫了《太誓》的《太子發(fā)》篇來反對他。你們何不向上考察商周虞夏的典籍,從這些書籍篇章上溯歷史,都沒有“天命”的說法,為什么會(huì)這樣呢?
墨子說:當(dāng)今天下的君子研究文學(xué)發(fā)表言論,不是為了使他們的喉舌辛勞,使他們的嘴巴變得快利,他們內(nèi)心確實(shí)是為了對國家、鄉(xiāng)里、人民在治政上有所貢獻(xiàn)。現(xiàn)在王公大人之所以一早就上朝,很晚才回家,以審理案件,治理政事,自始至終都這樣做,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yàn)樗麄冎溃k事勤勉,國家就一定治理得好;如不勤勉,就一定會(huì)混亂;努力辦事勤勉。國家就一定安定,如不勤勉,就一定危險(xiǎn)。所以不敢懈怠。現(xiàn)在卿大夫之所以竭盡全身力量,絞盡腦汁,對內(nèi)治理好官府,對外征收關(guān)市山林湖泊魚梁的稅利,用來充實(shí)倉廩府庫,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yàn)樗麄冎溃懔ψ鍪拢麄兊牡匚痪湍艿玫教嵘绮幻懔θプ觯麄兊牡匚痪蜁?huì)降低;努力的人一定顯榮,不努力的人就會(huì)聲譽(yù)掃地,所以不敢懈怠。現(xiàn)在農(nóng)夫之所以早出晚歸,努力耕田種植,多收糧食,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yàn)樗麄冎溃Ω骶湍軌蚋蛔悖慌Ω骶蜁?huì)窮困;努力耕作就能夠吃飽,不努力耕作就會(huì)挨餓,所以不敢懈怠。現(xiàn)在婦女之所以早起睡晚,努力紡紗織布,多制麻絲葛線,織出成捆的布帛,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yàn)樗齻冎溃徔椌湍芨蛔悖慌徔椌蜁?huì)窮困;努力紡織就能穿得暖,不努力紡織就會(huì)受凍,所以不敢懈怠。現(xiàn)在如果人們相信有“天命”而影響到自己的行動(dòng),那么,對于王公大人來說,就必然會(huì)荒于審理案件治理政事,卿大夫就必然會(huì)懶于治理官府,農(nóng)夫就必然會(huì)懶得耕田種植,婦女就必然會(huì)懶得紡紗織布了。而如果王公大人荒于審理案件、治理政事,卿大夫懶于治理官府,那我認(rèn)為天下一定會(huì)混亂了。如果農(nóng)夫懶得耕田種植,婦女懶得紡紗織布,那我認(rèn)為天下衣食財(cái)用就必然要缺乏了。如果照這種情況去治理天下,向上敬事天帝鬼神,天帝鬼神也認(rèn)為是不順從天意的;向下保養(yǎng)百姓,百姓也認(rèn)為對他們是不利的,就必然會(huì)離散出去,不能為主上所用。因而入城守衛(wèi)就不能鞏固,出城攻伐就不能取勝。從前夏商周三代的暴君,夏桀、商紂王、周幽王、周厲王之所以會(huì)喪失他們的國家,喪失他們的社稷,就是因?yàn)檫@個(gè)緣故。
因此墨子說:現(xiàn)在天下的士君子,如果心中果然想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那么對于堅(jiān)持“天命”論者的說法,就不可不堅(jiān)決加以批判,因?yàn)椤疤烀笔且恍┍╈宓木跛斐鰜淼模怯梢恍┢矫裱菔龀鰜淼模皇侨嗜藨?yīng)說的話。現(xiàn)在要行仁義的人,不可不審察并堅(jiān)決加以反對的,就是這個(gè)“天命”論。
【總案】 《非命》共有三篇,這是下篇。“非命”的觀點(diǎn),是墨子在與儒者辯論中針對儒家“天命”觀提出來的。墨子認(rèn)為,國家的興亡,取決于統(tǒng)治者的治理;人的貴賤貧富,決定于各自的努力。如果信守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思想,那作為統(tǒng)治者就必然會(huì)荒于政治,導(dǎo)致天下混亂;作為黎民百姓就必然會(huì)荒廢生產(chǎn),導(dǎo)致衣食不足。墨子這種“非命”意識(shí),有樸素的唯物因素。文章一開頭就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即判斷是非真?zhèn)危灰袣v史的依據(jù),二要憑人們所見所聞的實(shí)情,三要看付諸實(shí)行的效果。接著,作者就運(yùn)用“三表”法對“天命”問題加以鑒別和辯析。首先從歷史上看, “三代圣王”禹湯文武治理有方,故天下治,“三代暴王”桀紂幽厲施政無道,故天下亂,因而得出結(jié)論:安危治亂在于人為,哪有什么“天命”!作者援用“圣王”們的考察作驗(yàn)證,引用夏禹、商湯、周武王的書籍,說明古代典籍上都沒有“天命”的說法,證明“天命”之說的荒唐。作者又從現(xiàn)實(shí)的角度指出,如果信奉“天命論”,王公卿大夫以及勞動(dòng)者就會(huì)拋棄本業(yè),導(dǎo)致天下混亂、衣食匱乏的后果。“三表”法是一種以實(shí)踐為基礎(chǔ)的認(rèn)識(shí)論,以“三表”法來論析,使文章論據(jù)充實(shí),道理堂正,具有難以辯駁的邏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