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莉《生命之樹》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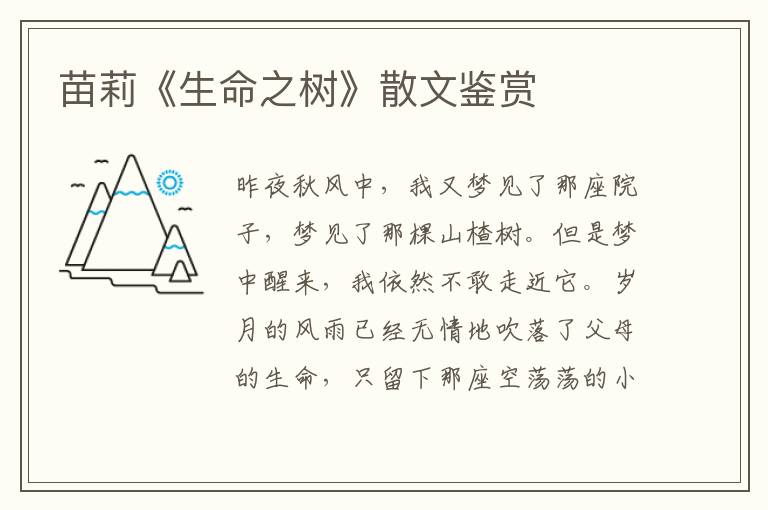
昨夜秋風中,我又夢見了那座院子,夢見了那棵山楂樹。但是夢中醒來,我依然不敢走近它。歲月的風雨已經無情地吹落了父母的生命,只留下那座空蕩蕩的小院,在孤單中度過每一個清晨和黃昏。小院承載著太多的歡樂,太多的悲傷,這些歡樂和悲傷,都像碑文一樣深深鐫刻在我的記憶里。父親離開那座小院走了將近3年,我竟然一篇有關他的文字還沒有寫成,而對父母那份刻骨的思念卻常常如鯁在喉。
2016年的深秋,天氣開始冷了,已是秋風蕭瑟落葉飄零。這一天的上午,父親身體不適住進了醫院,在踏進病房的那一刻,我還沒有意識到,我活著的父親、站立著的父親,僅僅在幾天之后,竟然就以橫著的姿態出了醫院的大門。橫著的他,沒有能夠再回到那座小院,而是直接去了另一個世界。
或許,父親自己是有感知的,在進入醫院的那一刻,父親的目光和我相遇,他用無奈的口氣說:“反正早晚都有這么一天。”我聽了之后,心就像被刀子扎了一下。
父親住院之后,我們從超市買了許多的日用品,是讓超市直接送貨到病房的。父親看著買來這么多東西,還開玩笑地說:“這是打算打持久戰嗎?”但是陪父親住院的日子太短了,短得讓兒女們猝不及防他就撒手人寰了,父親去了,去找我的母親了。忘不了在病房陪父親的那個夜晚,父女幾乎徹夜長談,話到動情之處,父親眼含熱淚聲音哽咽,他說:“我想你娘了,我太想她了,她已經離開我八年了。”那一刻,對母親的思念對父親生命的擔憂,就像潮水一樣擊打著我的心扉,這悲傷的潮水,幾乎讓我的身體從那張小小的木凳上跌落,我即刻站起身背對父親,望著窗外的萬家燈火,淚流滿面。
2008年的冬天,我的母親去世。母親離世的那一年,是我生命中灰暗的日子,昏昏沉沉中過了大半年的時光。一生與母親相濡以沫的父親情緒也沉到了冰點。與父親在一起的時候,更多的是相向而泣。想用那一場又一場痛徹心扉的哭泣,來彌補母親離世后我們心靈上的重創和生活上的空洞。
父親離世前的那一天上午,我的朋友去醫院看望他,父親還跟人家攀談,問朋友在哪個單位工作?做了一輩子干部的父親,一生都在關心別人的生活狀態,而且他非常健談。
送走朋友,為了讓父親開心一點,我說:“你看那么多朋友都來看您了。”
父親還詼諧地說:“人家主要是來看你的吧。”
然后,我離開病房去一個朋友的婚禮上,飯還沒吃,妹妹在電話中就催我趕緊回醫院。
僅僅過去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等我再回到病房的時候,父親已經陷入昏迷閉上了雙眼。淚眼迷離中,我在病床前呼喚著父親。我看見,昏迷中的父親,竟然努力地睜了一下眼睛,然而我卻沒有看到父親的眸子。我的父親,他再也看不到他寵愛的女兒,他認為為她爭了光的女兒了。從一開始住院他就向同室的病友說,“我女兒是作家,寫的散文可好了。”那種發自內心的驕傲和自豪溢于父親的言表。說得我不好意思了,就跟著父親的話后邊自嘲幾句。現在回想起來,能讓在世的父親以自己為榮以自己為傲,是一種多么大的幸福,對一輩子都在奮斗的父親來說是多么大的安慰。
父親是從齊魯大地上走出來的孩子,背井離鄉的第一站就是隨著奶奶去闖關東,在東北那片黑土地上,艱難中得以生存。當過放牛娃,那時候他連一雙完整的鞋都沒有,是主人家給做了一雙鞋,上山放牛的時候他舍不得穿,就把那雙鞋拴上繩子背在肩上。后來父親就穿著這雙鞋走進了學校。剛剛上學的父親已經十一歲了,上算術課總是把阿拉伯數字3反著寫。老師批評他,說他在黑板上用了多少粉筆還沒學會寫個3。父親生怕老師從此不讓他去學校,一臉真誠地對老師說:“粉筆用完了,明天就讓俺哥給買。”那一本正經認真的樣子把老師都逗笑了。
在學校短短幾年的學習,奠定了父親一生發展的基礎,從東北回到山東的父親,又從黃河岸邊來到河北闖蕩生活。他與我的母親,就像飄飛的兩棵蒲公英,在冀南平原這塊土地上相遇,是偶然也是命運的使然,他們是人間最好的相遇。我年輕的十八歲的父親,在歲月深處的那個春天,除了身上背著一個小小的包袱,別無長物,但是他高高瘦瘦英俊瀟灑一臉正氣,讓我的母親一見傾心。兩個人相知相愛組成家庭,這一生一世,經風沐雨,不離不棄,伉儷情深。
今生今世,真的感謝我的父母雙親,他們給了我們姊妹一個多么好的家、多么溫暖的家。兒女們在父母這兩棵大樹下,就像一群快樂的鳥一樣在成長。我記事的時候,父親就已經從縣醫院調到縣委辦公室工作。他有很好的文字功底,會寫文章,他有很高的情商,懂得如何溝通和處理一些事情,非常年輕就成為縣委辦公室主任。他在河北舉目無親,一切成長和進步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
那個時候的廣宗縣委會,在老縣城的某個街道上,小時候常常去父親的辦公室里玩,可惜的是父親辦公室里除了辦公桌文件柜之類并沒有什么好玩的。某一天,在父親的辦公室里極力想找到一點能吃的東西,父親從他的抽屜里給我拿出了幾個紅紅的顆粒,喜出望外的我以為是像葡萄干一樣好吃的東西,填進嘴里卻發現嚼起來澀澀的并不好吃,原來是中藥房里配藥用的枸杞子。父親看見我失望的樣子,止不住笑起來。
忘不了在突然而至的狂風大雨中,我行走在泥濘的街道上,瘦小的身體幾乎要被風卷去,我在滿是嘩嘩流過的雨水中,掙扎著恐懼著絕望著。忽然間,我看見風雨中,我年輕的父親,正撐著一把紅色的油布雨傘向我走來,他穿著黑色的長筒雨鞋,走過來的他喊著我的名字,一把拉住了我在風雨中飄搖的手。那雙手堅定而有力,讓我懸著的那顆心回到了自己的胸膛。此去經年,這一幕是永遠也抹不去的記憶,永遠生長在我思念的土壤上。
縣委會是個非常大的院子,每一排瓦房的連接處都建有一個通道,是個圓拱形的過道,那里的穿堂風很涼爽。大院里種滿了高高的泡桐樹,父親說,種上這些樹,是為了紀念和學習人民的好干部、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這些泡桐樹長得很好,每一年的夏天都會竄上一截子,父親說,看看這些泡桐樹多像你,個子一年年在長高。
在那座古樸的縣委大院里,后院是人們很少去的地方,那里長了好多的花草,夏天的時候非常茂盛,我喜歡在那充滿神秘的后院里尋找自己的夢。那時我的夢中,離我最近的城市是邢臺市,遠一些的有北京、廣州、長沙,我在心里描繪著這些城市的面貌,渴望著有一天,走出那座縣城,走向外面的世界。
那一天午后,我徜徉在綠植豐茂的后院,做著一些迷茫的夢。或許是累了,睡意悄悄襲來,不知不覺中眼皮一合,我就沉沉睡去。天都黑下來了,大人們都下班了,父親和母親并沒有看到我的身影,他們急得四處尋找,怎么喊我的名字,都沒有人答應。最后在百般焦急的尋找中,發現我竟然正靜臥花草叢做著美夢。
當我被父親喚醒的時候,恍惚間,竟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卻感受到了父親那喜出望外的心情。當發現自己剛剛就睡著在花草之中,對夜晚的恐懼即刻彌漫而來。在漆黑的夜色中離開縣委會的大院,父親拉著我的手回家,問我餓了吧冷了吧?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我看見了家里的那盞燈,那一束燈火透出的光亮,閃耀著家的溫暖父母的恩情。
有一年,我年輕的父親病了,那個時候,他是縣革委分管農業的領導。他去魏村指揮為老百姓打井,那口井打得很艱難,打井的設備非常原始,在選定的井址區域內打了好幾次,才打出了一口井,把父親急得累得,在村子里就發起高燒。我記得父親是被一輛牛拉著的大板車送回縣城的,我和母親出了縣城北關去接父親,父親很瘦,臉色憔悴,躺在板車的一床舊被子上,見了我和母親無聲地笑了笑,用手撫摸了一下我的頭。趕大車的把式頭上包著白色的毛巾,他看見我的母親,幾乎掉下眼淚,說都是為了給俺村打井累得,可不打這口井,俺村就要吃不上水了。從那時開始,父親就在用他一生的行動,不斷詮釋著一個黨的好干部的形象。
1976年,河北省委往保定地區選派干部,四十歲的父親又一次背起行裝,告別家人到保定地區徐水縣委工作,后來又調到曲陽縣委。父親在曲陽縣工作期間,我和母親、妹妹一起搬家前往。十年之后的1986年,父親及我們全家又從保定調回邢臺工作。
父親新任職的邢臺地區外貿局,為他改建了一座平房小院作為住房。搬進這座新建的小院,父母興奮地忙著添置東西,在院子里植樹種花。那棵山楂樹,從太行山腳下移過來的時候很小,父親一锨土一桶水,親手栽下。每年的春天,那棵山楂樹都會開滿花,那潔白的花,一朵朵散發著淡淡的清香,讓整個院子都閃爍著夢幻般的光芒。父親好像特別在意那棵山楂樹,山楂樹開花了,父親會打電話,讓我們姊妹們去賞花。山楂樹下,父母為我們燒好開水,泡上茶,一壺濃濃的親情,在歲月的凝煉中愈加醇香。秋天的時候,那棵山楂樹枝頭滿是紅紅的果,越長越大枝繁葉茂的山楂樹,粗壯的樹干早已經超過了房頂。每到山楂成熟的時候,父親的電話又打來了:“山楂熟了,該摘了。”摘山楂的時候,歡聲笑語充滿了這座小院。
大哥和妹妹喜歡到房頂上去摘,摘了一筐又一筐,那些長在高枝上的山楂果就要用桿子打,我和父親在院子里撐開一個大大的布單子,接著那些身居高處的果子,免得果子落在水泥地面上摔壞,無法保存。父親的心很細,早早地預備好打山楂的桿子,收山楂的筐子,一家人享受著收獲的喜悅和人間的至愛親情。之后,父親會把這些擺在院子里的山楂分成若干份,送給鄰居,送給朋友,送給兒女各自拿回家。 但是,這一年的秋天,又到了山楂收獲的季節,卻遲遲沒有接到父親催促收山楂的消息,直到11月份第一場雪都下了,父親說:“今年的山楂果沒長好,很小,本想讓它們在樹上多長些日子,看來再也長不大了,就收了吧。”
那一年,我們家院子里的山楂長得個頭很小,吃上去又酸,與往年的又紅又大又甜的山楂,仿佛不是一個樹上長的,讓忙活了半天最愛吃山楂的大哥有些失望。
誰能料想,這一樹山楂果,竟是這棵樹最后的奉獻了。第二年春天,我去父親的小院,看見那棵山楂樹似乎有些異樣,雖然長出了樹葉,卻是又小又弱,我以為它太干旱了,缺少水分了,就把樹坑深挖了一下澆上了水。幾天后我又來看望父親,卻發現那棵山楂樹上,剛剛冒出來的嫩芽和花朵,居然都回芽了,枯萎了,從樹上飄落下來了。不知為什么,我仿佛能聽見那些花和葉子墜落的聲音,它們一片一片疊加在一起,在這個花草葳蕤的世界里,顯得多么無奈和蒼涼。
仔細看看那粗壯的山楂樹干,樹皮在一點點皸裂。這棵山楂樹要死了,瞬間我的內心就掠過一絲不祥的預感。抑制不住的那份不安和傷心,讓我躲在一個房間里掩面而泣,妹妹顯然是刻意的勸我說,你也太多愁善感了,一棵樹死了你就這么傷感呀。
我擦干眼淚,極力驅趕著內心的不祥預感,希望這一切擔憂和不安真是我太過敏感。但是我的僥幸心理落空了,那棵山楂樹春天的時候死了,我父親的生命之樹就在深秋凋落了。這一切,是巧合還是冥冥中天地萬物的感應?那棵在院子生長了三十年的山楂樹,它是用盡了最后的力氣,為我們奉獻了最后一季的果實,而懵懂不知的我們,居然還嫌它小嫌它酸。
父親在他住院后的第六天突發心梗,陷入昏迷。那一夜,醫院的樓道里病房里睡滿了我家的兒女和孫輩們。黑夜過去了,天亮了,父親的呼吸卻越來越微弱。我的目光,緊緊地盯著那臺監測儀,我的手,緊緊地攥著父親的手。父親的手掌很厚實,依然是綿軟的,帶有溫度的,我握著他的手,他已經基本上沒有回應。這雙陪伴我們長大、在風雨中拉著我們保護著我們的手,已經不再有力。醫生讓癱坐在父親病床前的我起來,讓我不要太悲傷。我知道,只要撒開這雙手,就會像當年失去母親一樣,在頃刻間,我就會與父親天上地下,陰陽兩隔。
最后的時刻,不可抗拒地到來了,被我緊緊握著的父親的手,還是給了我一個回應,他用力地攥了一下我的手指。我突然想到那棵山楂樹上最后的一季果實,多么像父親拼盡全身的力氣給我的回應。山楂樹,那棵陪伴了他三十余年的山楂樹,像有靈性一樣陪著父親走了。
前不久,我去山東,車從冀南平原駛入了齊魯大地聊城,那是我父親的故鄉,是生他養他的土地,是他生命出發的地方。看著車窗外萬木蔥籠、百花盛開,想起我已經歸于泥土的父親,想起他曾經是在這塊土地上奔跑的孩子,不禁百感交集,淚如雨下,這塊被他生前心心所念的故土,父親是回不去了。
父親在世的時候,想去看看山西洪桐的大槐樹,我們總是擔心父親在了卻某種心愿,之后會有什么不測,就沒帶他去。然而這一切努力,又如何能夠留住父親漸漸離去的腳步,就像我拼命地給那棵山楂樹澆水,依然無法挽留住它的生命一樣。面對著站立在人生終點的石碑,誰能逃脫走向它的腳步,一切多像夢一場。
這一刻,我坐在北戴河的沙灘上,看云卷云舒。橙色的夕陽在云層中一點點墜落,晚霞把潔白的云彩照耀得無比璀璨,那云層后邊透過來的光束無比明亮。
遠處有兩只相伴飛過的鳥兒,我看不清它們的模樣,只看見它們在輕快地飛翔,自由自在,儀態萬方。我想到已經安葬在一起的父親母親,這對人世間的恩愛夫妻,在那個未知的世界里,他們一定會是這樣比翼雙飛的模樣,那是我父親臨終的心愿,他去找我母親了,他們是在人間相伴五十多個春秋的好伴侶。
多少關于父親母親的記憶,是永遠刻在我們心里的。這記憶就像少時那盞燈,閃閃爍爍的燈火閃耀親情的光芒,照耀著我們走向更深的遠方,直到人生的終點。
黃昏了,起風了,漲潮了,那白色的大浪洶涌而來又瞬間退去,多像在這永恒的時光里,來過又消失了的生命。當我想起這些文字的時候,心中不斷閃念著父親的臉龐,他偉岸的身軀,好像就站立在不遠的海灘上,多想走過去喚一聲父親,多想再看看父親的模樣,這些都是虛空的幻想……一切幻想都會換來更大的失落和悲傷,父親已經去了我們永遠找不到的地方。
一篇文字,怎能盡述父親一生的風雨歲月?幾許深情,怎能道盡父母雙親的似海之恩?就讓那棵跟隨著父親一路離去的山楂樹,在我們看不到的世界里,春天依然開一樹繁花,秋天如期結一樹碩果,陪伴我的父母雙親琴瑟和鳴歲月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