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戲劇《關(guān)漢卿·感天動(dòng)地竇娥冤》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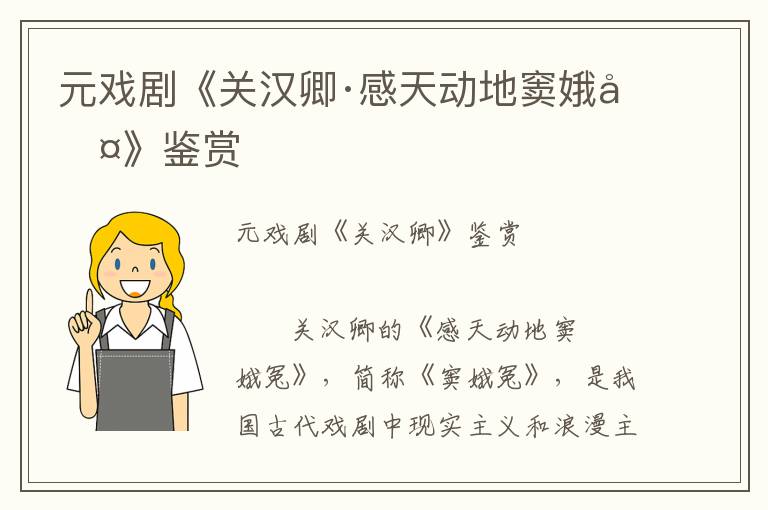
元戲劇《關(guān)漢卿》鑒賞
關(guān)漢卿的《感天動(dòng)地竇娥冤》,簡(jiǎn)稱《竇娥冤》,是我國(guó)古代戲劇中現(xiàn)實(shí)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jié)合的著名悲劇,是關(guān)漢卿的代表作。
我國(guó)民間曾經(jīng)流傳過(guò)一個(gè)“東海孝婦” 的故事,說(shuō)的是于定國(guó)的父親于公在東海郡當(dāng)獄吏時(shí),郡里一個(gè)對(duì)婆婆很孝順的寡婦,被郡守冤判了死刑,于公為之力爭(zhēng)而不得。后來(lái)東海郡大旱三年; 新郡守聽(tīng)了于公的話,洗刷了孝婦罪名,上天立即下了大雨。這個(gè)故事在劉向的《說(shuō)苑》和干寶的《搜神記》中都有記載。
關(guān)漢卿的《竇娥冤》主要根據(jù)現(xiàn)實(shí)生活創(chuàng)作而成,其中明顯地受到 “東海孝婦”故事的啟發(fā)。劇中的主人公是年輕的寡婦竇娥。作者在劇中一開(kāi)始,便先寫了竇娥童年時(shí)的一系列不幸遭遇。
竇娥三歲喪母; 長(zhǎng)到七歲,父親竇天章因欠高利貸者蔡婆的錢無(wú)力償還,上京趕考又無(wú)路費(fèi),只好把她送給蔡婆抵債,從此當(dāng)了童養(yǎng)媳。她十七歲成婚,不久丈夫早死,年輕守寡,與蔡婆相依為命。蔡婆一次向賽盧醫(yī)討債,賽盧醫(yī)騙她到郊外,想害死她,卻被張?bào)H兒父子無(wú)意沖散。張?bào)H兒趁機(jī)威逼她婆媳兩個(gè)嫁給他父子二人,竇娥不肯,張?bào)H兒想用藥毒死蔡婆威脅竇娥成親。誰(shuí)知張?bào)H兒父親誤食身死,張?bào)H兒誣陷竇娥藥死父親,逼竇娥相從。竇娥不但不從,反和他同去見(jiàn)官。楚州太守桃杌是個(gè)只認(rèn)錢財(cái)?shù)幕韫伲迅]娥打得皮開(kāi)肉綻,又要打蔡婆。竇娥為使婆母免遭酷刑,只得屈招,被判死刑。在赴刑場(chǎng)途中,竇娥滿腔悲憤,立下三樁誓愿:血濺白練,六月降雪,三年亢旱。竇娥屈死之后,三樁誓愿,件件實(shí)現(xiàn)。竇娥的鬼魂后來(lái)把狀告到了考中進(jìn)士以肅政廉訪使身份來(lái)到楚州地面的父親竇天章那里,奇冤才得昭雪。從“東海孝婦”的傳說(shuō)到《竇娥冤》,已經(jīng)帶上了元代社會(huì)的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生活色彩。
(一)
《竇娥冤》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竇娥這個(gè)從安于命運(yùn)到與命運(yùn)抗?fàn)幍男愿駝倧?qiáng)的婦女形象。竇娥小小年紀(jì)便經(jīng)歷了人生的重大不幸。她開(kāi)始把自己的不幸遭遇歸之于“命運(yùn)” ,“莫不是八字兒該載著一世憂” ,“莫不是前世里燒香不到頭,今也波生招禍尤” ,認(rèn)為是前生燒了斷頭香所致。由于她父親是個(gè)窮書生,自小對(duì)她進(jìn)行三從四德教育,再加上蔡家并非“沒(méi)有飯吃,沒(méi)有衣穿,又不是少錢欠債、被人催逼不過(guò)” ,就是說(shuō)婆媳倆命雖苦生活并不十分苦,因此使竇娥產(chǎn)生了“我將這婆侍養(yǎng),我將這服孝守,我言詞須應(yīng)口” 的思想,目的并不僅僅是消極度過(guò)今生,而是為了“把來(lái)世修” 。這里雖然有安于命運(yùn)、相信天命的成分,但也不乏用今生的善行換取來(lái)生好命的爭(zhēng)強(qiáng)好勝之心,這正是一種外柔內(nèi)剛的性格表現(xiàn)。當(dāng)張?bào)H兒父子闖進(jìn)他的生活圈子里來(lái)的時(shí)候,她的內(nèi)里剛強(qiáng)開(kāi)始外露,她對(duì)引狼入室的婆母埋怨、不滿,認(rèn)為她“舊恩愛(ài)一筆勾,新夫妻兩意投,枉把人笑破口” ,“婆婆也,你豈不知羞! ”對(duì)于厚顏無(wú)恥的張?bào)H兒,她“不禮”,斷喝“兀那廝,靠后!”張?bào)H兒調(diào)戲她,她毫不客氣地推倒他。張?bào)H兒藥殺親父,想以此要挾她,和她“私休” ,她就是不向張?bào)H兒低頭,寧愿“官休” 。她為的是爭(zhēng)個(gè)貞潔之名,爭(zhēng)個(gè)做人的最起碼的自主權(quán)利。她開(kāi)始滿以為官府會(huì)公正執(zhí)法,在事實(shí)面前她的幻想破滅了。臨死前她才看清了官府的面目,覺(jué)悟到“這都是官吏們無(wú)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 ,悲憤已極,發(fā)下三樁誓愿: “不是我竇娥罰下這等無(wú)頭愿,委實(shí)的冤情不淺; 若沒(méi)些靈圣與世人傳,也不見(jiàn)得湛湛青天。”在這里,竇娥爭(zhēng)的是清白,表的是無(wú)辜。她的怨忿已不僅僅是針對(duì)某個(gè)丑惡的個(gè)人,而是代表封建階級(jí)利益的濫官污吏們。竇娥死后,雖然三樁誓愿樁樁實(shí)現(xiàn),但她并沒(méi)有因此而對(duì)惡勢(shì)力罷休。她的鬼魂“每日哭啼啼守住望鄉(xiāng)臺(tái),急煎煎把仇人等待” ; 她不僅請(qǐng)求父親為自己除去“莫須有” 的罪名,而且高呼“衙門自古朝南開(kāi),就中無(wú)個(gè)不冤哉! ”這已經(jīng)不是為自己一人鳴冤叫屈,也不是向一個(gè)桃杌太守或一大批“官吏們”挑戰(zhàn),而是向整個(gè)封建統(tǒng)治階級(jí)的官僚機(jī)構(gòu)發(fā)出挑戰(zhàn),為所有受冤百姓嗚屈。
作者在表現(xiàn)竇娥剛強(qiáng)性格的同時(shí),又寫了她性格的另一面: 善良。她的善良最初表現(xiàn)為對(duì)婆母的孝順。她發(fā)現(xiàn)婆母從外討債回來(lái)兩淚漣漣,“連忙迎接慌問(wèn)候” ; 蔡婆末經(jīng)她同意引來(lái)張?bào)H兒父子,她對(duì)此深為不滿。但蔡婆病了想吃羊肚湯,她還是給做了。張?bào)H兒說(shuō)少鹽,她連忙取了鹽來(lái),對(duì)蔡婆可謂孝順之至了。桃杌太守公堂上聽(tīng)信張?bào)H兒一面之詞對(duì)她嚴(yán)刑拷打,但她寧死也不招認(rèn)所謂“藥殺公公” 的“罪名” 。而當(dāng)桃杌太守要打她婆母時(shí),為使婆母免遭酷刑折磨,她竟毫不猶豫地招認(rèn)了張?bào)H兒強(qiáng)加給她的罪名,被下入死囚牢里。在這里,竇娥的善良已不僅是一般的孝順,而是寧愿自己蒙冤也不讓別人受屈的自我犧牲精神。劊子手要押她赴刑場(chǎng)時(shí),她怕婆母看見(jiàn)了傷心,要求劊子手押她走后街,這又表現(xiàn)了竇娥高尚的被壓迫者與被侮辱者之間的同情心。最后竇娥冤屈已伸,其亡魂還叮嚀父親: “我婆婆年紀(jì)高大,無(wú)人侍養(yǎng),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兒盡養(yǎng)生送死之禮,我便九泉下,可也瞑目。”她的鬼魂不僅為自己報(bào)仇,還要她父親一類清官保護(hù)蔡婆這種無(wú)依無(wú)靠的孤苦老人,“收養(yǎng)我奶奶,憐她無(wú)婦無(wú)兒,誰(shuí)管顧年衰邁” ,只要婆婆平安終生,自己死而無(wú)怨。
不可否認(rèn),關(guān)漢卿筆下的竇娥,是個(gè)封建道德的虔誠(chéng)信奉者。她的信條一是貞節(jié),二是孝道。她反對(duì)蔡婆改嫁張?bào)H兒父親,主要是不同意“張郎婦去做李郎妻” ; 她自己不嫁張?bào)H兒,所持理由也是“一馬不備二鞍,好女不嫁二男” 。最后她的鬼魂向父親竇天章請(qǐng)求申冤時(shí)那樣理直氣壯,也是因?yàn)樗哉J(rèn)為一生對(duì)封建道德毫無(wú)越軌行為,因此問(wèn)心無(wú)愧。但是,關(guān)漢卿并不是要通過(guò)竇娥宣揚(yáng)封建道德。竇娥受到流氓張?bào)H兒的無(wú)理威逼,為了與之斗爭(zhēng),在沒(méi)有其他思想武器的情況下,只有用她父親自小教給她的三從四德等封建道德準(zhǔn)則作為防身自衛(wèi)的武器。在當(dāng)時(shí)條件下,唯一可能和竇娥站在一起的就是蔡婆,蔡婆的動(dòng)搖軟弱和引狼入室使竇娥處于孤立無(wú)援的境地。她為了說(shuō)服蔡婆和自己始終站在一起對(duì)付張?bào)H兒父子的威逼,只有用 “一馬不備二鞍,好女不嫁二男” 的封建道德標(biāo)準(zhǔn)最有說(shuō)服力,因?yàn)楦]娥的守節(jié)不是為了別人、就是為了蔡婆的親生兒子。她若用其他大道理批判蔡婆的軟弱,一方面違背她本人的身份和性格,另方面對(duì)失節(jié)改嫁的蔡婆也缺乏針對(duì)性。其結(jié)果不但說(shuō)服不了蔡婆,還可能使蔡婆完全倒向張?bào)H兒一邊。再說(shuō)竇娥開(kāi)始對(duì)官府抱有幻想,要和張?bào)H兒官休而不私休,見(jiàn)了太守耐心地細(xì)致地?cái)⑹鍪虑榈慕?jīng)過(guò),認(rèn)為“大人你明如鏡,清如水,照妾身肝膽虛實(shí)” ,即使被打得“肉都飛,血淋漓” ,對(duì)官府也無(wú)一句怨恨之詞,幻想著“官吏們還復(fù)勘” 。她滿以為自己虔誠(chéng)地遵守封建道德,理所當(dāng)然地應(yīng)該受到提倡這種道德的官府的保護(hù)。誰(shuí)知“本一點(diǎn)孝順的心懷,倒做了惹禍的胚胎” ,在統(tǒng)治階級(jí)的屠刀下掉了腦袋,這豈不是天大的冤枉! 竇娥沉冤最后之所以能得到昭雪,也是因?yàn)樗赣H竇天章得知她生前“不肯辱祖上” ,沒(méi)有違背竇家“三輩無(wú)犯法之男,五世無(wú)再婚之女” 的傳統(tǒng);而謀害她的張?bào)H兒卻是“亂綱常合當(dāng)敗” 。如果她對(duì)封建道德稍有逾越,那將會(huì)被竇天章“牒發(fā)城隍祠內(nèi)”,“永世不得人身,罰在陰山永為餓鬼” 。那樣的結(jié)局,將在觀眾心中造成多大的遺憾啊!
可見(jiàn),作者對(duì)竇娥身上的封建道德的描寫,是從維護(hù)被侮辱被壓迫者的利益出發(fā)的,是把封建道德作為下層人民在黑暗混亂的社會(huì)條件下的防身武器來(lái)對(duì)待的。同時(shí),作者這樣作也是服從于作品所表現(xiàn)的特定主題的。《竇娥冤》的主題是揭露元代社會(huì)法制黑暗,綱紀(jì)松弛,官吏昏庸,流氓橫行,無(wú)辜受害; 同時(shí)歌頌下層人民的斗爭(zhēng)和反抗。堅(jiān)守封建道德不愿屈就流氓的竇娥屈死封建統(tǒng)治者屠刀之下; 跌踏封建道德、不惜陷害好人的張?bào)H兒得到封建統(tǒng)治者的保護(hù),逍遙法外; 并不胡作非為但卻愿意改嫁的蔡婆,命運(yùn)不如張?bào)H兒,卻勝過(guò)屈死的竇娥!作者就是這樣通過(guò)竇娥、蔡婆、張?bào)H兒三個(gè)對(duì)封建道德持不同態(tài)度的人物的不同命運(yùn)的描寫,反映元代社會(huì)已經(jīng)到了何種不可救藥的程度。
作者對(duì)竇娥身上的封建道德的描寫,還服務(wù)于表現(xiàn)竇娥其人的性格特點(diǎn)。竇娥的善良、剛強(qiáng)這兩重性格是與封建道德聯(lián)系在一起的。她的善良建立在孝順的思想基礎(chǔ)上。她的與惡勢(shì)力斗爭(zhēng)則以貞節(jié)為指導(dǎo)思想。她若順從婆母屈就張?bào)H兒,那只符合孝而違背了節(jié)。她若因不屈就張?bào)H兒而拋棄婆母,那只符合節(jié)而違背了孝。只有既不拋開(kāi)婆母又不屈就張?bào)H兒,才是既孝又節(jié)。但就是這樣一個(gè)既孝且節(jié)的婦女,卻以“藥殺公公”的罪名被判死刑,這樣的冤枉,怎能不感天動(dòng)地!
(二)
《竇娥冤》的突出成就,還表現(xiàn)在對(duì)竇娥悲劇根源的揭示上。劇幕乍起,便見(jiàn)以高利貸為生的蔡婆等待窮書生竇天章送女抵債。這種開(kāi)頭一下子就把人引入濃郁的悲劇氣氛之中,使人對(duì)悲劇主角竇娥產(chǎn)生深切的同情。但高利貸并不是造成竇娥悲劇的根源。高利貸只是把蔡家和竇家聯(lián)系起來(lái),組成蔡婆和竇娥的矛盾統(tǒng)一體; 又把蔡婆和賽盧醫(yī)、并進(jìn)一步把張?bào)H兒父子和蔡婆竇娥聯(lián)系起來(lái),使張?bào)H兒和竇娥發(fā)生沖突。當(dāng)然高利貸在劇中出現(xiàn),客觀上反映了元代一種新的剝削方式的出現(xiàn)。但這種剝削方式既受不到封建法律的保護(hù),更不會(huì)構(gòu)成竇娥悲劇的根源。相反,這種以討債為生的“小康生活”,倒使竇娥產(chǎn)生了“把來(lái)世修”的思想。作者沒(méi)有把高利貸剝削作為竇娥悲劇根源,還表現(xiàn)在對(duì)高利貸者蔡婆同情多于批判,寫她受欺多于欺人,把她基本上寫成了一個(gè)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此人雖有原夫留下的一點(diǎn)錢財(cái)可作高利貸資本,但因無(wú)政治背景,無(wú)依無(wú)靠,無(wú)新的生財(cái)之道,無(wú)欺人之心,所以大有坐吃山空之勢(shì)。財(cái)產(chǎn)雖未吃空,卻被冤案牽連。作者對(duì)她有批判,但決不是因?yàn)樗帕烁呃J,而是因?yàn)樗那优场⒂奚埔灾烈侨胧业目杀愿瘛?br>
那么,《竇娥冤》所揭示的竇娥悲劇的主要社會(huì)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是元代豺狼當(dāng)?shù)馈⒘髅M行的社會(huì)環(huán)境。賣藥看病本來(lái)是急人危難,救死扶傷,但“死的醫(yī)不活,活的醫(yī)死了”的賽盧醫(yī),自己承認(rèn)“不知醫(yī)死多少人,何嘗怕人告發(fā),關(guān)了一日店門”,于是膽量由小變大,以至還不起所欠蔡婆之債,竟然欺騙她到郊外荒村企圖用繩勒死了之; 張?bào)H兒向他討要毒藥,先還不肯。當(dāng)張?bào)H兒以他害人未遂為由要拉他見(jiàn)官時(shí),他竟給張?bào)H兒合了毒藥,事后卷包而逃,無(wú)人過(guò)問(wèn)。賣藥看病的不是好人,救了蔡婆之命的張?bào)H兒也是個(gè)披著人皮的豺狼。這個(gè)自稱“美婦人我見(jiàn)過(guò)萬(wàn)千向外”的流氓,搭救蔡婆并非出于路見(jiàn)不平、拔刀相助的正義感,不過(guò)是偶然相遇,順路人情。當(dāng)賽盧醫(yī)被嚇跑,他便提出要蔡婆寡婦寡媳二人招他父子為夫的無(wú)理要求。蔡婆稍微答應(yīng)得慢了點(diǎn),他便露出了禽獸的猙獰面目,重新拿起賽盧醫(yī)的繩索,欲干賽盧醫(yī)所未干成之事。到了蔡家后,因竇娥堅(jiān)決拒婚,他便起了殺人之心,想藥死蔡婆以逼竇娥屈就于他,不意藥死了親父。如果竇娥答應(yīng)招他為夫,他完全可能葬父息事。偏偏竇娥是個(gè)不屈的女性,和他去見(jiàn)太守,張?bào)H兒當(dāng)堂誣竇娥“藥死公公” ,結(jié)果構(gòu)成竇娥死罪。就是這樣一個(gè)一再作惡的流氓地痞,竟然無(wú)人管他!再看“為民父母”的太守桃杌吧。對(duì)于這個(gè)人物,作者著墨不多,只有兩處,但已把他表現(xiàn)得維妙維肖。一處是科渾亮相動(dòng)作,一見(jiàn)告狀的便下跪,還說(shuō)了一句“凡來(lái)告狀的都是我的衣食父母”,這就表明他是一個(gè)貪官;又一處是相信張?bào)H兒一面之詞,說(shuō)什么“人是賤蟲,不打不招”,說(shuō)明他是一個(gè)視民為草介的溢官。竇娥之案本無(wú)難斷之處,但他卻一逼二打,構(gòu)成冤獄。什么法律,什么正義,全不放在他眼里。
竇娥就生活在這樣一個(gè)從官到民、壞人充斥的黑暗社會(huì)之中。她一個(gè)孤弱寡婦,縱然不被張?bào)H兒、桃杌逼死,也仍然是壞人共目之弱肉。
竇娥悲劇的第二個(gè)根源是,在元代那種混亂局面下,無(wú)辜善良之輩總是犧牲品,既無(wú)法主宰自己的命運(yùn),在邪惡勢(shì)力襲來(lái)時(shí)也難以防身自衛(wèi),竇娥正是這樣一個(gè)典型。竇天章欠蔡婆高利貸還不起,上京趕考奔自己的前程,卻無(wú)路資,于是就把三歲離母、眼下只有七歲的小女端云(竇娥幼時(shí)之名)送到蔡婆家當(dāng)童養(yǎng)媳抵債,雖然也說(shuō)了句“這個(gè)那里是做媳婦,分明是賣與她一般”,但無(wú)論是“送女”還是“賣女”,實(shí)質(zhì)都是一樣。作者主觀上是要表現(xiàn)竇天章送女抵債比賽盧醫(yī)殺人賴賬好得多,而且女兒為父親的前途作出犧牲這件事本身,從封建道德的觀點(diǎn)看來(lái)也無(wú)可非議,但問(wèn)題的實(shí)質(zhì)正在這里: 竇天章從蔡婆那里得到的是進(jìn)京趕考的路資,賣掉的卻是只有七歲的親生小女。竇娥就這樣成了封建家長(zhǎng)的犧牲品。
蔡婆為了報(bào)答張?bào)H兒父子救命之恩,未征得竇娥同意,便引張家父子來(lái)到門前,準(zhǔn)備答應(yīng)張?bào)H兒的無(wú)理要求。竇娥雖然執(zhí)意不從,但蔡婆既已引狼入室,竇娥縱然插上翅膀,也難逃出張?bào)H兒魔掌。竇娥實(shí)際上充當(dāng)了蔡婆和張?bào)H兒私相交易的犧牲品。
張?bào)H兒逼婚不成,欲毒死蔡婆結(jié)果毒死親父,作為執(zhí)行封建法律的桃杌太守,本應(yīng)查明真相,使兇手張?bào)H兒正法。但他卻貪財(cái)昏聵,聽(tīng)信張?bào)H兒的誣告,把無(wú)辜的竇娥判成“藥殺公公”的死罪就刑,竇娥又成了官吏流氓互相庇護(hù)狼狽為奸的犧牲品。
造成竇娥悲劇的第三個(gè)根源,是封建的上層建筑衰朽不堪。竇娥這個(gè)忠實(shí)遵守封建道德安分守己的年輕女子,遭遇如此悲慘,卻得不到社會(huì)輿論的同情;擾亂封建秩序、敗壞封建道德的賽盧醫(yī)、張?bào)H兒也沒(méi)有受到社會(huì)輿論的譴責(zé),更沒(méi)有受到封建法律的制裁。封建的社會(huì)輿論和法律,連自己所應(yīng)維護(hù)的東西尚且維護(hù)不了,那里還能為無(wú)辜受害者伸張正義!作者把蔡婆寫成剝削者,但沒(méi)有把她寫成壞人,她和竇娥同樣是受害者,這至少說(shuō)明兩個(gè)問(wèn)題: 一是象蔡婆這種靠正常的封建剝削過(guò)日月的人,尚且難免飛來(lái)之禍,一般窮苦百姓可想而知;二是說(shuō)明在那禽獸遍野的社會(huì)里,竇娥能和蔡婆這種剝削者和平共處已感到極大的滿足,但仍不免陷入冤死的厄運(yùn),足見(jiàn)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黑暗和混亂到多么不堪的程度!
(三)
《竇娥冤》藝術(shù)上突出的成就,就是浪漫主義手法的運(yùn)用,這就是三樁誓愿和鬼魂復(fù)仇。
竇娥臨刑前發(fā)出三樁誓愿后,陰云四起,冷風(fēng)盤旋,雪花飄飛,出現(xiàn)了一種陰暗凄慘的景象,加重了悲劇氣氛。三樁誓愿是竇娥含冤而死以前極度悲憤和壓抑而又死不甘心的反抗情緒的產(chǎn)物。張?bào)H兒未闖進(jìn)她的生活圈子里來(lái)以前,她歸命于天,“滿腹閑愁,數(shù)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自怨“命苦”,欲修“來(lái)世”。等到蒙冤赴刑,便“將天地也生埋怨”,“天也,你錯(cuò)勘賢愚枉做天”。就刑之前,她唱道: “天公不可欺,人心不可違”,“皇天也肯隨人愿”,深信“浮云為我陰,悲風(fēng)為我旋” ,三樁誓愿實(shí)現(xiàn)之時(shí),“那其間才把你個(gè)屈死的冤魂這竇娥顯”。劇情發(fā)展到此,竇娥由“信天”、“怨天”發(fā)展到“勝天” ,以至主宰天地鬼神,達(dá)到感天動(dòng)地的程度。
《冤娥冤》第四折鬼魂的出現(xiàn),雖然有點(diǎn)消極,但卻沒(méi)有給人造成恐怖之感。相反,魂旦在舞臺(tái)上游來(lái)游去,更激發(fā)了觀眾對(duì)萬(wàn)惡的封建制度的憎恨,加深了對(duì)屈死的竇娥的同情和懷念。魂旦出場(chǎng)復(fù)仇,又使觀眾從中受到鼓舞。魂旦出面作證,則進(jìn)一步暴露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腐朽到何種地步,以至人間無(wú)主持正義之人,只有依靠鬼魂出來(lái)作證了。鬼魂雖在現(xiàn)實(shí)中子虛烏有,但魂旦作為一個(gè)復(fù)仇形象出現(xiàn),卻表現(xiàn)了被迫害而死的竇娥不除人間邪惡決不罷休的斗爭(zhēng)精神。因此,鬼魂的出現(xiàn)乃是用消極的形式表現(xiàn)了積極的思想,即為被迫害者復(fù)仇的思想。
在《竇娥冤》中,現(xiàn)實(shí)主義是和浪漫主義結(jié)合在一起的。相對(duì)而論,“楔子”和前兩折主要用的是現(xiàn)實(shí)主義手法,后兩折則主要用的是浪漫主義手法。總觀全劇,并無(wú)割裂之感,而是融為一體的。前面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描寫著重在揭示竇娥悲劇的根源及其性格變化。后面的浪漫主義則是進(jìn)一步表現(xiàn)竇娥性格的發(fā)展及正義的伸張,真理的力量。沒(méi)有前面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描寫,后面的浪漫主義精神便成了無(wú)源之水,無(wú)本之木; 而如果沒(méi)有后面的浪漫主義描寫,前面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便成了“爬行式”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在觀眾面前展現(xiàn)的只能是一片黑暗,而無(wú)求生的希望。那樣既違背生活真實(shí),也不符合觀眾的愿望。
《竇娥冤》在結(jié)構(gòu)上也有自己的特點(diǎn): 在楔子里,作者寫了竇娥幼年的悲慘遭遇,接著第一折,作者略去中間十多年的生活不寫,一下子開(kāi)始了二十歲的竇娥喪夫之后的生活描寫,既給觀眾留下想象的余地,又使戲劇情節(jié)簡(jiǎn)練集中。作者在開(kāi)頭的楔子和前兩折把主要事件都集中交待清楚之后,騰出筆來(lái),濃墨重潑,寫了驚心動(dòng)魄的第三折,專門表現(xiàn)竇娥對(duì)不平世界的強(qiáng)烈控訴,戲曲波瀾驟起,人物性格也升華到一個(gè)新的高度。這種別出心裁的結(jié)構(gòu)安排,既很好地達(dá)到了表現(xiàn)人物性格的目的,又能自始至終抓住觀眾的心。
(四)
《竇娥冤》第三折是全劇的高潮,重點(diǎn)寫了竇娥性格的飛躍,表現(xiàn)竇娥對(duì)黑暗現(xiàn)實(shí)的控訴和悲憤已極咒天罵地的感情。竇娥本來(lái)是相信命運(yùn)的,爭(zhēng)取來(lái)世能有好報(bào)。但她人在家中守,禍從天上降;她本來(lái)是相信官府的,而官府卻是非顛倒,判她死刑。所以她一上場(chǎng)就在[正宮端正好]這支曲子里唱道:
沒(méi)來(lái)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憲,叫聲屈動(dòng)地感天、頃刻間游魂先赴森羅殿,怎不將天地也生埋怨。
“不提防”說(shuō)明她對(duì)自己安分隨時(shí)卻被判死刑料想不到; “沒(méi)來(lái)由”表現(xiàn)她對(duì)官府草菅人命的大膽指責(zé)。這是她在刀擱在脖子上時(shí)對(duì)“王法” 、“刑憲” 的強(qiáng)烈不滿。什么 “王法” 、“刑憲” ,卻原來(lái)都是官吏們用來(lái)對(duì)付善良無(wú)辜的老百姓的。竇娥再也不能象過(guò)去那樣聽(tīng)天由命了,罪惡的統(tǒng)治階級(jí)連她“修來(lái)世” 的權(quán)利也剝奪了。今生尚且遭此不白之冤,怎圖來(lái)世得到好報(bào)! 她叫屈了,她埋怨天地了。而這完全是被逼出來(lái)的,是她臨死前在內(nèi)心極度壓抑、極度悲憤的情況下,用悲亢慘痛的語(yǔ)言所表達(dá)出來(lái)的反抗怨恨之情。接著,她又在著名的[滾繡球]這支曲子里唱道:
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quán)。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 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gè)怕硬欺軟,卻原來(lái)也這般順?biāo)拼5匾玻悴环趾么鹾螢榈?天也,你錯(cuò)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
這又是她身處絕望之中,負(fù)屈含冤,欲訴無(wú)人,求救無(wú)援,叫天不應(yīng),叫地不答,轉(zhuǎn)而對(duì)天地鬼神發(fā)出的斥責(zé)和怒罵。用今天的話來(lái)說(shuō)就是: “天上有日月每天照著人間,地下有鬼神掌握著人的生死大權(quán)。天和地,本應(yīng)該把是非屈直從公判斷,為什么混淆了好人和壞蛋! 善良的人得到的報(bào)應(yīng)是貧窮和短命,作惡的人卻得到富貴又壽比南山! 天地呵,你原來(lái)也是這等的善惡顛倒,怕硬欺軟,順?biāo)拼? 地呵,你既然不分好壞,就沒(méi)有資格叫人相信你。天呵,你把賢愚錯(cuò)判,也就算不得公正的蒼天 !”
天是宇宙的主宰,據(jù)說(shuō)連皇帝都是受命于天的。可竇娥在這里卻咬牙切齒,咒天罵地,皇帝官府就更不放在眼中了。她罵得好,罵得有理。她這個(gè)一心一意守節(jié)行孝的年輕女子,不但得不到一個(gè)“孝婦”的“美名”,反而被強(qiáng)加了一個(gè)“藥殺公公”的不孝惡名被處死; 作惡多端的張?bào)H兒,不但得不到應(yīng)有的制裁,反而落了個(gè)孝子之名而活在人間,這是多么的不公正!竇娥這詛咒的語(yǔ)言,激憤的感情,如江河怒吼,狂風(fēng)呼嘯,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shù)力量。
劇情至此,竇娥的反抗性格已經(jīng)發(fā)展到一個(gè)新的高度。但是作者并沒(méi)有就此罷筆,接著又寫了竇娥性格的另一面,寫了她被綁赴刑場(chǎng),和蔡婆哭別的令人心碎的慘痛場(chǎng)景。
竇娥被劊子手前拖后擁,推向法場(chǎng),她在中途唱道:
則被這枷紐的我左側(cè)右偏,人擁的我前合后偃。我竇娥向哥哥行有句言。
這個(gè)在官府“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的酷刑折磨下不口軟不討?zhàn)埖膭偭遗裕F(xiàn)在竟然稱劊子手為“哥哥”。但她并不是要乞求哀憐,而是為了叫劊子手讓她走后街不走前街,為的是怕在前街遇見(jiàn)婆婆。她的這一要求就連劊子手也感到詫異: “你的性命也顧不得,怕她見(jiàn)怎的?”善良而孝順的竇娥回答道: “俺婆婆若見(jiàn)我披枷帶鎖赴法場(chǎng)餐刀去呵,(唱)枉將他氣殺也么哥,枉將他氣殺也么哥”。原來(lái)她自己快死了,卻還在設(shè)身處地地為婆母著想。竇娥孤身只影,無(wú)親無(wú)故,爹爹音信全無(wú),對(duì)于婆母這個(gè)她死前唯一的可見(jiàn)之人,有多少訣別之言要說(shuō)呵! 多么希望和她再見(jiàn)最后一面呵! 可是為了不讓婆母因感情受刺激而發(fā)生意外,卻向劊子手提出迥避婆母的要求。她這種對(duì)婆母欲見(jiàn)而又不愿見(jiàn)的矛盾心情,表現(xiàn)了一個(gè)受迫害女子的美好心靈。看到這里,觀眾怎能不對(duì)迫害她的黑暗現(xiàn)實(shí)深惡而痛絕之!
竇娥為了不使婆母遭受酷刑而致死,招認(rèn)了“藥殺公公”的罪名。可是她對(duì)婆母卻無(wú)一點(diǎn)埋怨的意思,因?yàn)樗啦唐烹m然糊涂愚善,也和自己一樣是弱者,她詛咒使他們共處于弱者地位的罪惡社會(huì)。臨死前她也沒(méi)有對(duì)蔡婆提出更多的要求,只是請(qǐng)她“遇著冬時(shí)年節(jié),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漿水吃,瀽半碗兒與我吃; 燒不了的紙錢,與竇娥燒一陌兒,則是看你死的孩兒面上。”她唱道:
念竇娥葫蘆提當(dāng)罪愆,念竇娥身首不完全,念竇娥從前以往干家緣;婆婆也,你只看竇娥少爺無(wú)娘面。
念竇娥伏侍婆婆這幾年,遇時(shí)節(jié)將碗涼漿奠; 你去那受刑法尸骸上烈些紙錢,只當(dāng)把你亡化的孩兒薦。
婆婆也,再也不要啼啼哭哭,煩煩惱惱,怨氣沖天。這都是我做竇娥的沒(méi)時(shí)沒(méi)運(yùn),不明不暗,負(fù)屈銜冤。
乞求的口氣,凄慘的語(yǔ)調(diào),連聲幾個(gè)“念竇娥” ,如泣如訴,聲淚俱下,讀來(lái)令人肝腸欲斷!
竇娥對(duì)天地鬼神痛罵不絕,對(duì)風(fēng)燭殘年的年邁婆母,感情如此哀婉動(dòng)人; 她為使婆母免于苦刑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而對(duì)婆母的要求卻是這樣的微不足道! 分明自己已經(jīng)對(duì)命運(yùn)發(fā)生不滿,對(duì)自己銜冤痛感不平,但為了不使婆母因?yàn)檫^(guò)度悲哀而煩惱傷身,卻用了“都是我竇娥沒(méi)時(shí)沒(méi)運(yùn),不明不暗,負(fù)屈銜冤”的字眼,這是多么崇高的人格! 這是多么善良的女性! 殺害她的罪惡現(xiàn)實(shí),怎能不在人們的咒罵聲中崩潰!
已經(jīng)在臨刑之前認(rèn)識(shí)到“這都是官吏們無(wú)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的竇娥,當(dāng)然不會(huì)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 她堅(jiān)信真理和正義在自己一邊,即使死了也要控訴官府衙門的黑暗,也要向世人表明自己是個(gè)無(wú)辜的受害者! 就在臨刑之前,她發(fā)出了驚天動(dòng)地的三樁誓愿,
不是我竇娥罰下這等無(wú)頭愿,委實(shí)的冤情不淺,若沒(méi)些靈圣與世人傳,也不見(jiàn)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熱血紅塵灑,都只在八尺旗槍素?zé)拺摇5人南吕锝郧埔?jiàn),這
就是咱萇弘化碧,望帝啼鵑。
你道是署氣喧,不是那下雪天,豈不聞飛霜六月因鄒衍。若果有一腔怨氣噴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滾似綿,免的我尸骸現(xiàn)。要什么素車白馬,斷送出古陌荒阡。
“你道是天公不可欺,人心不可憐,不知皇天也肯從人愿,如今輪到你山陽(yáng)縣,這都是官吏們無(wú)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
她從咒罵天地到支配天地。她也真的把和統(tǒng)治階級(jí)一氣的天地改變?yōu)楸粔浩日咧涞奶斓? 這是作家的理想,也是人民的愿望。這些百年難遇的奇事,終于出現(xiàn)了。但觀眾并不感到突然,因?yàn)檫@是竇娥悲憤感情和反抗怒火的必然流露,非如此不足以表現(xiàn)竇娥屈死之冤,非如此不足以解觀眾心頭之恨,非如此不足以驚天地動(dòng)鬼神,非如此不足以顯示黑暗現(xiàn)實(shí)的極端不合理!
這一浪漫主義手法的運(yùn)用,使全劇頓然增色,使人物大放異彩,使觀眾感憤不已,收到了杰出的藝術(shù)效果。
在關(guān)漢卿的許多戲曲中,矛盾的解決和暴逆的鏟除,幾乎都是依靠清官的判案,和《竇》劇中的竇天章一樣,《蝴蝶夢(mèng)》中的包拯,《望江亭》中的李秉忠,《救風(fēng)塵》中的李公弼等等,都是由清官出來(lái)伸張正義懲除邪惡的。可見(jiàn),清官治世是關(guān)漢卿的一貫思想。作者希望有一大批清官“把金牌勢(shì)劍從頭擺,將濫官污吏都?xì)模c天子分憂,萬(wàn)民除害”。在元代,科舉取士被廢除七八十年之久,選擇官吏不以科考為途徑。關(guān)漢卿在《竇娥冤》中寫竇天章以科考為官,并非無(wú)的放矢,而是針對(duì)當(dāng)時(shí)廢除科考而導(dǎo)致濫官污吏遍野的黑暗現(xiàn)實(shí)。當(dāng)然科舉取士弊病甚多,但在關(guān)漢卿看來(lái),卻要比以等級(jí)取士好得多。事實(shí)上,封建制度不廢除,無(wú)論那種取士制度都是不利于下層人民,而只利于封建統(tǒng)治階級(jí)的。在這一點(diǎn)上,表現(xiàn)了關(guān)漢卿的局限。但清官出來(lái)為民伸冤也還有表現(xiàn)人民愿望的積極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