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戲劇《馬致遠·破幽夢孤雁漢宮秋》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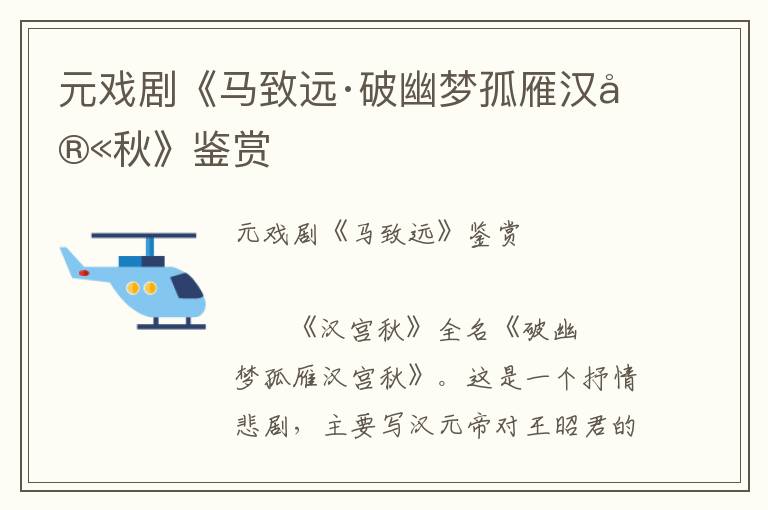
元戲劇《馬致遠》鑒賞
《漢宮秋》全名《破幽夢孤雁漢宮秋》。這是一個抒情悲劇,主要寫漢元帝對王昭君的深情厚愛,對權奸的無比憎惡,以及對忠臣良將的思念。全劇用愛國還是誤國,抑或叛國,這一思想紅線貫穿始終,構成為一個統一的藝術整體。
(一)
《西京雜記》中有一段關于照君出塞和番的記載,說的是漢元帝時宮妃極多,不能一一相見,元帝便命畫工把宮妃畫成圖形,按照圖形召幸。許多宮妃用五萬甚至十萬金錢賄賂畫工,只有王墻不背賄賂,所以見不了君王之面。匈奴王派人向元帝求婚,元帝按圖形所畫,決定派王嬙(昭君)前往匈奴和親。到了動身的那一天,元帝召見昭君,發現昭君容貌為后宮第一,而且善于應對,舉止婉雅,元帝后悔不該派昭君和番。但要對匈奴國講信用,便不再更換他人。事后元帝追查此事,把畫工全趕出宮去了,沒收畫工家資巨萬。畫工中有一人便是杜陵的毛延壽。
《漢宮秋》作者對昭君出塞的故事進行了根本改造,用古人酒杯,澆自己塊壘,表現馬致遠自己的愛國民族情緒。當然作者既用元帝之名,也并非完全“出師無名”。首先,元帝時漢朝已歷十代,中央集權削弱,權奸勢重,險象叢生;漢元帝一反漢宣帝“霸” 、“王”之道雜用,而采用儒學治國。這些情況在劇中都有反映。其次,《漢宮秋》中愛國主義主題和歷史上昭君和番所起的愛國進步作用相一致。歷史上昭君出塞的原因是匈奴呼韓邪單于主動歸漢稱婿,漢元帝以后宮王嬙賜之,結束了自武帝以來與匈奴的連年戰爭,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當然沒有漢武帝時的正義的反侵略戰爭,也就不會有呼韓邪單于的主動歸漢;而呼韓邪單于主動歸漢稱婿,也不必象關羽對待孫權求婿那樣斷然拒絕,招致漢匈不睦。經過楚漢相爭,人民需要安定,漢初與匈奴和親符合人民愿望; 但匈奴卻視漢為軟弱可欺,越來越驕橫,不斷侵擾邊郡,劫掠人口畜產,在漢朝國力強盛時,漢武帝向匈奴發動反侵略戰爭也符合人民過和平安定生活的愿望。經過對匈奴連年戰爭,一方面鞏固了邊界安寧,使匈奴力量衰竭,不敢犯漢。另方面漢朝的人力財力消耗也非常大,武帝晚年便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文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引眾遷徙于陰山附近,歸漢稱婿,元帝恢復和親,以王嬙嫁單于,使北部疆土六、七十年“邊城晏閉,牛馬布野” ,這也是符合人民愿望的好事。
《漢宮秋》作者借昭君出塞一事反映的是愛國的民族感情。但卻對具體歷史事實做了重大改造,主要表現在: 把歷史上元帝沒有寵幸昭君改為元帝寵幸昭君; 把歷史上昭君嫁給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死后又嫁給了他的兒子,改為昭君在匈漢邊界投江殉漢;把歷史上毛延壽貪賄作弊,改為不僅貪賄作弊,并且投敵叛漢,最后又被匈奴押送漢朝就刑。所有這些改動,強化了作品的愛國民族感情。
(二)
《漢宮秋》中的王昭君是個有愛國民族氣節的女性。她生在成都秭歸縣莊農王長者家,家道貧窮,但是“光彩照人,十分艷麗;真乃天下絕色”。她不僅容貌出眾,而且很有節操。毛延壽為元帝刷選宮女,看中了她,向她索取賄賂,她“全然不肯”。毛延壽老羞成怒,將她影圖點破,使她不曾得見文帝,退居永巷(禁錮宮女的宮中長巷) 。她在夜深孤悶之時,彈琵琶消遣,被元帝發現,受到寵幸。匈奴呼韓邪單于為了索求昭君,以武力威逼漢元帝。在這國勢危急之際,王昭君雖然對元帝萬分留戀,但“怕江山有失”,便挺身而出,對元帝說: “妾既蒙陛下厚恩,當效一死,以報陛下。妾情愿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寥寥數語,表明昭君不是一個一般有正義感的女性,而是能夠割舍個人情腸,顧全民族大局的光輝女性。番王封她胡閼氏,坐正宮,拔兵北行。至黑龍江,昭君望南奠酒,說道: “漢朝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尚待來生也”,毅然跳入江中,以身殉漢。比起元帝周圍那些只顧個人安逸不顧民族安危的文臣武將,王昭君簡直是聳入云端的高山。作者對這個人物的正面描寫不多,但卻能抓住她關鍵時刻的表現,再加上元帝對她容貌的傾倒以及分離后對她的思念,使這個外表美心靈更美的女性,給人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和昭君相對立,作者又寫了幾個丑惡的奸臣形象。一個是中大夫毛延壽。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 “為人雕心雁爪(心狠手辣) ,做事欺大壓小; 全憑陷佞奸貪,一生受用不了。……因我百般巧詐,一味諂諛,哄的皇帝老頭兒十分歡喜,言聽計從。朝里朝外,那一個不敬我,那一個不怕我。我又學的一個法兒,只是教皇帝少見儒臣,多昵女色,我這寵幸,才得牢固”; “大塊黃金任意撾,血海王條全不怕;生前只要有錢財,死后那管人唾罵”。他的特點:一是奸,慫恿皇帝遣官遍行天下,選擇宮女,“不分王候宰相軍民人家,但要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者,容貌端正,盡選將來,以充后宮” ; 二是貪,利用選妃之機,搜刮民財,所得金銀不少; 三是狠,王嬙不愿行賄,他本待不選,但想到 “狠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不要倒好了也” ,于是“只把美人圖點上些破綻,到京師,必定發入冷宮,教他受苦一世” ; 四是叛,元帝發現他畫圖作弊,要加刑斬首,他便拿著昭君圖影投奔匈奴。正在尋找借口準備侵漢的的匈奴呼韓邪單于,便趁此機會以取昭君為名,用武力威脅漢朝。和一切叛賊都沒有好下場一樣,毛延壽最后被呼韓邪單于解送漢朝處治,落了個可恥的結局。
劇中的尚書令五鹿充宗 (權臣石顯黨羽)是另一種類型奸臣形象。匈奴以索取王昭君為名,用武力威脅漢朝,五鹿充宗不敢對匈奴道半個不字,勸元帝獻出昭君,“以息刀兵” ,“咱這里兵甲不利,又無猛將與他相持,倘或疏失,如之奈何! 望陛下割恩與他,以救一國之生靈” ,“陛下割恩斷愛,以社稷為念,早早發送娘娘去吧”。這個奸臣,平時“臥重裀,食列鼎,乘肥馬,衣輕襲” ,只知道“山呼萬歲,舞蹈揚塵,道那聲誠惶誠恐” 。一旦邊關有事,“似箭穿著雁口” ,一聲也不敢咳嗽,既無拒敵之策,又無抗戰之勇,只能迎合番幫,欺侮昭君軟善。最無恥的是五鹿充宗等文武百官妻妾成群,荒淫無度,絲毫也沒有意識到 “女人禍水” 、“女人誤國” ,現在他們卻以此為據催促元帝獻出昭君,說什么: “他外國說陛下寵昵王嬙,朝綱盡廢,壞了國家。若不與他,興兵吊伐。臣想紂王只為寵妲己,國破身亡,是其鑒也”,“不是臣等強逼娘娘和番,奈番使定名索取;說自古以來,多有因女色禍國者” :毛延壽慫恿元帝沉溺酒色,所謂“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怎能不廣選美女以充后宮?”五鹿充宗現在又以“女人禍水”為據,強逼元帝獻嬙和番,他們對待女人的態度表面上完全相反,其實質則是一致的,都把女人當作犧牲品,或詐錢,或保官,內心深處隱藏著非常卑下的骯臟的利己目的,而絲毫也不顧及民族的尊嚴。他們在投江殉國的王照君面前黯然無光,在漢元帝面前也顯得非常渺小。
(三)
《漢宮秋》是一個抒情悲劇,漢元帝是貫穿全劇的抒情主角。但劇中的漢元帝已經不是歷史上那個封建帝王漢元帝了。在《漢宮秋》中,漢元帝主要是作為漢民族的象征而出現在觀眾面前的。
作者極寫元帝的善良多情。他深夜巡宮,聽到琵琶聲,命昭君接駕。一見昭君有傾國之色,便神魂顛倒,喜出望外,禁不住手舞足蹈起來。當他得知因為毛延壽從中作糶,使他不得寵幸昭君,立即下令“拿毛延壽首級報來” 。昭君為其遠在秭歸的父母求取恩榮,元帝欣然答應,并封昭君為明妃。自從得幸昭君,他“如癡如醉,久不臨朝” ,見文武無心,離明妃悲秋。明妃在他眼中如月里嫦娥,“體態是二十年挑剔就的溫柔,姻緣是五百載該撥 (注定)下的配偶,臉兒有一千般說不盡的風流”。奸臣逼他獻嬙和番,這對他來說簡直是睛天霹靂,他堅決不肯,斥責奸臣: “我養軍千日,用軍一時; 空有滿朝文武,那一個與我退的番兵! 都是些畏刀避箭的,恁不去出力,怎生教娘娘和番?” 奸臣以紂王因寵妲已而亡國相逼,他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辟護: “俺又不曾徹青云高蓋起摘星樓” ,訓斥奸臣: “你須見舞春風嫩柳宮腰瘦,怎下的教他環佩影搖青塚月,琵琶聲斷黑江秋! ”他質問奸臣: “昭君共你每有甚么殺父母冤仇?”他要求文武們商量對策,以退番兵,“免教昭君和番” ; 他揭穿奸臣,“大抵是欺娘娘軟善,若當時呂后在日,一言既出,誰敢違拗! 若如此,久已后也不用武,只憑佳人平定天下便了! ”昭君挺身而出,請求和番,以息刀兵,元帝只得忍痛割愛,他提出要親去霸陵橋,送餞一杯去,“怕娘娘覺饑時吃一塊淡淡鹽燒肉,害渴時喝一杓兒酪和弼。我索折一枝斷腸柳,餞一杯送路酒。眼見得趕程途,趁宿頭,痛傷心,重回首,則怕他望不見鳳閣龍樓,今夜且則向霸陵橋畔宿。”霸陵餞別,作者寫元帝與昭君的別情感人肺腑。
說什么大王、不當、戀王嬙,兀良,怎禁他臨去也回頭望!那堪這散風雪旌旗影悠揚,動關山鼓角聲悲壯。呀,俺向著這迥野悲涼。草已添黃,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蒼, 人搠起纓槍, 馬負著行裝, 車運著糧, 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 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墻; 過宮墻,繞回廊; 繞回廊,近椒房; 近椒房,月昏黃; 月 昏黃,夜生涼; 夜生涼,泣寒螀; 泣寒螀,綠紗窗; 綠紗窗,不思量!
……
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 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掛昭陽,我那里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我只索大臣行說一個推辭謊,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不見他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里風光?唱道佇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寒雁南翔,呀呀的聲嘹亮,卻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氈車半坡里響。
這一段曲子把元帝憂傷恍惚,凄切纏綿的心里狀態表現得淋漓盡致。面對眼前深秋蒼涼的曠野,想起回宮后寂寞空虛的秋夜,怎不叫他痛苦悲傷!車聲使他心碎,雁聲使他斷腸,難見的昭君啊,再也不會回到身旁。
明妃和番去后,元帝一百日不曾設朝。一天,夜景蕭條,好不煩惱,掛起美人圖以解悶懷。在他疲倦困睡時,昭君從北地逃回漢宮,剛叫一了聲“陛下,妾身來了也” ,便被番兵抓走了。元帝從夢中驚醒,呼喚娘娘,無人答應,抬頭一看,“卻原來是畫上的丹青”。正在悲痛惆悵,傳來幾聲雁鳴:
多管是春秋高,筋力短;莫不是食水少,骨毛輕;待去后愁江南網羅寬;待向前,怕塞北雕弓硬。
傷感似替昭君思漢主,哀怨似作薤露哭田橫,凄愴似和半夜悲歌聲,悲切似唱三疊陽關令。
這失群的孤雁和離開明妃的他一樣可憐;這失群的孤雁和遠去番邦的明妃一樣進退兩難;這孤雁是不幸的象征,令他同情。但這孤雁的叫聲又給他帶來無窮的煩惱,使他因思念明妃而“神思不寧”的心境更加惡化。他馬上想到,遠在番邦的明妃聽見這“尋子卿,覓李陵”的雁叫聲,心中也一定不會好受。她“雖然薄命,不見你個潑毛團,也耳根清凈” ,于是他對孤雁的叫聲便由同情變成討厭,希望大雁快快離開。可是大雁偏偏不愿離去,呀呀哀鳴:
又不是愛聽,大古似林風瑟瑟,巖溜冷冷。我只見山長水遠天如鏡,又生怕誤了你途程。見被你冷落了瀟湘暮景,更打動我邊塞離情。還說甚雁過留聲,那堪更瑤階夜永,嫌殺月兒明!
……漢昭君離鄉背井,知他在何處愁聽?
孤雁呀呀飛過,檐間鐵馬丁丁,寶殿御榻冷清,落葉蕭蕭,長門燭暗,“一聲兒繞漢宮,一聲兒寄渭城” 。明知憂思過度添白發,還只是思念昭君勸不醒。
總之,作者用夢會、雁聲表現元帝的孤凄心情和對昭君的思念,其多情如此,能不感人?!
《漢宮秋》沒有孤立地表現元帝的多情與善良,而是把它與思念忠臣良將和斥奸罵佞結合在一起來寫的。他懷念為劉家創江山立下十大功勞的韓信,斥責身邊文武: “太平時,夸你宰相功勞; 有事處,把俺佳人遞流 (流放) 。你們干請了皇家俸,著甚的分破帝王憂?”他揭露這些逼他獻出昭君的文官武將和拿美人圖叛漢投匈的“忘恩咬主賊禽獸” 毛延壽是一丘之貉,他后侮自己“空掌著文武三千隊,中原四百州” ,到頭來,一個站出來為君分憂的也沒有。他對文武眾卿的言語,都答應照辦; 關鍵時刻,他的話文武公卿一句也不依。他痛感“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 ,今日“做了別虞姬楚霸王,全不見守玉關征西將。那里取保親的李左車,送女客的蕭丞相” 。
《漢宮秋》中元帝的多情善良、愛憎分明以及對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和依戀,都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表現,而不僅僅是封建帝王的性格特點。漢元帝和昭君的關系,既是封建帝王的愛情,也是中國人民要求和平安定生活的生動反映。呼韓邪單于以武力相威脅索取昭君,是對封建帝王個人愛情生活的破壞,更是對整個漢民族安定生活的挑戰。尚書五鹿充宗力主割愛獻嬙,也不是什么愛國和番的行為,而是和毛延壽遙相呼應的可恥行徑。元帝的勉強獻嬙和對奸臣的斥責、對昭君的依戀和對忠臣的思念,有著特定的政治背景,并非完全出于個人的生活需要。正是在作者所描寫的典型環境中,昭君投江和歷史上的昭君出塞,元帝的不愿獻嬙和歷史上的守信賜嬙一樣,都具有愛國的性質。而劇中尚書逼迫獻嬙和歷史上的元帝賜嬙也有了帶根本性質的區別。《漢宮秋》這一抒情悲劇的主要意義就在于: 它不僅表現了元帝和昭君為了愛國而生離死別,同時也表現了中國人民在民族危機的關鍵時刻,犧牲個人幸福乃至生活而保衛國家民族尊嚴的愛國精神和民族節操。
《漢宮秋》既然是抒情悲劇,所以不以人物個性鮮明和劇情曲折取勝,而以濃郁的抒情色彩取勝。這一特點首先表現在全劇曲詞優美,哀婉動人。其次,作者用唱詞節奏由緩變急,情調由歡變悲,道具由琵琶變孤雁來表現元帝與昭君歡會與分離前后感情的變化,自然貼切,富有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