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勸 學》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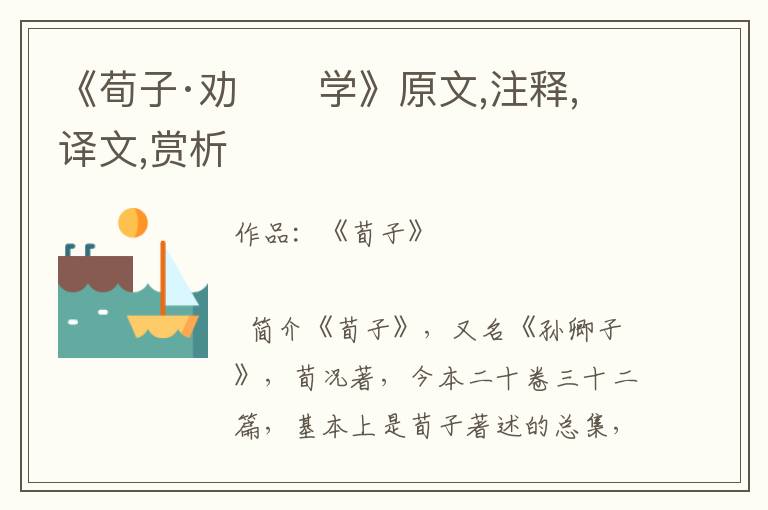
作品:《荀子》
簡介
《荀子》,又名《孫卿子》,荀況著,今本二十卷三十二篇,基本上是荀子著述的總集,也是研究荀子哲學思想的第一手資料。
荀況(約前313—前238),又稱荀卿或孫卿,趙國(今山西安澤)人。戰國時期思想家、教育家,曾三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校長),為當時最負盛名的學者之一。他從哲學上總結了諸子百家的論戰。荀子的思想來源于孔子,他發展了儒家的禮治思想,主張禮法兼治,王霸并用。他強調學習、后天的努力對人的精神發展的重要作用。對于儒家經典的傳授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勸學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繩,揉以為輪①,其曲中規,雖有槁暴②,不復挺者,揉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③,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長于無禍。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⑤,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發,系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⑥,莖長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⑦,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⑧,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⑨。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蛇鱔之穴無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⑩,鼫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
注釋
①揉:同“煣”,用微火熏烤木料使其彎曲。 ②槁暴(gǎopù):烤干。 ③干(hán):同“邗”,指吳國;貉(mò):同“貊”,我國古代東北部的少數民族。 ④跂(qǐ):通“企”,踮起腳后跟。 ⑤生:同“性”,人的資質。 ⑥射(yè):草名,根可入藥。 ⑦滫(xiǔ):臭水。 ⑧柱:通“祝”,折斷。 ⑨醯(xī):醋。 ⑩螣(téng):傳說中能飛的神蛇。 鼫(shí):鼠名,又稱石鼠、土鼠。
譯文
君子說:學習是不可以停止的。青是從藍草中提取出來的,反而比藍草更青;冰是由水凝結成的,反而比水更寒冷。木料筆直地合乎繩墨,但把它熏烤彎曲做成車輪,它的彎曲程度就同圓規所畫的圓相合,即使再將它燒烤暴曬,它也不會變直了,這是因為熏烤彎曲使它這樣。所以木料受到墨線的校正才能取直,金屬制成的刀應在磨刀石上磨過才變得鋒利。君子廣泛地學習,而又能夠每天不斷地反省自己,那就會使自己見識高明,而行為也沒有什么過錯了。
因而,不登上高山,就不知道天有多高;不俯視幽深的溪谷,就不會知道地有多厚;不知道前代圣明帝王的遺言,就不會知道學問的精深博大。吳國、越國、夷族、貊族的人,生下來時啼哭的聲音都是一樣的,而長大以后的習俗卻迥乎不同,這是因為教化使然的。《詩經》上說:“哎!你們這些君子啊,不要時常歇息著。安心地供奉你們的職位,要愛好正直的行為。神知道了這些以后,便會給你們很大的幸福!”對于一個人來說,精神的修養沒有比與圣賢之道融為一體更高的,幸福沒有比無災無難更大的。
我曾經整天地思考,可是卻不如片刻之間的學習得到的多;我曾經踮起腳跟眺望,可是并不如登上高處看見的多。登上高處招手的時候,你的手臂并沒有加長,但是在遠處的人卻能看得見;順著風向呼喊,你的聲音并沒有加強,但聽的人就覺得很清楚。憑借車馬的人,并不是因為他善于走路,但到達了千里之外;憑借船、槳的人,并不是因為他善于游泳,但渡過了江河。君子的資質與普通人并無二致,只是他們善于利用外物罷了。
南方有一種鳥,叫做蒙鳩,用羽毛為自己做窩,又用毛發將窩密編起來,系在蘆葦的花穗之上。風吹來的時候,葦穗就斷了,窩掉下來,鳥蛋跌破了,小鳥摔死了。當然,它所做的窩并不是不完善的,只是因為窩所系的地方而使它這樣。西方有一種樹,叫做射干,莖長四寸,生長在高山之上,俯臨七百多尺的深淵。并不是它的莖能長到那么高,而是它所處的位置使它這樣。蓬草即便是生長在大麻之中,不去扶持它也會長得挺直;雪白的沙子若是放在黑土之中,就會跟黑土一般黑了。蘭槐的根,原本是香芷,但是若把它浸在臭水中,君子就不再會去接近它,普通的人也不再會去佩帶它。并不是蘭槐的本質不美,只是因為所浸泡的臭水而使它這樣的。因此,君子安家確定住所必定會選擇鄉鄰;外出交游必定會去接近賢士,這是為了防止自己走向邪道而不斷地接近正道。
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一定會有它的原因的;榮辱來的時候,肯定是與人的行為相對應的。肉腐爛了就會生蛆,魚干枯了就會生蟲。當人懈怠疏忽而忘記了自身修養的時候,災禍也就來了。堅硬的東西自然會被用作支柱,柔軟的東西自然會被用來捆束東西。如果有邪惡污穢的東西在自己身上,那是會招致怨恨的。鋪在地上的柴草看起來都是一樣的,但火總先在干燥的柴草上燒起來;平坦的地面看起來是一樣的,但是水總是向低濕的地方流去。草木是依類生長的,禽獸是合群而生的,萬物都依附于它們的同類。因此,箭靶一張設,弓箭便往這邊射來了;樹林一茂盛,有人就拿著斧頭來這里砍伐了;樹木一成蔭,群鳥便到這里棲息了;醋一變酸,蚊子便匯集過來了。所以說話有時會招致災禍,行為有時會招致羞辱,君子對自己的立身行事應當小心謹慎!
積土成山,山高則風雨興;積水成淵,水深則蛟龍生;積善成德,德行成則心智澄明,圣人的思想境界也就具備了。所以不從一步兩步開始積累,就沒有辦法到達千里之外;不匯積涓涓細流,就無法成為江河。駿馬日行千里,但它一躍也不會超過六丈;劣馬日行不已,十日也能到達千里之外,它的成功,即在于不停蹄地跑。雕刻東西,如果刻一下就把它放在一邊,即便是腐爛的木頭也不能被刻斷;如果不停地刻下去,即便是金屬或者堅石都會被雕刻成形。蚯蚓沒有鋒利的爪子和牙齒,也沒有強壯的筋骨,但是它卻能夠上食塵土,下飲黃泉,這是因為它用心專一之故;螃蟹有八只腳兩只螯,但是要是沒有蛇、鱔的洞穴,它便無處寄身,這是因為它用心浮躁。因此,如果沒有專心致志、埋頭苦干的精神,就不會有洞察一切的聰明;如果沒有默默無聞的工作,就不可能會有非常顯赫的功績。徬徨于歧路的人是達不到目的地的,依違在兩個君主之間的,最終不能為兩者所容。一個人的眼睛不可能同時看兩樣東西,而且都看得很清楚;耳朵不可能同時聽兩種聲音,而且全都能聽清楚。螣蛇沒有腳,但是它卻能夠飛;鼫鼠雖然有五種技能,卻陷入了困境。《詩經》上說:“布谷落在桑樹上,領著七只小鳥在飛。那些善人君子們,他們的儀表始終是純一的。儀表是純一的,因而他的心志就像受到了約束一般。”所以君子學習的時候,要把心志集中在一點之上。
天論
天行有常①,不為堯存②,不為桀亡③。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④。強本而節用⑤,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⑥,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⑦,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兇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⑨,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⑩,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兇。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⑬。故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⑮。
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⑯。如是者,雖深⑰,其人不加慮焉⑱;雖大⑲,不加能焉;雖精⑳,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㉑。舍其所以參㉒,而愿其所參㉓,則惑矣。
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㉔,夫是之謂天。唯圣人為不求知天㉕。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㉖,夫是之謂天情㉗。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㉘,夫是之謂天官㉙。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㉚。財非其類以養其類㉛,夫是之謂天養㉜。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㉝。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兇。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㉞。其行曲治㉟,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所志于天者㊱,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㊲。所志于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㊳。所志于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㊴。所志于陰陽者,已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㊵。官人守天㊶,而自為守道也。
治亂天邪㊷?曰:日月星辰瑞歷㊸,是禹、桀之所同也㊹;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啟蕃長于春夏㊺,畜積收臧于秋冬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㊼。”此之謂也。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㊽,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輟行㊾。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㊿。君子道其常〔51〕,而小人計其功〔52〕。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53〕!”此之謂也。
注釋
①天:指自然界。常:一定的規律。 ②堯:古代傳說中的賢君。 ③桀:夏朝最后一個君主,暴君。 ④應:對待;治:合理的措施;亂:不合理的措施。 ⑤本:指農業生產。 ⑥養備:供養完備;動時:勤勞而且適時。 ⑦循:遵循;不貳:堅定不移。 ⑧妖怪:指自然界中的災害、變異等現象。 ⑨略、罕:均指少。 ⑩倍:通“背”,違背。 薄:逼近,侵襲。 受時:遭遇到的天時。 ⑬道:指統治措施。 天人之分:指自然和人事的區分。 ⑮至人:最明事理的人。 ⑯天職:自然的功能。 ⑰深:思慮深遠。 ⑱其人:指至人。加慮:超越自然現象而替天別作思慮。 ⑲大:指才能廣大。 ⑳精:指見識精妙。 ㉑參:參與、配合。 ㉒所以參:指人為的努力。 ㉓愿:指望;所參:指天地。 ㉔無形:自然的功能無形跡可以尋。 ㉕不求知天:對自然不做主觀臆斷。 ㉖臧:通“藏”,蘊藏;焉:這里。 ㉗無情:人類自然具有的情感。 ㉘相能:互相替代。 ㉙天官:人類自然具有的感官。 ㉚天君:心是自然具有的五種感官的主宰。 ㉛財:通“裁”,利用;非其類:與人相異的萬物。 ㉜天養:自然的供給。 ㉝天政:自然的“政令”。 ㉞官:職守;役:役使。 ㉟曲:周遍,涵蓋各個方面。 ㊱志:通“識”,認識,研究。下同。 ㊲已:通“以”,由于,下同;見:通“現”,顯現,下同;期:預期。 ㊳宜:土地宜于作物生長的各項條件;息:生長。 ㊴事:農業生產。 ㊵治:治理政事。 ㊶官人:專職人員;守天:掌握、研究自然現象與規律。 ㊷邪:通“耶”,疑問詞。 ㊸瑞歷:自然的祥瑞現象。 ㊹禹:舜的繼承人,古代傳說中的賢君。 ㊺繁:眾多;啟:萌芽;蕃:茂盛。 ㊻畜:通“蓄”,積聚。 ㊼詩句引自《詩經·周頌·天作》。作:生;高山:指岐山,位于今陜西省岐山縣東北;大(tài)王:也稱古公亶父,為周文王姬昌的祖父;荒:開辟;作:興起;文王:周文王姬昌;康:安居、安定。 ㊽惡:厭惡;輟:廢止。 ㊾匈匈,通“讻讻”,喧嘩吵鬧。 ㊿常道、常數、常體:指一定的規律、法則、行為標準。 〔51〕道:奉行、遵行。 〔52〕功:事物的功利,指眼前的利益。 〔53〕該引文不見于現存《詩經》。愆(qiān):差錯;恤:顧慮。
譯文
自然的運行是有一定規律的,不會因為堯而存在,也不會因為桀而滅亡。用合理的措施去對待自然規律就吉利,而用不合理的措施去對待則不吉利。若加強農業生產并且節約費用,即便是天也不能使人貧窮;供養完備并且活動適時,即便是天也不能使人生病;遵循天道并且堅定不移,即便是天也不能使人受禍害。因而,水旱災害不能使人饑餓,寒暑驟變不能使人生病,自然災異不能給人帶來兇險。若荒廢了農業生產并且費用奢侈,即便是天也不能使人富裕;供養不足并且活動稀少,即便是天也不能使人健全;違背天道并且胡作妄為,即便是天也不能使人吉利。因而,水旱災害未到而饑餓已經產生,寒暑時節未近而疾病已經產生,自然災異未及而兇險已經產生。這樣,雖然他遭遇到的天時是與社會安定之際相同,但他所受到的禍害卻與社會安定之際迥異,這不可以埋怨天的不公,而是因其所行之道使然。因而,若是明白了自然與人事的區別,便可以稱之為至人了。
不做卻能成功,不求卻能得到,這便稱之為自然的功能。對于此類情況,即便異常深奧,至人是不會去思慮它的;即便異常廣大,至人是不會去夸大其能的;即便是精妙無比,至人是不會去多加考察的。這便是不與自然爭能。天有天時,地有地財,人若能合天時地利以用之,則可謂與天地配合了。若是人放棄了人為的努力,而只是指望天地,那么是糊涂透頂了。
群星相隨旋轉,日月交替照耀,春夏秋冬四季更迭,陰、陽二氣相互作用,風雨普施萬物,萬物得到各種自然條件的協調而生,得到其給養而成。人們看不見自然的行事過程而目睹了其功績,這便稱為“神”。人們都知道自然所化生的萬物,但不知道生成萬物的無形無跡的過程,這便是“天”。只有圣人是不求知天的。
自然的功能已經確立,自然的功績已經完成,人的形體具備了,人的精神也隨之產生。好惡、喜怒、哀樂等情感蘊藏在形體之中,是人的自然情感;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形體各有其不同的接觸外物的能力,但不能相互替代,這是人自然具有的感官;心處胸膛之中而統率人的五官,這是人自然具有的主宰;人利用自身之外的萬物來供養人類,這是自然的養育;順應人類的稱為福,違逆人類的稱為禍,這是自然的政令。遮蔽人心,擾亂感官,舍棄自然的養育,違逆自然的政令,背離自然的情感,從而喪失了自然的功績,這是大兇。圣人則使人心純凈,感官端正,完備自然的供養,順應自然的政令,持養自然的情感,從而成全自然之功績。這樣,便知道哪些是應該做的,哪些是不應該做的,因而天地盡其職守,萬物供人類役使。于是,人的行為各個方面都有條理,人的給養各個方面都恰到好處,生命未曾受到些許損害,這便稱為“知天”。
因而,最能干的人是不去做那種不能做的事情,最聰明的人是不去想那種不能想的問題。對于天的研究,是根據已經顯現出來的現象來預測將來;對于地的研究,是根據已經顯現出來的適宜作物生長的條件來安排作物;對于四季的研究,是根據已經顯示出來的農業季節性規律來從事農業生產;對于陰陽的研究,是根據已經顯示出來的和諧變化來治理。圣人任用專職的官員觀察天象,而自己則恪守自然規律。
社會的安定、混亂是由天造成的嗎?答:日月星辰以及祥瑞之象,在禹和桀的時代都是相同的,但是禹能使天下安定,而桀則使天下混亂,社會的安定、混亂并不是由天造成的。那么,是時令造成的嗎?答:萬物都是在春夏萌芽成長,在秋冬收獲貯藏,這在禹、桀的時代也是相同的,但是禹能使天下安定,而桀卻使天下混亂,社會的安定、混亂并不是由時令造成的。那么,是地造成的嗎?答:萬物在大地上則能夠生長,離開大地則死亡,這在禹、桀的時代也是相同的,但是禹使天下安定,桀卻使天下混亂,社會的安定、混亂并不是由地造成的。《詩經》里面說:“天生高峻岐山,太王開辟艱難。民眾辛勤勞作,文王撫定平安。”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天不會因為人們厭惡寒冷而廢除冬天,地不會因為人厭惡遼闊遙遠而不廣闊,君子不會因為小人的喧嘩不止而廢棄自己的行為。天有永恒的規律,地有永恒的法則,君子有永恒的行為準則。君子的行為是遵循永恒的法則,而小人則斤斤計較于眼前的得失。《詩經》上說:“若禮義無紕漏,何必顧慮別人的言語呢?”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解蔽
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治則復經,兩則疑惑矣。天下無二道,圣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妒繆于道而人誘其所迨也①。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離走,而是己不輟也。豈不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于使者乎!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
故為蔽: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于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于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啟,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群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于鬲山,紂縣于赤旆②,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于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③。文王監于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蔽于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于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于宋,奚齊戮于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寧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勉之強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
昔賓孟之蔽者④,亂家是也。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賢,申子蔽于勢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辭而不知實,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欲謂之道盡嗛矣⑤,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
圣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⑥。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
注釋
①迨:通“怡”,喜愛。 ②旆(pèi):古代豎掛的旗幟下懸垂的裝飾品。 ③九有:有,通“囿”,九囿,即九州。 ④賓孟:孟,通“萌”、“氓”,民。賓孟,指游士。 ⑤嗛(qiè):滿足,指欲望少而知足。 ⑥縣衡:縣,同“懸”。縣衡,掛秤。
譯文
一般人的毛病,是被事物的某個局部所蒙蔽而不明白整體的大道理。如果見解精審,就步入正道;如果在偏見和大道理之間徘徊,就會走向迷途。天下不會有兩種對立的正道,圣人也不會有兩種對立的心志。現在,諸侯的政令不同,百家學說各異,那么其中必定是有對、有錯,有的能導致安定、有的會導致混亂。搞亂了國家的君主們,弄亂了學派的學者們,這些人沒有不誠心實意地尋求正道而為自己服務的,只是因為他們對于正道既嫉妒又帶有偏見,因而別人就可以根據他們的偏好而引誘他們。他們都偏愛自己所學的東西,惟恐聽到別人對自己學說的指責。他們憑借自己所偏愛的學說去觀察與自己不同的學術,惟恐聽到對異己學說的贊美。這樣,他們與正道相背而馳,但卻還是自以為是、不能停止。這豈不是被事物的局部所蒙蔽而失去了對正道的追求嗎?人們如果心不在焉,那么即便是白的黑的東西擺在眼前也會看不見,即便是雷鼓在旁邊敲擊,耳朵也聽不見,更何況是那些心被蒙蔽了的人呢?對于掌握了正道的人,搞亂國家的君主在上面非難他,搞亂了學派的人在下面非議他,這豈不是很悲哀的嗎?
什么東西蒙蔽人?欲望可以造成蒙蔽,憎惡可以造成蒙蔽;開始可以造成蒙蔽,終了可以造成蒙蔽;遠可以造成蒙蔽,近可以造成蒙蔽;博聞可以造成蒙蔽,淺識可以造成蒙蔽;好古會造成蒙蔽,悅今可以造成蒙蔽。事物只要有所不同,都可以相互造成蒙蔽,這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個禍害啊!
從前君主被蒙蔽的,夏桀、商紂就是例證。夏桀被末喜、斯觀所蒙蔽而不賞識賢臣關龍逢,因而迷惑了自己的心志,昏亂了自己的行為;紂王被妲己、飛廉所蒙蔽而不賞識微子,因而迷惑了自己的心志,昏亂了自己的行為。所以,群臣也都拋棄了忠誠而去謀求自己的私利,百姓都怨恨責怪他們而不為他們出力,賢能的人都辭官而隱居避世,這便是他們之所以喪失了九州之地,而亡失了祖宗之國的原因。夏桀死在鬲山,紂王的頭被懸掛在紅旗桿上,他們本身不能夠事先預知,而別人又沒有誰勸阻他們,這便是他們受到蒙蔽的禍害啊!商湯明察夏桀的失敗,以此為鑒,所以端正自己的心志,謹慎地治理國家,因而能夠長期地任用伊尹而本身又不背離正道,這就是他能夠取代夏桀而擁有九州的原因。周文王吸取殷紂的教訓,所以端正了自己的心志,謹慎地治理國家,因而能夠長期地任用呂望而本身又不背離正道,這就是他能夠取代殷紂而擁有九州的原因。遠方各國沒有不送上自己的奇珍異寶的,所以他們的眼睛能觀賞所有的美色,耳朵能聽到各種美妙的音樂,嘴巴能吃到各種美味。他們住在各種各樣的宮殿里,他們的名字加上了各種各樣的尊稱。他們活著的時候,天下人都歌頌其功德,死了以后天下的人都痛哭流涕,這就叫做極盛。《詩經》上說:“鳳凰翩翩起舞飛翔,它們的翅膀如盾牌一般,它們的鳴聲似洞簫般悠揚。鳳啊!凰啊!使王的心中喜洋洋。”這便是不被蒙蔽的幸福。
從前人臣中被蒙蔽的,唐鞅、奚齊就是例證。唐鞅蒙蔽于追求權勢而驅逐了國相載子,奚齊蒙蔽于爭奪君位而加罪于異母兄申生。結果唐鞅在宋國被殺,奚齊在晉國被殺。唐鞅驅逐有賢能的國相而奚齊則加罪于孝順的兄長,結果自己卻被殺了,然而仍不明白為什么,這就是蒙蔽的禍害啊!所以因貪婪鄙陋而背叛、爭權奪利,反而不遭到危險、屈辱,以至于滅亡的,從古到今,不曾有過。鮑叔、寧戚、隰朋都是仁愛、明智而不被蒙蔽的,所以他們能夠扶助管仲,而且他們的名利、官祿都和管仲并列。召公、呂望都是仁愛、明智而不被蒙蔽的,所以他們能夠扶助周公,而且他們的名利、官祿和周公并列。古書上說:“能夠識別賢人叫做明智,能夠扶助賢人叫做才能。不斷地努力,他的幸福定能長久。”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這就是不被蒙蔽的幸福啊!
從前,游士受到蒙蔽的,混亂學派的百家學者就是例證。墨子蒙蔽于實用而不知道文辭的修飾,宋子蒙蔽于見到人有寡欲的一面而不知道人也有貪得的一面,慎子蒙蔽于法治而不知任用賢良,申子蒙蔽于權勢而不知才智的作用,惠子蒙蔽于名辯而不知真實,莊子蒙蔽于自然而不知人為。所以,從實用的角度來論正道的,就全成了功利;從欲望的角度來論正道的,就全是滿足了;從法的角度來論正道,就全是法規條例;從權勢的角度來論正道的,就全憑權力地位便宜行事了;從名辯的角度論正道,就全是不切實際的理論了;從自然的角度來論正道,就全是因循依順了。可是,所有這些觀點,都僅僅是揭示了正道的一個方面而已。就正道而言,它的本體是恒常的,但又是能夠窮盡一切變化,任何的一個角度都不足以來概括它。這些一知半解的人,只是看到了正道的一個方面而沒有能夠真正認識它,而卻以為認識了它,并以自己的見解加以文飾。于是,在內心則擾亂了自己的思想,在外則迷惑了別人,在上的蒙蔽了在下的,在下的蒙蔽了在上的,這便是蒙蔽的禍害啊!
孔子仁愛、明智而又不被蒙蔽,所以他學習了百家的知識而集其大成,可以用來輔助先王。在天下百家學說之中,只有孔子一家掌握了這種全面的正道,推崇并運用正道,而不被成見所蒙蔽。因而,他的德行是與周公相等的,名聲是與三王并列的,這就是不受蒙蔽的幸福啊!
圣人知道思想方法上的毛病,也看到了被蒙蔽的禍害,所以,不論是欲望、憎惡,還是開始、結束,遠、近,博聞、淺識,好古、悅今,都不受它們的蒙蔽,要把所有的事物都排列出來,根據內心的一定標準進行權衡。因此,各種不同的事物就不會互相蒙蔽,以至于弄亂了條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