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生《烘托與反襯》古詩詞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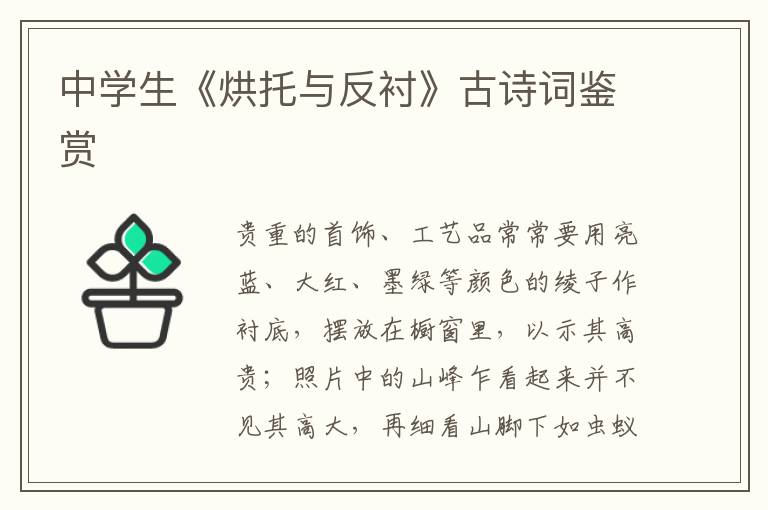
貴重的首飾、工藝品常常要用亮藍、大紅、墨綠等顏色的綾子作襯底,擺放在櫥窗里,以示其高貴;照片中的山峰乍看起來并不見其高大,再細看山腳下如蟲蟻般的牛羊,才覺其高聳入云。這就是托襯的手法,前者叫烘托,也叫正襯、襯托;后者叫反襯。繪畫也是一樣,《蒙娜麗莎》的背后有青山綠水烘托著,充滿了生氣,才更能顯出她內心的滿足,她的微笑才有那樣無窮的魅力。如果她身后是窮山惡水,則大煞風景。《神女圖》中仙女的身邊偏偏臥著一只老虎,兇猛的老虎見了她竟這般馴服,自然反襯出她的無窮神力。
寫詩常常如同畫畫,畫面的主體也要有個背景托襯著。林逋的《山園小梅》:“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這里,似乎只有朦朧清冷的月光、清淺的池水和水中橫斜的倩影,才配作梅樹的背景。這是一層烘托。接著詩人又寫鳥兒不敢隨意去棲止,怕玷污了她;蝴蝶一旦靠近了她,會忘掉自己的美麗,和她融為一體。這第二層的烘托。又把梅樹的圣潔托舉到何等高度!而在陸游的《卜算子·詠梅》中的梅樹可沒有這般幸運:它生長在“驛外斷橋邊”,在黃昏中孤獨愁苦地站著,又有凄風冷雨嚴相逼(“更著風和雨”)。然而,正是這嚴酷的外部環境,才反襯出梅樹——詩人的孤傲來:“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以上是以物為主體的。也有以人為主體的。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中,周瑜的身邊站著一位千古美人(“小喬初嫁了”)。以美人襯英雄,則更見周郎的年輕英武。此為烘托。繼而又寫他“談笑間,檣虜灰飛煙滅”:赤壁鏖兵,何等慘烈,然而卻只是“談笑間”的事,那么周郎是何等舉重苦輕的英雄!這又是反襯的力量了。這與關公刮骨療毒,卻安然下棋,棋步不亂,是同樣的手法。
詩與畫當然有其不同之處。繪畫是視覺藝術,其背景與主體一目了然,托襯較為明顯。詩歌是語言藝術,寫景是為了托情,而感情又似乎看不見摸不著,所以其托襯手法常常很隱蔽。要反復揣摩,才能體會得到。曹操的《觀滄海》,通篇描寫大海的無限廣闊。細加揣摩會發現這正烘托出詩人吞吐宇宙、雄視天下的壯闊胸懷和建功立業的積極進取精神。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乍一看不知詩人“涕下”為何。當我們“披文”(琢磨語言)“入境”之后,就會發現,這里有兩層強烈的反差(反襯)在:作者登臺遠眺,獨立蒼茫,眼前是空曠的天宇和原野。“天地”無限廣闊,望不到盡頭;自己無限渺小,竟如一粒塵埃……這是空間的反差。再看時間的反差(“悠悠”二字透露了此中消息):此臺為古代建筑,不免又生古今變易的感慨:天地悠久,無限綿長;人生短暫,真如一瞬。有這時空的兩層反差(反襯)存在,怎不讓詩人生出壯志難酬、懷才不遇、知音難覓的孤獨感。
再如“以樂景襯悲更增其悲,以悲景襯樂更增其樂”的反襯手法則顯得更加隱蔽。《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詩中描寫雨后初睛,空氣清新,柳色青青,爽人眼目,是何等開朗明快的景象!然而“西出陽關,進入大漠荒寒之境,再無故人相伴,再無眼前美景。那么,朋友,再喝一杯送行酒,再看一眼故地景吧!玩味至此,方知詩中的良辰美景絕非虛設,詩人正以此樂景襯離別的怨情。反之,則有《詩經·鄭風·風雨》中的“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的典型例子:風雨迷蒙,天氣陰晦,雞子的喔喔鳴叫更撩撥起女人思夫的愁緒……恰在此時,響起了那熟悉的敲門聲,急忙拉開門栓,啊!……那么,前面的愁景也絕非空谷來風,沒有它,女主人公之“喜”哪有這般濃度!
至于“蟬噪樹愈靜,鳥鳴山更幽”的以聲襯靜,則比較簡單,不再贅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