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思潮、流派·心理分析學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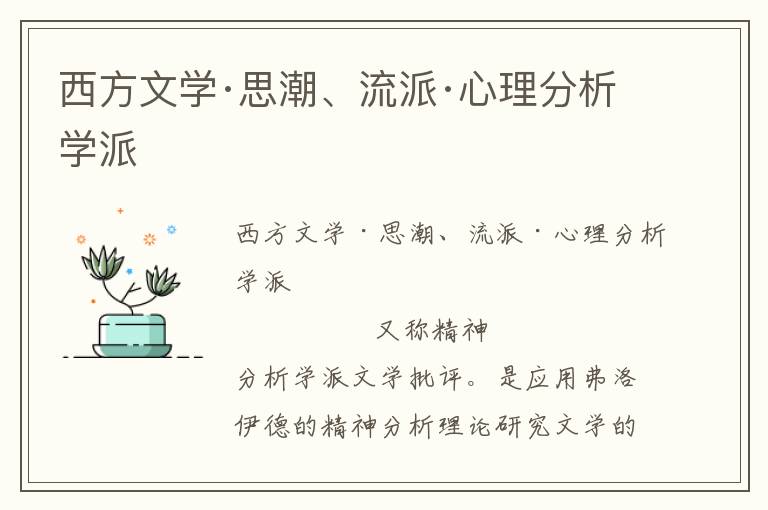
西方文學·思潮、流派·心理分析學派
又稱精神分析學派文學批評。是應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研究文學的現代批評流派。弗洛伊德著力于研究動力學式的心理學,所謂精神分析,就是通過分析心理現象來揭示隱匿在內心深處的精神原因。他認為,這些原因大多深藏在潛意識領域,而且大多與性欲有關,這兩點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前提。他認為決定精神過程有三個因素,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總是處于潛意識領域,“自我”和“超我”則可以進入意識領域,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就形成一個人的性格和心理狀態。“本我”是精神機能最基本的來源,其作用是滿足人的原始的本能的欲望;“自我”是保護個人精神的調節因素,對“本我”的本能沖動加以適當控制;“超我”是保護社會的精神因素,其作用是壓抑“本我”的本能沖動,不讓它闖入意識領域。弗洛伊德把人的性欲本能稱為“里比多”,當它被壓抑在潛意識領域時,逐漸郁積而成所謂“情結”。最有名的是男孩戀母妒父的俄底浦斯情結,及女孩戀父妒母的埃勒克特拉情結。受到壓抑的欲望總是以曲折的方式進入無意識領域。弗洛伊德把夢看成是滿足意愿的曲折方式之一,把文學創作也看成是受壓抑的“里比多”的升華,是以想象的作用代替現實行動,在幻想中求得滿足。他常在自己的著作中用文學和藝術作品為例來闡明心理分析原理。最有名的是對《哈姆萊特》 中王子的心理分析,認為正是由于“俄底浦斯情結”造成了他的性格和行為。對達·芬奇的繪畫、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和惠特曼的詩歌,弗洛伊德派的批評家們都認為是受到壓抑的同性戀欲望的升華。
文學批評中的心理分析(或稱精神分析) 者,在作品分析中采用了弗洛伊德的某些原理。有的批評家用弗洛伊德關于“本我”、“自我”、“超我”的三重關系來分析作品中的人物關系。如默里在論述美國作家麥爾維爾的長篇小說《白鯨》時,就把白鯨視為新英格蘭清教精神的象征,亦即麥爾維爾本人“超我”的象征; 渴望報復,驅使全體船員追捕白鯨而遭毀滅的船長埃哈伯,被視為無可遏制的“本我”的象征; 而大副斯巴達克努力調停由白鯨和埃哈伯船長代表的敵對力量,則象征著“自我”的理性精神。“俄底浦斯情結”也常被用來分析莎士比亞、勞倫斯、喬伊斯、福克納等作家的某些作品。弗洛伊德的理論是一種泛性主義,即基本上用性欲沖動來解釋人的各種精神和實踐活動。在這方面,心理分析派引起的爭論最多,如把文學作品中的種種形象都解釋為性象征。把騎馬、跳舞、飛翔都解釋為性的快感的象征等,瑪麗·波拿巴在論美國作家愛倫·坡的生平與創作時,把坡的全部作品視為俄底浦斯情結的產物,甚至把坡的嗜酒也說成是逃避現世而忠于死去的母親的一種方式。她對作品的分析完全側重性象征方式,把小說中描寫的地窖、酒窖都解釋成子宮的象征,甚至把坡的名詩 《尤拉盧姆》,中下垂的翅膀說成是暗指坡本人的陽萎、這類牽強的批評常受到學者和一般讀者的反對。
弗洛伊德研究的主要對象是人,是人的潛意識,因而心理分析派文學批評著重研究作家潛意識在作品中的流露,研究作家個人心理與作品之間的關系。發生在作品中的一切都要歸結到作家個人心理的偶然性,就是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是為了和作家的心理,特別是潛意識掛起鉤來。如瓊斯分析哈姆萊特的躊躇和延宕,其目的就是為了讓讀者了解莎士比亞心理的許多更為深沉的顫動。心理分析派的解釋盡管有時非常牽強,但在運用得當時,對于理解某些作品也不無價值。其主要局限在于它常常忽略決定作品內容和形式的社會歷史因素,也難以說明一部作品的審美價值。它的某些概念和術語在現代各種新的批評流派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