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國語·齊姜勸重耳勿懷安(節選)》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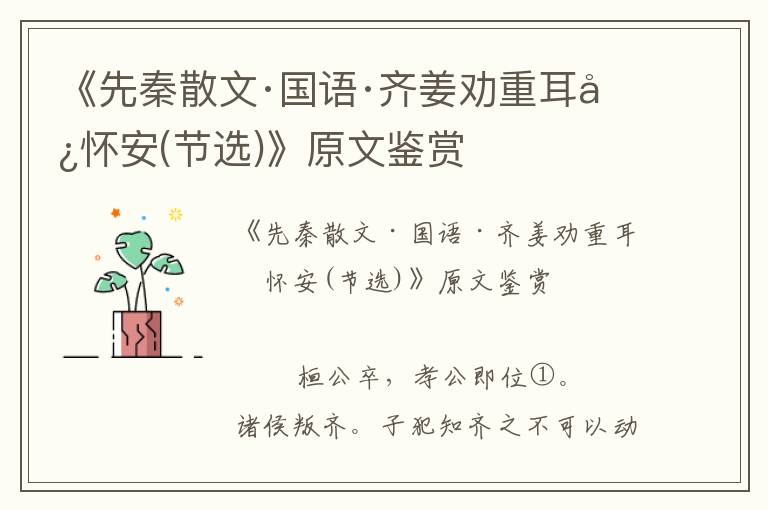
《先秦散文·國語·齊姜勸重耳勿懷安(節選)》原文鑒賞
桓公卒,孝公即位①。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②,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焉③,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④,姜氏殺之,而言于公子曰⑤:“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⑥。《詩》云⑦:‘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于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
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于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⑩:‘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11):‘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畏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12),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從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13),閼伯之星也(14),實紀商人(15)。商之饗用三十一王。瞽史之紀曰(16):‘唐叔之世(17),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
【注釋】 ①孝公:齊桓公之子齊孝公,公元前642年——公元前633年在位。 ②子犯:晉文公重耳的舅父,名狐偃。 ⑧蠶妾:宮中養蠶的侍女。 ④姜氏:齊桓公之女,重耳之妻。 ⑤公子:即重耳。 ⑥命:天命。 ⑦《詩》:指《詩經·大雅·大明》。 ⑧每:雖然。 ⑨遑:閑暇。 ⑩西方之書:即《周書》。 (11)《鄭詩》:指《詩經·鄭風·將仲子》。 (12)辟:刑法。 (13)大火:星名。 (14)閼伯:人名,唐堯時為火正。 (15)紀:標志。 (16)瞽史:記載陰陽天時禮法的書。 (17)唐叔:武王之子叔虞,封地為唐,是晉國的先人。
【今譯】 齊桓公去世了,齊孝公即位。諸侯背叛了與齊國的盟約。子犯了解齊國不會允許重耳回到晉國的請求,而且了解重耳認為齊國安逸,有在此終老之心,就打算離開齊國,但又擔心重耳不肯走,于是就與隨行重耳的人在桑樹下商量這件事。齊國宮中一個養蠶的侍女正在那里,他們沒人發現她。這個侍女把子犯他們的談話報告給姜氏,姜氏把她殺了,然后對重耳說:“你的隨從要帶你離開齊國,聽到了這件事的人已經讓我除掉了。你一定要聽他們的,不能三心二意。三心二意的話就不能完成入晉為君的天命了。《詩經·大雅·大明》說:‘上天保佑著你,你心里不要遲疑不決。’周武王知道天命,所以能成大事,遲疑 哪能成事呢?你在晉國因躲避殺身之禍才來到這里。自從你走后,晉國沒有一年安寧過,晉國的人民也沒有一個可以信賴的君主。上天還沒有讓晉國亡國,晉獻公又沒有其他的兒子了,能統治晉國的人,不是你是誰呢?你應當努力啊!上天已經保佑你了,你要遲疑的話,一定會惹禍。”
公子重耳說:“我不會被說動的,一定要老死在這里。”姜氏說:“不對。《詩經·小雅》上說:‘那些仆仆路途的征夫,雖然常惦記著自己要辦的事,還恐怕來不及辦好。’他們晝夜奔忙,連休息的閑暇都沒有,還怕做得不夠,何況那些聽從自己的欲念眷戀安逸的人,怎么能來得及呢!人要是不想實現自己的目標,他哪還能實現呢?日月運行不息,人又豈能貪圖安逸?《周書》上有一句話說:‘留戀安樂,會妨礙大事。’《詩經·鄭風》說: ‘他是可愛的,但是別人的閑話,也是可怕的。’從前管仲有一段話,我曾聽到過,說的是:‘害怕國家政令的威嚴象害怕疾病一樣,這是最好的國民。象流泄的水一樣放縱自己的欲望,這是最壞的國民。看到自己所要的又因害怕政令的威嚴,不敢妄動,這是中等的國民。如果百姓們害怕國家的政令象害怕疾病一樣,統治者才能用威嚴來統治上等的國民。要在中等國民的頭上顯示出政令的威力,他們才能畏懼刑法。下等的國民放縱自己的欲望如同流泄的水一樣,距離政令的威嚴很遠,所以稱之為下。治理刑法,要以中等國民為主要對象。《詩經·鄭風》里的話,我要遵照去做。’大夫管仲就是以此治理齊國的,因此才輔佐先父桓公形成了稱霸諸侯的大業。你要是不顧拯救晉國的大事,不也是很難的嗎?齊國的政治已經敗落了,晉國的混亂已經很久了,你的隨從的謀劃夠忠心的了,時機已到,你做國君的日子近了。做一國的君主能夠救助百姓,要是放棄這種事情,簡直不能算是人。齊國已經敗落,不可久居,有利時機不可錯過,從者的忠心不能棄置不顧,自己的私念不能放縱,你一定要快點走。我聽說晉國的先祖剛被封時,大火是歲星,這是火正閼伯掌管的星,實際是商朝的標志。商朝靠此先后經歷了三十一位君主。瞽史上面記載說:‘唐叔的朝代,將同商朝一樣,有三十一位國君。’如今還沒到一半。晉國的混亂不會拖幾代,總要平定,晉獻公的兒子中又只剩你一個了,你一定會統治晉國的。為什么還留戀安樂!”重耳不聽她的話。
【集評】 民國·秦同培《國語評注讀本》:“凡作文字,優相體而裁衣。欲狀何人,即當肖其人之口吻動作,如此篇寫文公不肯去齊,有終身安焉之慨,文便極描摹其一種公子態度。寫子犯欲使公子回國計謀,極見忠心。寫齊姜之勸告引經據典,真是巾幗中之丈夫矣。看他寫一人,各有一人之身分、言語、動作。能深心體會,自能悟其妙處。”
【總案】 《國語》記載史事,能夠從實際出發,不美善,不隱惡,寫出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晉文公重耳在“三公子”中德行、才干都最為出色,而且曾創立霸業,是當時一位有名的君王,《國語》卻仍然記錄下一些表現他個性中懦弱或鄙劣的一面,“懷安”便是一例。“吾不動矣,必死于此”,沒有一點欲興大事的志氣。這樣的記史方法和態度,保存了歷史的真實面貌,使后世之人能夠從中準確地了解歷史,也能夠洞悉歷史人物的全貌。就文學價值而言,也能使久遠的歷史人物永遠富于真實可信、可見可感的生命力。
姜氏對政治問題的看法,顯然受到了管仲主張的深刻影響,與法家的思想一脈相承。這種觀念在《國語》中雖然不占主流,卻也是一種思想意識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