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莊子·田子方(節選)》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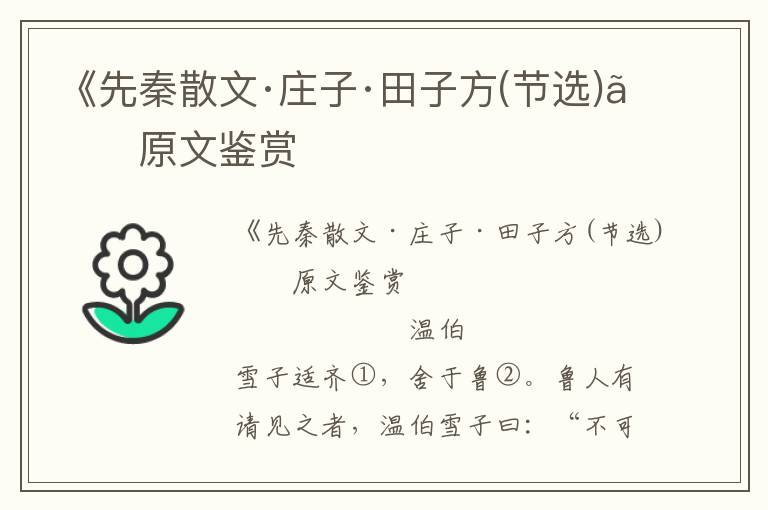
《先秦散文·莊子·田子方(節選)》原文鑒賞
溫伯雪子適齊①,舍于魯②。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③,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④,吾不欲見也。”至于齊,反舍于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⑤,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⑥。”出而見客,入而嘆。明日見客,又入而嘆。其仆曰:“每見之客也⑦,必入而嘆,何邪?”曰:“吾固告子矣⑧:‘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也,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⑨、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⑩,是以嘆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11),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 目擊而道存矣,以不可以容聲矣(12)。”
【注釋】 ①溫伯雪子:姓溫名伯,字雪子,楚國人;適,往。 ②舍:投宿,住宿。 ③中國:中原之國,這里指魯國。 ④陋:拙;人心,指人純真的本性。 ⑤蘄:求。 ⑥振:起,這里意為啟發。⑦之客:這位客人。 ⑧固:本來。 ⑨從容:舉動;一,或。⑩道:通導,開導。 (11)吾子:古代對人的尊稱,猶言您。 (120容:通庸,用;聲,聲音,指言語。
【今譯】 溫伯雪子到齊國去,途中住宿在魯國。魯國有人請求會見他。溫伯雪子說:“不行。我聽說魯國的君子雖然很懂禮義,卻拙于了解人的本性,我不想見到他。”到了齊國,返回途中又住宿在魯國,這位魯國人又請求會見。溫伯雪子說:“以前他要求見我,現在又要求見我,這一定是要來啟發我的。于是出去會見客人,進來后就嘆氣。第二天會見過客人,進來后又嘆氣。他的仆人說:“每次會見這位客人,進來后一定要嘆氣,為什么呢?”溫伯雪子說:“我本來就告訴過你,‘魯國的人,雖然很懂禮義,卻拙于了解人的本性。’先前來見我的人,見面,告別都極有禮貌,一舉一動都合乎禮儀的規矩,舉止或若龍,或若虎,他勸諫我,就象兒子對父親一樣,開導我,就象父親對待兒子一樣,因為這樣,我才嘆氣的。”孔子見到溫伯雪子后卻一言不發。子路說:“您想見到溫伯雪子時間已經很久了,見到溫伯雪子后卻又一言不發,為什么呢?”孔子說:“象那樣的人,一望見他便知大道存在于他的身上,用不著再說什么了。”
【集評】 清·宣穎《南華經解》:“雪子口中,寫得豎儒可笑。”
又:“李太白《嘲魯儒》,頗得此意。”
清·劉鳳苞《南華雪心編》:“此段前后分作兩截,純是寫溫伯雪子之真。前幅雪子不欲見魯人,強見之而嘆,嘆其多此一見也。后幅仲尼久欲見雪子,逮見之而不言,無言勝于有言也。……描寫溫伯雪子,真如藐姑射神人,冰雪肌膚,不食人間煙火,一結反照魯人,全在無字句處,凌空宕漾,妙絕文心。”
【總案】 本段借溫伯雪子之口,抨擊儒家“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的虛偽性,并以溫伯雪子與儒士的對比,寫出真性的可貴,遵從禮義的可笑。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①,受揖而立②,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僮僮然不趨③,受揖不立,因之舍④。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裸⑤。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注釋】 ①史:指畫師。 ②揖:拱手作禮。 ③儃(tan音坦)儃然:悠閑自在的樣子;趨,小步快行;臣見國君須小步快行;不趨,慢慢走,指不拘小節。 ④之:至,到;舍,客舍,住所。 ⑤般礴:盤腿而坐。
【今譯】 宋元君將要使人畫畫,眾畫師都來了,受命之后,拱手作禮,立于一旁,有的舐筆,有的和墨,屋里站滿了人,還有一半站在門外。有一位畫師最后到來,他悠閑自得,慢慢地走過來,受命后拱手作禮,并不象眾畫師一樣站在這里,而是回到自己的住所。宋元君使人去看他,這位畫師解開衣服,裸露著上身,盤腿而坐。宋元君聽后說:“是的,這才是一個真正的畫師。”
【集評】 清·胡文英《莊子獨見》:“作兩層襯寫。”
清·劉鳳苞《南華雪心編》:“張伯英以首濡墨,而草書入圣;趙子昂解衣伏地,而畫馬入神。天機所觸,皆不求形似,而自肖其真也。”
【總案】 畫師為宋元君作畫時“解衣般礴裸”式的不拘禮節,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精神的形象寫照,這與作者要求人當按照人的本性來表現自己的思想是一致的。同時,從中也可以見出作者崇尚自然的藝術觀。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①,措杯水其肘上②,發之③,適矢復沓④,方矢復寓⑤。當是時,猶象人也⑥。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⑦,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⑧?”于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⑨,足二分垂在外(10),揖御寇而進之(11)。御寇伏地,汗流至踵(12)。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窺青天(13),下潛黃泉(14),揮斥八極(15),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16),爾于中也殆矣夫(17)。”
【注釋】 ①引:拉弓;盈貫,弓已張滿。 ②措:放置。 ③發:射。 ④適:往,指射出去,矢、箭;沓,重復。 ⑤寓:寄寓,放置。 ⑥象人:木偶人。 ⑦嘗:試。 ⑧若:你。 ⑨逡巡:退步而行。 ⑩垂在外:腳垂在山石之外。 (11)揖:揖請,邀請。 (12)踵:腳跟。 (13)窺:窺測。 (14)黃泉:地之深處。 (15)揮斥:縱放奔馳;八極,八方,指整個天地間。 (16)怵然:恐懼的樣子;恂目,目眩;志,心。 (17)中(zhong音眾):命中靶;殆,危險,指列御寇射中的可能性小。
【今譯】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表演射箭,他拉滿了弓,在胳膊肘上放一杯水,開始射箭,第一枝箭剛射出去,第二枝箭又搭在弦上,第二枝箭剛射出去,第三枝箭又搭在弓弦上。在他射箭的時候,就象個木偶一樣。伯昏無人說:“你這是有心的射箭,而不是無心的射箭。你試著跟我一起登上高山,腳踩著危石,下臨萬丈深淵,你還能射箭嗎?”于是,伯昏無人就登上了高山,腳踩著危石,下臨萬丈深淵,背對深淵向后退走,腳的三分之二懸空在山石之外,邀請列御寇到懸崖上。列御寇恐懼地趴在地上,汗流到了腳跟。伯昏無人說:“至人,向上能看透青天,向下能探測黃泉,奔馳于八方,但神色卻不改變。現在你因心中恐懼而目眩,你射中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集評】 明·楊慎《莊子解》:“透語工妙。”
清·林云銘《莊子因》:“(‘背逡巡’二句)讀至此,便覺毛發悚然矣。”
清·陸樹芝《莊子雪》:“妙繪絕險。”
滑·劉鳳苞《南華雪心編》:“(‘是射之射,二句)能以巧用,而不能以神用也,二句束上啟下,措詞極妙。”
又:“此段從不射之射,托出正文。一矢方行,而二矢已注;二矢甫離,而三矢又起。御寇之技,已極精能。……轉入至人,特顯出廬山面目,全是真宰內充,并非尋常本領。上窺青天,何有于登高履危;下潛黃泉,何有于臨淵百仞;揮斥八極,何有于垂足逡巡。愈唱愈高,愈險愈快,真有飛仙劍俠之能。”
【總案】 本段以列御寇的“射之射”與伯昏無人的“不射之射”,形成對比,說明有生死之慮、性命之憂的人,即使技巧再高,一遇特殊情況,也就無從施展其技巧了。只有象伯昏無人那樣,達到“上窺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凝神從容的地步,才是真正高超的境界,是世俗之人無法企及的境界。
作者以高度的夸張,精湛的比喻、正繪反摹,盡情渲染伯昏我人的超脫,特別寫他“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的場面,尤其驚心動魄,具有很強的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