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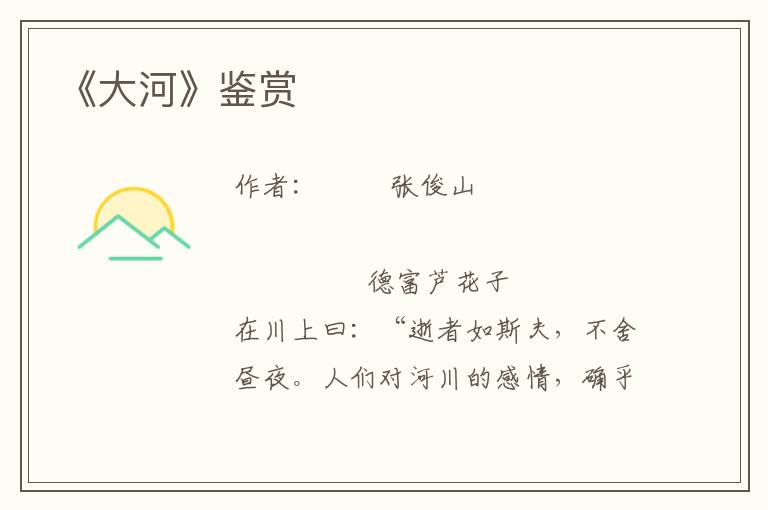
作者: 張俊山
德富蘆花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人們對河川的感情,確乎盡為這兩句話所道破。詩人千百言,終不及夫子這句口頭語。
海確乎寬大,寂靜時如慈母的胸懷。一旦震怒,令人想起上帝的怒氣。然而,“大江日夜流”的氣勢和意味,在海里卻是見不著的。
不妨站在一條大河的岸邊,看一看那泱泱的河水,無聲無息,靜靜地,無限流淌的情景吧。“逝者如斯夫”,想想那從億萬年之前一直到億萬年之后,源源不絕,永遠奔流的河水吧。啊,白帆眼見著駛來了……從面前過去了……走遠了……望不見了。所謂的羅馬大帝國不是這樣流過的嗎?啊,竹葉飄來了,倏忽一閃,早已望不見了。亞歷山大,拿破侖翁,盡皆如此。他們今何在哉。溶溶流淌著的唯有這河水。
我想,站在大河之畔,要比站在大海之濱更能感受到“永遠”二字的涵義。
(陳德文 譯)
面對無始無終、永續(xù)不絕的時間,人類一向懷著深刻的迷茫和困惑。因此,孔夫子才在“川上”發(fā)出了那聲千古喟嘆。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間如流水,“從億萬年之前一直到億萬年之后,源源不絕,永遠奔流”,德富蘆花也油然興起同樣的感懷。
這就是“時間”作為哲學之謎在不同時代的人們心中喚起的同樣思考。
是的,時間是永恒的。在這個日夜奔流的“永恒”中,世間的一切可以把捉的事物顯得多么短暫而微不足道!古代的羅馬大帝國可謂盛極一時,威震宇內(nèi)了,可是,在時間的長河里它也不過如過眼即逝的“白帆”和倏忽飄去的“竹葉”,“早已望不見了”。亞歷山大、拿破侖翁這樣的歷史人物,也曾叱咤風云,高高挺立于歷史舞臺,可是,“他們今何在哉”!時間就是這樣以它不可征服的“永恒”淘盡世間的一切,永不衰老,永不枯竭。人類一代一代地思考著這個不無神秘,無限深奧的“謎”,卻永遠解不開它的謎底:
我想,站在大河之畔,要比站在大海之濱更能感受到“永遠”二字的涵義。
如歷史上眾多的哲人一樣,德富蘆花也只能去“感受”永恒時間的涵義了。
作者興發(fā)于“泱泱的河水”,聯(lián)想到孔夫子的喟嘆,又以海洋的博大雄渾相比照,突現(xiàn)了“溶溶流淌著的”河水的象征意蘊。以這個“不舍晝夜”靜靜流淌的“河水”意象為情思奔瀉口,精鶩八極,神馳古今,拓開了曠遠幽深的意境,啟迪人們一起感受和思索,這就使作品獲得了詩意內(nèi)涵。
作品的語言是平樸的,并且始終保持著淡淡敘說的語調(diào)。但是,由于它有豐富的詩意內(nèi)蘊,所以仍然顯示出詩的質(zhì)性、詩的魅力。中國詩學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美學評判,那么《大河》作為散文詩,正是體現(xiàn)了自然而雋永的詩美品格。從這一點說,東方人的審美情趣確有共同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