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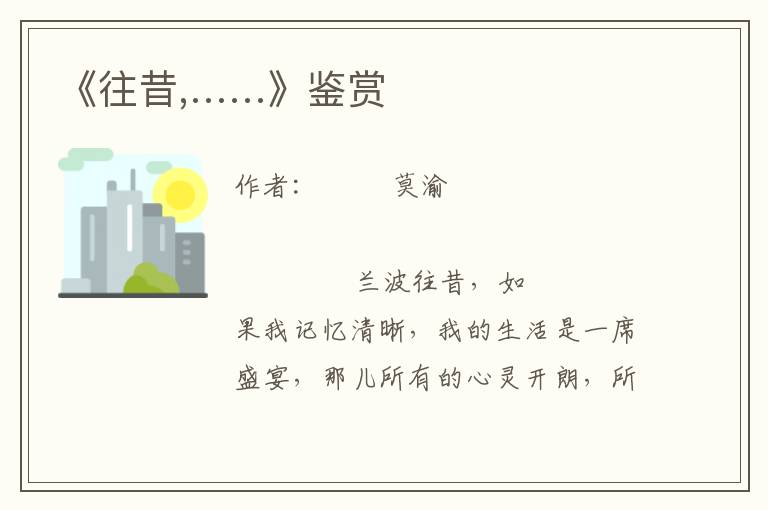
作者: 莫渝
蘭波
往昔,如果我記憶清晰,我的生活是一席盛宴,那兒所有的心靈開朗,所有的醇酒傾溢。
某個黃昏,我讓“美”置于膝上。——我發覺它面露愁苦。——于是我唾棄它。
我全神戒備的反抗正義。
我逃亡。女巫啊,痛楚啊,憎恨啊,我曾把財富信托你們!
我曾將一切人間希望自心中消隱。為了扼死歡樂,我像猛獸般悶聲奔躍。
我呼喚劊子手們,以便啃噬殆盡他們的槍枝。我呼喚巨禍,以便用砂用血窒息自己。痛苦是我的神祗。我身陷泥濘。我曝曬于罪惡之中。我裝瘋作傻。
而春天回報我癡人之楞笑。
最近,我仿佛跌入失意谷中,我夢想尋回昔日盛宴之鑰,好再饕餮一番。
那枚鑰匙就是仁慈。——這念頭證明我在作夢!
“你恒是貪婪,……”以如此可愛嬰粟花替我加冕的的魔鬼呼叫著,“用所有你的欲望,自私及重大罪孽去贏得你的死期。”
啊!我承受太多了。然而,親愛的撒旦,求你別獰目視我,稍后,待我完成少許罪行之頃,你呀!熱愛于漠視描寫、漠視教條的作家的你,我贈你這幾頁見不得人的我的地獄手記。
(臺灣 莫渝 譯)
蘭波是法國19世紀中葉的詩人,作品少,約60首詩和50篇散文詩,本身的文學活動也短,從15歲到20歲(約1869—1874),短短五年的創作,勝過他人一生文學堆累。
《在地獄里一季》是他生前出版的第一部作品。1873年(詩人19歲)4月構思,7月完稿,10月出版,包括8篇或長或短的散文詩。美國文評家佛里(Wallace Fowlie)在論著《法國現代文學指引》內,比較紀德的《地糧》和韓波這冊小書,他說:“《地糧》是法國文學界第二次對十九世紀科學、市儈和國家所扮演的夸大狂角色之攻擊。第一次攻擊在1873年,由一位十九歲的少年蘭波首開其端,在其所著之《在地獄里一季》中,公然宣稱逃向非洲,與土人結合,才可以在原始情況中忘記宗教,道德和當時的市儈氣。”這段論評,可以指引出二書的血緣關系。紀德的《地糧》出版于1897年,兩年前,他正值26歲,動筆撰寫該書。如果沒有韓波此書的前導,紀德的《地糧》能否完成,似乎可堪置疑。另一方面,在文體上在行筆間,二者均有相同之處。
《往昔,……》是《在地獄里一季》的首篇,開宗明義的提示撰寫宗旨。這本小冊子是他的《地獄手記》,叛逆性甚強,不愿傳統教條束縛的韓波自謂他是“被打入地獄者”。
十九世紀的法國詩壇有三位詩人與地獄攀親。波德萊爾(1821—1867)肯定他的美學來自地獄,其女友被稱為“地獄嬌娃”;聶瓦(奈瓦爾,1808—1855)則學奧菲斯(希臘神話的音樂家)出入地獄,且達兩次(見其詩作《被遺棄者》),以便重生,蘭波則自我放逐于地獄中,完成此集。
在這篇開場白,他想及自己曾經在傳統下享有的風光、盛宴,如今覺悟了,他要拋棄“美”,反抗世俗所謂的正義,把一切人間的希望全從內心驅除、消失,拒絕歡樂,折磨自己,裝瘋作傻。
萬物蘇醒的春天,并沒有特別關照詩人,反而給予傻笑,因而,詩人在失意谷底,極盼回復往昔的盛況,他猜想只要仁慈些,就做得到。然而,同魔鬼打交道之后(被撒旦戴上嬰粟花環,回憶別的詩人頭戴桂冠),卻發現無法回到昔日盛況,于是乞求撒旦,愿意奉獻出見不得人(自謙)的地獄經驗。
本篇可以說是詩人同撒旦開始交往的剖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