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路》東方文學名著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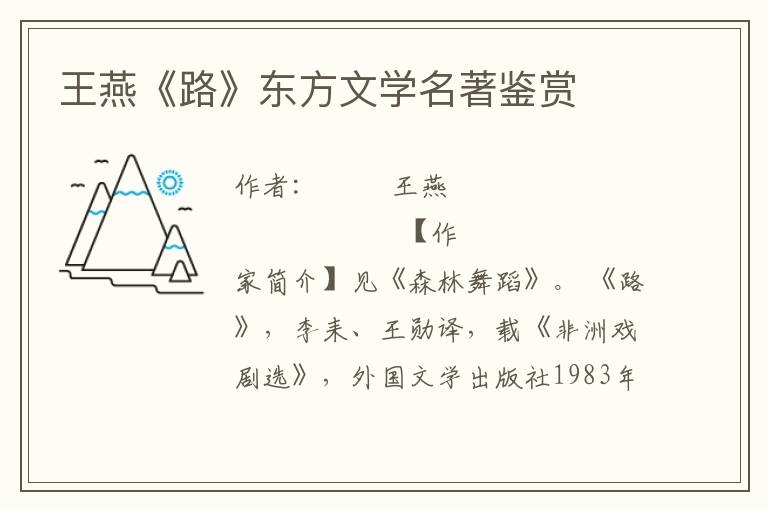
作者: 王燕
【作家簡介】見《森林舞蹈》。
《路》,李耒、王勛譯,載《非洲戲劇選》,外國文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
【內容提要】某日,晨曦初現,曙色朦朧,寄居在一爿掛著“車禍商店”招牌的棚屋中的幾個人相繼醒來(其中有汽車司機、售票員以及不明身份的游民),開始了各自的謀生活動。車禍商店的老板是個被人稱作“教授”的神秘老人,他當過主日學校的教師,還在教堂里當過祈禱儀式的主持人,而現今這個有著文學士和神學士多重頭銜的怪老頭卻一面銷售著得自于車毀人亡的汽車零件,另一方面還私下里出賣偽造的駕駛執照。每到夜幕降臨,他還時不時地出入于教堂墓地與亡靈為伍,借著畫符念咒賺死人的錢。
百無聊賴,司機薩魯比和售票員沙姆遜在房中戲擬著與“教授”對話,惡作劇中混亂了棚屋里舊有的陳設布局,以致于從車禍現場歸來的“教授”竟辨認不出自己的家來,反以為有鬼神附體或符咒作祟,勾引自己錯入于別人的宅邸。“教授”離去后,鎮長登堂入室,同綽號叫“東京油子”的流氓頭子作了一場骯臟的交易雇傭流氓團伙為其保鏢并充當鎮壓政敵的打手。緊接著,“東京油子”又用剛從鎮長處得到的海洛因封住了轄區警察那張“專愛找碴兒”的嘴巴。
工作復歸的“教授”總算找到了家門,便又執著地繼續著他經年累月努力從事著的尋找《圣經》啟示的工作。失業司機薩魯比闖進房來哀求“教授”為其偽造行車執照,因其言辭中提到了“自殺”而被“教授”斥之為褻瀆神明。“教授”的仆人穆拉諾每天出去采割棕櫚酒以滿足過往旅客的需求,但他的身世卻始終是個神秘的不解之謎。在科托奴的詢問下,“教授”言稱他是位被肇事車輛撞傷后棄之不顧的苦主,“教授”救助他恢復了健康,雖然事故后遺癥使之又聾又啞,但在“教授”眼中他卻是個道德高尚的圣徒和永恒真理的衛士。
司機科托奴突然決定不再開車了,究其原委,是恐懼車禍——他的父親死于車禍;好友“緬甸中士”不久前于事故中喪生;幾天前親眼目睹了一場車毀人亡的慘禍,更讓他寢食不安的是他曾在司機節撞人后逃之夭夭,而受害者的尸身卻神秘地消失了蹤跡,藏尸處只剩有一具奧貢神的假面頭飾。
“車禍商店”內外,眾人們跳起了假面舞,在“東京油子”和“教授”之間發生了沖突:
東京油子 別跳啦!別跳啦!(猛打他的一幫人)究竟誰是你們的主子?我叫你們別跳這種褻瀆神明的舞。
教授 (大聲吼叫)跳吧!
東京油子 太不像話!
教授 你太惹人注目了。坐下!
[鬼臉完全著了魔。東京油子看到這種情景,一個箭步奔到教授跟前,一把從他手中奪過葫蘆,向遠處的墻上擲去,撞個粉碎。
[鬼臉立刻停止舞蹈。片刻間他倆面對面站著,一動不動。突然他倆扭作一團,只聽他倆在竭力克制下相互摔撲扭打的氣喘聲。扭打之中,得到薩魯比援手的“東京油子”用匕首捅入了“教授”的背部,他本人則又被頭戴奧貢神假面的不明身份者摜倒在地。彌留之際,“教授”進行了最后一次布道:“但愿能像路一樣。……把生死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像路一樣呼吸吧,但愿能像大路一樣。”
“教授”在挽歌中死去,四周一片黑暗。
【作品鑒賞】寓意劇《路》作為索因卡角逐諾貝爾文學獎的主要入選作品,在他的創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向被推為其思想藝術成熟發展的重要標志。該劇作所表現的只是寄住在一爿路邊棚屋里的幾個人物不足一上午的群體活動。劇情圍繞著中心人物“教授”展開,最后以其被刺身死作結。
《路》劇不似一般劇作那樣具有密契整一、通貫始終的情節線索,亦缺少豐滿鮮明的常規式人物形象,比比皆是的隱喻和象征更造成一種撲朔迷離、朦朧神秘的氛圍,頗給人以荒誕奇幻的感受。然而,其間同時也寄寓著索因卡對社會及人生問題的認識,凝聚了劇作家對國家和民族前途的思考。劇作上演之際,已是尼日利亞國家獨立5年之后,其時,人們已從切盼改革的狂熱中漸次清醒冷靜過來,而新建的民族國家非但沒有走上繁榮發展的道路,反而暴露了深刻的社會危機——當政者恣肆妄為、營私舞弊;部族和黨派沖突日劇、紛爭不息;老百姓生活貧困、民怨鼎沸;國家則面臨著分崩離析,到處都散發出腐敗惡臭。這樣一幅污濁的社會畫面即是《路》劇藝術圖象的現實背景。
為了寄寓自己對未來的深刻焦慮并表現社會理想幻滅的主觀感受,索因卡以某些無生命、無知覺的客觀物象作為人類思維的具象對應和象征喻體,使之與特定的抽象理念潛在契合,收到了擴大描述范圍,拓展心靈視野的奇效。《路》劇中展示的“物”象征喻體主要有破爛卡車和崎嶇的公路。開篇伊始,劇作即將一輛“車身歪斜、輪子短缺”,“車身后部朝向觀眾的四輪卡車”呈示在人們的視線之下。其后,卡車這一象征性物象又在劇中反復顯現——有的部件殘缺,車身破損;有的零件不配套,勉強湊合為一體;有的看似新車,實為廢物上涂了一層油漆……正是這些隨時都會散架、一發動便軋軋作響的老爺車在“運窮光蛋”,“運麻瘋病人”,“載三等六樣的人,運各種各樣的貨”。這般踟躕顛躓在凸凹坑洼、溝壑林立的公路上,“散發著腐爛食品和各種垃圾的臭味”,隨時可能肇禍傾覆的破爛卡車,其情狀恰似當時的尼日利亞社會。
與卡車相比,劇中更為突出的象征性物象是公路——險惡崎嶇,坑洼不平;不時有人挖穴打洞,橫設障礙;橋梁早已糟朽,再也不堪承重負載——如此路象,不出車禍反倒奇怪。可是跑車的司機,雖處生死關頭卻依然漫不經心。他們不是對工作力弗能逮、無法勝任,便是貪杯醉酒,視自家和他人的生命為兒戲。在他們中間,無執照者有,失業停職者有,肇事后逃之夭夭者亦有,更有的干脆結成流氓團伙,為政客充當保鏢打手。另外,在路上還寄生了眾多吃白食的流浪漢,販毒品的白面客和專事“找碴兒”撈油水的巡警憲兵。概言之,路上的各色人等,無不掙扎在絕望的困境之中,而公路本身,則如同一條繼往開來的中介紐帶,其一端聯接著苦難深重的過往傳統,另一端維系著無可預卜的暗淡將來。同時,劇中的路還兼備著溝通生死兩界的功能和人類主宰神明的位格。科托奴——獲得過“安全準點行駛”獎勵的司機,剛剛從一場喪身斷橋之下的慘禍中幸免;早年間,其父正在跑車,“一輛卡車朝他背后開來,他的脊梁骨撞在一車臭魚干上”,老頭子就此離開了人世;幾天前,科托奴的好友,車禍商店原任伙計“緬甸中士”也因路遇事故而喪生。對亡父故友的追憶,尤其是自己死里逃生的驚懼,促使他決心離開公路,再不操持舊日的駕駛營生。從這個意義上看,“路”的確與死亡毗連,可視其為死亡的賡續。但是另一方面,恰是在這條路上,父親開風流車同女人造愛,使科托奴緣此獲得生命,故而,“路”又是生命的延伸。在劇中,約魯巴傳統信仰中的奧貢神不時顯現于路上,司機們為得神明庇祐,便在驅車行駛時追軋路上的野狗,將其骨血獻祭奧貢以求取自體性命不受戕害。在索因卡筆下,鐵神暨戰神的奧貢更被賦以“路”之主宰的屬性。雖然索因卡創作《路》劇的直接動因或許確系有感于尼日利亞國家公路上頻頻發生的交通事故,但在更深層次上審度,“路”之物象亦是連結神界與人世的喻意性通道——既導向毀滅和死亡,也接引著創造和新生。索因卡以上述“物”象征手法,對尼日利亞當代現實進行了哈哈鏡式的折映,用犀利的筆觸昭示了對國家命運所作的理性沉思:路通向無路可走的絕望境界,車也隨時可能翻下深溝,前景暗淡,前途難卜。
在角色設計方面,索因卡一反傳統寫實劇的典型化塑造方法,不去運用早已約定俗成的流行語匯作突出個性特征的勾勒描摹,而是另辟蹊徑,對人物角色加以抽象化和原型化處理,或是抹煞其固有的本體特征(年齡、身世、體態、性格),或是剝離其生存的具體時空條件(民族、地域、時代、社會),使之成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某種人類命運,負載某種哲理精神的符號化了的“類”象征人物。在劇作所出無多的人物中,“教授”是個核心角色。他白天在店堂里給司機們偽造行車執照,夜晚則到教堂墓地去交鬼通靈,一俟車禍發生,他便急切切趕奔現場勘察,意欲從那血肉模糊的尸身和支離破碎的車骸上尋覓象征人生真諦的所謂“圣經”啟示。有的時候,他還故意挪移標牌號志,人為地制造災禍以探求死亡的奧秘。從其身份、行為判斷,“教授”這一形象決非西方觀念的產物,將其視作西非巫術信仰的人格具象更為恰當。同多數非洲部族一樣,約魯巴人對于把宇宙精神同人的特征加以類化,將人的命運及行為與自然現象混同認知存在著特殊的興趣。故而,崇尚神秘性信仰的心理積淀便藉助于異常豐富的具象聯想,對自然秩序、生命現象作出了種種非理性的詮釋。巫術便是這種詮釋的過程,此一過程要由所謂巫覡——超自然力量的代理人——施行。非洲的巫覡一般在夜間活動,他們設法使其犧牲者生病、瘋狂,并在祭典儀式上以死者的肉體獻祭。《路》劇中這位以“同死人打交道”為己任的“教授”身上,對應性地集中著非洲巫覡的諸多習性,“他同鬼魂閑談,他同森林之神共進餐”,此一角色確系崇尚巫術這一約魯巴文化精神的人格象征。
為了強化象征效果,索因卡有意淡化人物的本體特征,戲劇角色不僅在動作、行為方面失卻了常態,不少人物還被抽取了具體稱謂而冠之以“東京油子”、“緬甸中士”、“流浪漢”、“戴假面具的人”一類抽象代碼,就連中心人物也僅以綽號“教授”稱之,始終沒曾賦以其稍規范些的指代符號。至于沙姆遜、科托奴們的稱謂,也僅為劇作提供了表層意象的結構素和情節元,其內在意蘊的趨向仍在于把握人類心魂的本質屬性和觀照人類命運的哲理性涵容。
《路》劇的形式構成亦很有特色。索因卡創造性地將大量歌曲插入劇中,觀其類式,獨唱、合唱兼而有之,頌歌、挽歌、舞樂、喪樂一應俱全;就內容而言,宗教贊詠、乞食小調、淫辭蕩曲參差雜陳。這些歌曲或長或短,漸弱漸強,貫穿全劇,直至終局。以歌入戲,不但固化著原本松散的情節結構,還起到了凈化情感、加強接受者心理共鳴的作用。
概而言之,寓意劇《路》以其哲理化與藝術化高度整一,文化精神與戲劇精神完美融合的總體特征,以其獨具特色的形式風格得到了世界性的認同。劇作家所致力于開創既立足于現代生活,具有20世紀時代意識,又不失卻尼日利亞鄉土氣息與民族性格的新型戲劇的藝術追求,也于此間得到了進一步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