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的訪問》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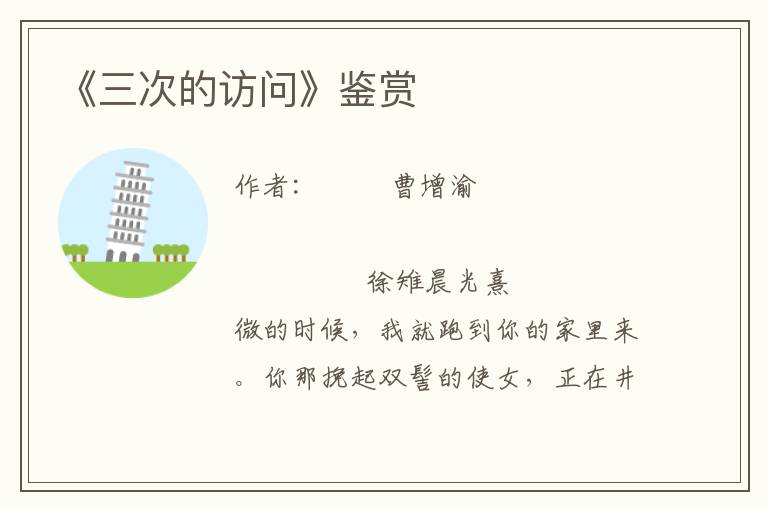
作者: 曹增渝
徐雉
晨光熹微的時候,我就跑到你的家里來。你那挽起雙髻的使女,正在井邊汲水,她把水桶放在井欄旁,低聲地對我說:“姑娘尚酣睡未醒呢。”但我明明聽見你在作晨禱,頌贊的歌聲悠揚地起于內室的門里,而與林鳥相應和,于是我知道你是不肯見我。
太陽正當日中時,我又跑到你的家里來。你的弟弟正在庭中嬉戲,他告訴我,說你上學去了,還沒有回來。但我明明看見你的書包歪斜地橫在紅木的方幾上,院門外又停著一輛駕著寶馬的香車。于是我知道你是不肯見我。
在黃昏的沉默里,我又提著紙糊的燈籠走來。將借蠟炬的明光的照耀,仔細辨認你淑美的臉兒。誰知道你家的大門又緊閉著,一個倦眼蒙眬的守門人開門出來說道:“她已睡了。”但我抬頭望你臥房的樓窗,明明瞧見一盞手照燈擺在靠窗口的八仙桌上;而且在搖搖欲滅的燈光里,我還隱約看得見你時隱時現的嬌小的面龐,和憧憧往來的人影。于是我知道你是不肯見我。
抒情主人公三次去找自己的心上人,然而那姑娘每一次都通過家里的人以某種借口將其拒之門外。主人公得悉真情,只好一遍又一遍地悲嘆:“于是我知道你是不肯見我。”
整個故事就這么簡單,我們甚至可以將其看作是同一個故事在不同情景中的三次重復。如果據此寫成小說,一定乏味得令人難以卒讀,因為它沒有提供任何可以索解的前因后果,構不成任何有意義的情節。然而,用散文詩的形式、散文詩的語言來講這個故事,效果就截然不同了。由于散文詩所引起的特定的閱讀期待,我們不會在這里尋找因果關系和人物性格,而是專注地沉浸在作者所描述的情景中,悉心地體味著那種無可奈何的失落感和惆悵落寞的情懷,同時生發出各種各樣的聯想。
這是一種一廂情愿且連連受挫的追求。那位意中人雖未正面出場,但她那與林鳥相應和的晨禱,她剛剛背過的書包和坐過的香車寶馬,特別是她在燈光里時隱時現的嬌小的面龐,都影影綽綽地勾畫出了一副逗人憐愛的形象。至于她的可望而不可即,則更令人生出一種虛無縹緲的感覺,進一步強化了審美效應。
明顯的虛擬性是這故事的另一個特點。早中晚的三次重復仿佛是一種象征,一種傳奇,作品中的種種描繪也確定很少給我們以可以信賴可以把握的現實感。但這種“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心緒反而因之凸現出來。這也許正是作者命意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