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宮詞》辨證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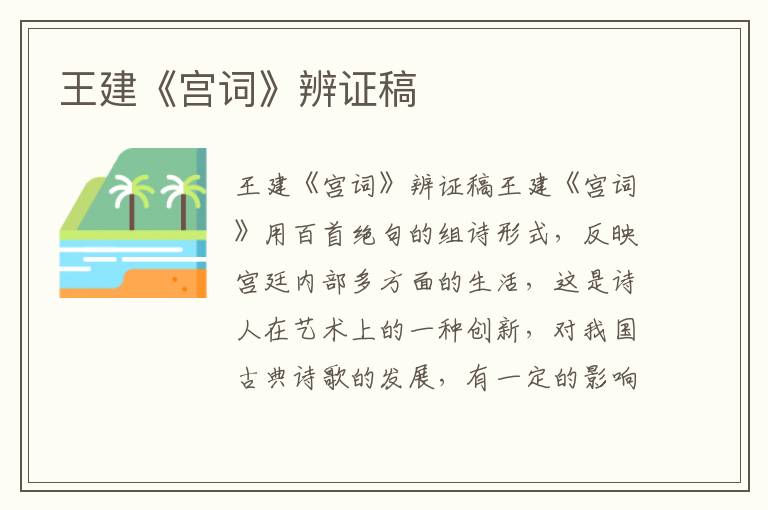
王建《宮詞》辨證稿
王建《宮詞》用百首絕句的組詩形式,反映宮廷內(nèi)部多方面的生活,這是詩人在藝術上的一種創(chuàng)新,對我國古典詩歌的發(fā)展,有一定的影響。后代效學王建,寫作百首《宮詞》的人很多,如蜀之花蕊夫人,宋之王珪等。
王建《宮詞》有一百首,早見之于宋人的記載。歐陽修《六一詩話》:“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宮禁中事。”司馬光《溫公續(xù)詩話》、李頎《古今詩話》、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十七并云:“元豐初,王紳效王建作《宮詞》一百首。”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十引《后山詩話》云:“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事后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六引《唐王建宮詞舊跋》:“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效此者雖有數(shù)家,而建為之祖耳!”
可是,王建《宮詞》在流傳過程中,出于多種原因,散失了其中的部分詩篇。后人為了補百首之不足,謬以他人的作品鈔錄入內(nèi),造成了王建《宮詞》真?zhèn)坞s陳的混亂現(xiàn)象,很有必要加以甄辨。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王建詩集》卷十《宮詞》(以下簡稱中華本王建《宮詞》),編者于七首詩下附注:“胡本注一作某某”,于一首詩下附注:“《全唐詩》一作某某。”其說未為完備。筆者因酌加考訂,作《王建〈宮詞〉辨證稿》,具體說明那些詩是雜入王建《宮詞》中的他人作品,那些詩是應該補入百首《宮詞》中的王建詩。
第一 雜入篇辨
(一)
最先提出王建《宮詞》中雜入他人作品的,是宋人胡仔,他在《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十四中說:
予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膾炙者數(shù)詞而已。其間雜入他人之詞,如“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一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系臂紗。”又如“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此并杜牧之作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此白樂天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詩也。
胡氏指出的這些詩,在中華本王建《宮詞》中,分別為第一百首,第八十八首,第九十五首,第九十九首。編者分別加上如下的校語:“胡本注一作杜牧”、“胡本注一作杜牧”、“胡本注一作白居易”、“胡本注一作王昌齡。”
這些重出詩,確是杜牧、白居易、王昌齡詩被誤錄入王建百首《宮詞》中。
“閑吹玉殿昭華管”一首,是杜牧《出宮人二首》中的第一首,見于《樊川詩集》卷二。《樊川詩集》四卷,是杜牧外甥裴延翰親自編集的。王建生活的時代,比杜、裴兩位要早得多,他的百首《宮詞》早在社會上流傳。因此,裴延翰還不致于把王建《宮詞》中的詩,誤收入舅父的詩集中去。相反,恰恰是后人不明真假,誤把杜牧詩錄入王建百首《宮詞》中去;何況,這首詩又正好排列在南宋陳解元書籍鋪刻本王建《宮詞》一百首的最后一首,補綴的痕跡更為明顯。
和胡仔的看法一樣,宋趙與時《賓退錄》卷一、明朱承爵《存余堂詩話》都指出“閑吹玉殿昭華管”一詩是杜牧的作品。毛晉《三家宮詞》的跋語,也說這首詩是“杜牧之《出宮人》之一也。”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嘉靖本、萬歷本,也都把這首詩收入王建百首《宮詞》中。《全唐詩》編者吸取了諸家的意見,把這首詩摒于王建《宮詞》之外,這樣處理是正確的。
“銀燭秋光冷畫屏”一詩,見于《樊川外集》,題為《秋夕》。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此一詩,杜牧之、王建集中皆有之,不知其誰之作?以余觀之,當是建詩耳。蓋二子之詩,其清婉大略相似,而牧多險側(cè),建多平麗,此詩蓋清而平者也。”周氏僅從風格而言,以為“銀燭秋光冷畫屏”一詩是王建所作,似乎還缺乏說服力。
其實,古往今來,有許多人明確指出過這首詩是杜牧的作品。宋洪邁《萬首唐人絕句》于王建《宮詞》中未載此詩,卻系之于杜牧名下。宋趙與時《賓退錄》卷一辨王建《宮詞》雜有他人詩時,就提到這首詩。明朱承爵《存余堂詩話》說:“王建《宮詞》一百首,蜀本所刻者得九十二,遺其八。近世所傳者百首俱備,蓋好事者妄以他人詩補入,殊以亂真。中有‘銀燭秋光冷畫屏’(下略),此牧之《七夕》詩也。”毛晉也說:“余閱王建《宮詞》,輒雜以他人詩句,如‘銀燭秋光冷畫屏(略)’,此牧之《秋夕》詩也。宋南渡后,逸其真作,好事者摭拾以補之。”(見毛晉《三家宮詞》跋語)近人浦江清先生也說:“杜牧《秋夕》詩,南宋時曾闌入王建《宮詞》中。”(見《浦江清文錄·花蕊夫人宮詞考證》)這首詩,確是應該把它排除在王建百首《宮詞》之外的。
“淚滿羅巾夢不成”一首,原載《白氏長慶集》第十八卷,題名為《后宮詞》。按,白居易《白氏文集自記》:“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之序。”朱彝尊《白香山詩集序》:“詩家好名未有過于唐白傅者,既屬其友元微之排纘《長慶集》矣,而又自編后集,為之序,復為之記。”則《白氏長慶集》五十卷,在白居易生前就由他的好友元微之編序的,《后宮詞》一詩,早已被編纂入集,自然不會有差錯。再則,這首詩被宋人洪邁收入《萬首唐人絕句》的白居易名下,題名為《宮詞》,卻并未收入王建百首《宮詞》中。《全唐詩》收錄白居易的《后宮詞》,并沒有將這首詩收入王建《宮詞》中。除上數(shù)證外,尚有趙與時、朱承爵、毛晉等人,分別在《賓退錄》卷一、《存余堂詩話》、《三家宮詞》跋語中,分別指出“淚滿羅巾夢不成”為白居易詩,誤入王建《宮詞》中。
“寶仗平明金殿開”一首,本是王昌齡的作品,早已見之于唐人所選的唐詩中,不過詩題和文字略有不同罷了。殷璠《河岳英靈集》卷中收錄王昌齡這首詩,題名為《長信宮》,前半首作:“奉帚平明秋殿開,暫將團扇共徘徊”,后半首全同。韋莊《又玄集》卷上亦錄王昌齡《長信宮秋詞》,文字與殷璠《河岳英靈集》除“秋殿”作“金殿”外基本相同。韋縠《才調(diào)集》卷八也收錄王昌齡《長信愁》,文字大體同《河岳英靈集》(惟“秋殿”作“金殿”,“暫將”作“且將”)。此外,宋以后人(如趙與時、朱承爵、毛晉等),不斷指出這首詩是王昌齡的作品。誤把這首詩編入王建《宮詞》中者,乃“不讀詩”!
總之,胡仔是有鑒別力的,他指出的四首,確是應該把它們從王建《宮詞》中剔除出去,洪邁、《全唐詩》編者的做法,尊重客觀事實,很好。
(二)
除了上述四首外,宋趙與時還指出另外四首雜入王建《宮詞》中的他人詩,《賓退錄》卷一云: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入,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猶肥,白日君王在內(nèi)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弦索初張調(diào)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nèi)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薰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盡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
趙與時所指出的這四首詩,中華本王建《宮詞》分別為第九十六首、第九十七首、第九十三首,第九十四首。第九十六、九十七兩首,詩下無注,可見南宋陳解元書籍鋪刻本、席氏《唐百家詩》本、胡氏本《王建詩集》都以為這兩首詩是王建所作。中華本王建《宮詞》僅于第九十三首下附注:“胡本注一作樂府《銅雀臺歌》”,第九十四首詩下附注:“同上”。
這四首詩,確系張籍、劉禹錫詩誤入王建《宮詞》中的。
趙與時的世次,后于洪邁,《賓退錄》所述,或即自洪邁《萬首唐人絕句》中來。因為洪邁沒有把這四首詩收入王建《宮詞》中,卻分別錄入張籍、劉禹錫名下,傳世的嘉靖本、萬歷本《萬首唐人絕句》可以證明這一點。
“新鷹初放兔猶肥”、“黃金捍撥紫檀槽”兩詩,《續(xù)古逸叢書》影宋本《張文昌文集》卷三載,題為《宮詞》二首,文字與中華本王建《宮詞》全同。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張司業(yè)詩集》卷六,亦載《宮詞》二首,然僅存“新鷹初放兔猶肥”一首,漏刻一首。毛晉《三家宮詞》刪去這兩首詩,并在跋語中云:“此皆張文昌宮詞也。”朱承爵《存余堂詩話》同此。《全唐詩》卷三百八十六張籍名下,收錄《宮詞》兩首,與此同。詩下,編者并未注明“一作某某”。同書卷三○二王建百首《宮詞》中,并沒有收錄這兩首詩。可見,《全唐詩》編者曾根據(jù)舊籍對這兩首詩作過鑒別的。
“日晚長秋簾外報”,“日映西陵松柏枝”兩詩,四部叢刊影印董氏影宋本(即日本崇蘭館藏宋刻本)《劉夢得文集》卷八“樂府”詩欄收錄之,題為《魏宮詞二首》。從詩意看,“望陵歌舞”、“憶得分時”、“日映西陵”、“下臺相顧”,確實都是詠魏銅雀臺事,這與王建百首《宮詞》“專言唐宮禁中事”的主題相背悖,顯然這是劉禹錫詩混入王建《宮詞》中去的。
這兩首誤入詩,明朱承爵也曾指出過,毛晉《三家宮詞》也沒有收它們,并指出這是劉禹錫詩。《全唐詩》也把它們剔除在外。計有功的《唐詩紀事》已把這兩首詩收入王建《宮詞》中,可見它們被混入的時間應早在北宋時代。
(三)
王建《宮詞》第九十八首:“鴛鴦瓦上瞥然聲,晝寢宮娥夢里驚。元是我皇金彈子,海棠花下打流鶯。”中華本于詩下附注:“胡本注一作花蕊失人。”
這首詩,早已混入王建《宮詞》中,計有功《唐詩紀事》列此詩于王建《宮詞》第九十八首,《全唐詩話》亦收錄這首詩于王建名下。清胡谷園刊本《王建詩集》的附注,是根據(jù)毛晉輯花蕊夫人《宮詞》第九十五首的附注:“此首或見王建集中”。然而,他本均無此詩。奇怪的是,毛晉《三家宮詞》中的王建《宮詞》里,卻并沒有這一首。嘉靖本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原無此詩,而黃習遠補竄的萬歷本《萬首唐人絕句》,于王建百首《宮詞》中,卻刪去“畫作天河”一詩,補上“鴛鴦瓦上”一詩,則已非洪邁的舊觀。由此可見,前人對這一首詩是否是王建詩有不同看法。
楊慎《詞品》卷二“李珣”條:“其妹事王衍為昭儀,亦有詞藻,有‘鴛鴦瓦上忽然聲’詞一首,誤入花蕊夫人集。”他又在《升庵全集》卷五十七中說:“好事者妄取唐人絕句補入之,‘鴛鴦瓦上忽然聲’,花蕊夫人詩也。”
浦江清先生對這首詩有過詳細的考證,云:“按:趙與時《賓退錄》謂當時人刻王建《宮詞》者,往往得九十首,而以他詩十首足之,內(nèi)八首可辨明作者,余二不明來歷,其一即‘鴛鴦瓦上忽然聲’也。可知此首之入王建《宮詞》自南宋已然。楊慎《詞品》以為蜀昭儀李舜弦作,不知何據(jù)?洪邁《萬首絕句》錄李舜弦詩,無此首。《全唐詩》又以之屬于李玉簫,亦不知何所據(jù)。李調(diào)元《全五代詞》從之。若是舜弦、玉簫,則皆前蜀時人,雖以之入宣華宮詞,亦無不可。”(見《浦江清文錄·花蕊夫人宮詞考證》)又云:“宣華苑內(nèi),如李舜弦、李玉簫皆通文墨,今九十八首之外,尚有‘鴛鴦瓦上瞥然聲’一首,相傳為李玉簫或李舜弦作,不知何據(jù)?倘真是李作,則竟入之花蕊《宮詞》中可矣,前人所以除外者,以李為前蜀,花蕊在孟蜀耳。”(同上)
據(jù)此數(shù)說,可知“鴛鴦瓦上”一詩,既不是王建的,也不是花蕊夫人的,為宣華宮內(nèi)李舜弦或李玉簫作。
(四)
王建《宮詞》第七首:“延英引對碧衣郎,江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考試,宮人手里過茶湯。”中華本于詩下附注:“《全唐詩》注:一作元稹詩。”計有功《唐詩紀事》于此詩下附注:“此詩亦云元稹作”。則《全唐詩》注,即據(jù)《唐詩紀事》注。按《全唐詩》卷四百二十三元稹名下確實收錄這首詩,題為《自述》,題下注:“一作王建宮詞。”
這首詩當是王建百首《宮詞》中的一首,后人誤以為元稹詩。
大量的前人記載,都證明這首詩是王建作品。姚寬《西溪叢語》卷下載王建這首詩,并云:“恐是用紅絲硯,江南李氏時猶重之。”洪邁《萬首唐人絕句》亦列此詩于王建《宮詞》第七首。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十四云:“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于其間,予以《元氏長慶集》檢尋,卻無之,或者之言誤也。”胡仔這段話,很值得注意,說明宋代的《元氏長慶集》中并沒有《自述》一詩,他用實證駁斥了“或者之言”。
“亦云元稹作”一說,源于范攄《云溪友議》卷十,然而,《云溪友議》這一段記載,紕漏百出,糾葛不清,茲摘其有關部分于下:
“王建校書為渭南尉,作《宮詞》。元丞相亦有此句,河南、渭南,合成二首。”“元公秀明經(jīng),制策入仕(雙行夾注:秀字紫芝,為魯山令,政有能明,顏真卿為碑文,號曰元魯山也。)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對綠衣郎,紅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里過茶湯’是時貴族競應制科,因為男子榮進,莫若茲矣,乃出自河南之詠也。”
這一段話文意不明。“河南、渭南,合成二首”不知所云。下敘“元公”,不知何人?是元稹,抑是元秀(元德秀)?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明經(jīng)擢第,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則這段文字,似乎是說元稹。但是,元稹沒有別名曰“秀”,制策之前,已仕校書郎,怎說是“制策入仕”?元稹別無字“紫芝”,也未做過“魯山令”。相反,這段文字與元德秀的名號、貫籍、官職相合,《顏魯公集》卷三十有《元德秀碑》:“唐元魯山墓碣,監(jiān)察御史李華撰,太子太師顏真卿書,院(四部備要本注:“缺二字”,疑在“院”上為翰林二字。)學士李陽冰篆額。魯山名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嘗為魯山令。”范攄把元稹、元德秀混為一談,又把王建《宮詞》誤以為元稹作,證之宋人的載述,可知這種小說家言,不足征信。
第二 補入篇證
綜上所述,中華本王建百首《宮詞》中,有九首是他人詩混入的,即第八十八首,本為杜牧《秋夕》,第九十三首、第九十四首,本為劉禹錫《魏宮詞》,第九十五首,本為白居易《后宮詞》,第九十六首、第九十七首,本為張籍的《宮詞》,第九十八首,本為李弦華或李玉簫《宮詞》,第九十九首,本為王昌齡《長信秋詞》,第一○○首,本為杜牧《出宮人二首》之一。
既然王建《宮詞》歷來以百首傳誦,那末,缺佚的九首,是否還傳世?關于這個問題,前人是作過努力的,現(xiàn)在把他們的說法和做法,擺出來,再作綜合分析。
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嘉靖本)補入十首:
“忽地金輿”、“畫作天河”、“春來睡困”、“彈棋玉指”、“宛轉(zhuǎn)黃金”、“供御香方”、“藥童食后”、“步行送入”、“縑羅不著”、“后宮宮女”。萬歷本刪去“畫作天河”、“后宮宮女”。
趙與時《賓退錄》卷八云: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知不廣,蓋建自有《宮詞》百篇。……所逸十篇,今見于洪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畫作天河”、“春來睡困”、“紅燈睡里”、“蜂須蟬翅”、“教遍宮娥”(企按,這三首當是王建作。朱承爵《存余堂詞話》云:“近讀趙與時《賓退錄》,其所述建遺詩七首,”朱氏已把這三首剔除在外。)“彈棋玉指”、“宛轉(zhuǎn)黃金”、“供御香方”、“藥童食后”。
楊慎《升庵全集》卷五十七云:
王建《宮詞》一百首,至宋南渡后,失其七首,好事者妄取唐人絕句補入之。……余在滇南見一古本,七首特全,今錄于左:“忽地金輿向月坡”、“畫作天河刻作牛”、“春來睡困不梳頭”、“彈棋玉指兩參差”、“宛轉(zhuǎn)黃金白柄長”、“供御香方加減頻”、“藥童食后進云漿。”(按:楊氏錄出全部詩作,為節(jié)省篇幅,這里僅引首句。)
毛晉《三家宮詞》跋語:
“宋南渡后,逸其真作,好事者摭拾以補之,今余歷參古本,百篇俱在,他作一一刪去。”
毛晉在王建《宮詞》中補入的篇目是:“忽地金輿”、“春來睡困”、“步行送入”、“縑羅不著”、“彈棋玉指”、“宛轉(zhuǎn)黃金”、“畫作天河”、“供御香方”、“藥童食后。”《全唐詩》補入十篇:
“忽地金輿”、“畫作天河”、“春來睡困”、“步行送入”、“縑羅不著”、“彈棋玉指”、“后宮宮女”、“宛轉(zhuǎn)黃金”、“供御香方”、“藥童食后”。
以洪邁、趙與時、朱承爵、楊升庵、毛晉、《全唐詩》六家之說統(tǒng)計,補入篇目被錄用的次數(shù)是:“忽地金輿”六次,“畫作天河”六次,“春來睡困”六次,“彈棋玉指”六次,“宛轉(zhuǎn)黃金”六次,“供御香方”六次,“藥童食后”六次,“步行送出”三次,“縑羅不著”三次,“后宮宮女”二次。
綜觀宋代流傳的王建《宮詞》各種版本,顯然有兩大類:一個是已經(jīng)混入他人作品的系統(tǒng)(簡稱紀事本系統(tǒng)),計有功《唐詩紀事》和南宋陳解元書籍鋪刊《王建詩集》卷十所收的王建《宮詞》,代表了這個系統(tǒng)的面貌。另一個是保留著原貌的系統(tǒng)(簡稱洪邁本系統(tǒng)),洪邁曾見到過這個系統(tǒng)的版本,因而據(jù)以錄入《萬首唐人絕句》,同時人吳曾也見到過,《能改齋漫錄》大量征引王建《宮詞》,就是根據(jù)這個系統(tǒng)的本子。
筆者認為洪邁本系統(tǒng)的王建《宮詞》是比較接近原貌的,理由有以下三點:
一 紀事本系統(tǒng)內(nèi)混入的九首詩,都能在他人集子中找到,朱承爵在《存余堂詩話》中說:“前所贗足者,每每見于諸人集。”所見極是。本文前面已作辨證。而洪邁本系統(tǒng)補入的詩篇,只有“后宮宮女無多少,盡向園中哭一團。舞蝶落花相覓著,春風共語亦應難。”一首,見于毛晉《三家宮詞》中的徽宗《宮詞》內(nèi),當是宋徽宗趙佶的作品。其余九首,均未見與他人詩重出。
二 洪邁本系統(tǒng)的補入詩,在宋元人的筆記中曾經(jīng)被征引過,如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教坊內(nèi)人”條云:“‘忽看金輿向月陂,宮人接著便相隨。恰從中尉門前過,當處教看臥鴨池’,王建《宮詞》也。”文字與《萬首唐人絕句》略有異同。又,同書卷六“雙陸”條云:“王建《宮詞》‘分明同坐賭櫻桃,攸(證之別本,當是收字)卻投壺玉腕勞。各把沈香雙陸子,局中門疊阿誰高。’”周密《齊東野語》:“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縑羅不著愛輕容’”。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十二:“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恩赦得還家。’”吳、周、陶三人確是根據(jù)當時他們所能看到的王建《宮詞》征引的。尤可注意的是,吳曾《能改齋漫錄》成書時間在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到二十七年之間(1154—1157),而洪邁的《萬首唐人絕句》成書時間在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吳書早于洪書三十多年,絕不會鈔錄洪邁的《萬首唐人絕句》,恰恰相反,這個事實正好證明在洪邁以前就有比較接近原貌的王建《宮詞》的版本傳世。吳曾是見到的,洪邁也是見到的。朱承爵說:“文敏所得,又不知其何所自也。”(《存余堂詩話》語)他還不明白其中的奧妙。因此,把這些詩補入到王建百首《宮詞》中去,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三 從詩歌的藝術風格、反映唐代宮廷生活的主題等角度看,洪邁本系統(tǒng)的補入詩,是比較接近王建原作的。王建《宮詞》常常寫到唐宮廷內(nèi)具體的殿名、地名,各類游戲和宮女的生活,補入詩也寫到“月陂”、“臥鴨池”、“乞巧樓”、“簸錢”、“彈棋”、“染退紅”、調(diào)配“香方”等等,和其他詩作比較一致。王建《宮詞》偶有構思靈巧的地方,如“樹頭樹底覓殘紅”一首,曾得到王安石的賞識(見陳輔《陳輔之詩話》)。但是,總的看來,它們?nèi)鄙俳^句詩的風韻,稍嫌質(zhì)直。補入詩也是如此,記事寫景,情思不足,少一點兒詩味。
《王建〈宮詞〉辨證稿》即將完篇的時候,我重復一遍:紀事本、陳解元書籍鋪刻本、中華本等《王建<宮詞>一百首》,其中九首是他人詩混入的,理當剔除;洪邁《萬首唐人絕句》、毛晉《三家宮詞》等補入的九首詩,比較接近原貌,可以抵上被剔除的九首,仍合王建《宮詞》一百首之數(sh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