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乍起·朋友是一曲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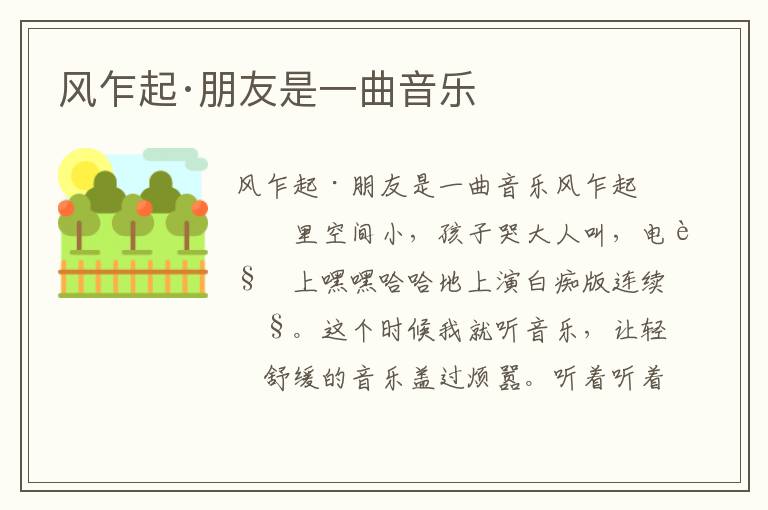
風乍起·朋友是一曲音樂
風乍起
家里空間小,孩子哭大人叫,電視上嘿嘿哈哈地上演白癡版連續劇。這個時候我就聽音樂,讓輕柔舒緩的音樂蓋過煩囂。
聽著聽著就走神兒,我拿起手機來看。上面存著幾天前的短信,朋友發來的,無非兩句淡話:“起床了,看見陽光了,熱。”心里漾起久已不見的溫暖。
從小到大,數得上來的朋友只有兩個。
初中一個,梳羊角辮,手拉手,公不離婆,槌不離鑼。我撒謊,她幫我圓謊,她抄襲,我幫她抄襲。有一次,我和家里鬧別扭,留張字條給她,想悄悄出走,她很快追出校門,披頭散發,衣服穿得亂七八糟,眼淚流得嘩嘩的……
當時想著要好一生一世,誰知道逐漸就淡了,十幾年后再相聚,已經是兩條路上的人了,除了黑白片兒一樣的回憶,仿佛再也找不到可以維系友情的線索。
晚上做夢,卻還能夢見她,還是當年梳羊角辮的那個……
第二個朋友,是遭受大難之后相識的。
那年,我忽然生了一場大病,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成天在心里罵:“真他媽的!”一個親戚出國,把一臺舊電腦送給我,結果失重的我一頭就栽進了網絡。
這是一片黑海,一個黑洞,不僅要吃掉我大把大把的光陰,還游著一個個鯊魚樣的男人。這個時候上帝緩緩降臨,手指一揮:“喏,賜你一個寶貝。”于是這個朋友來了。
如果不是他及時出現,恐怕我早墮落到生命不息,泡網不止,網戀無窮了。我后來就想,肯定是有神仙勸“孫悟空”:趕緊去救唐僧,去得遲些兒,就怕被妖精吃了!自從認識,他就像孫悟空,整天忙著搭救我,鼓勵我讀書,寫東西,不許我進聊天室,有時候我偷偷往聊天室跑,他一發現就拎出來痛罵:“幾乎失業了,還有閑心聊天?”
至今,我兩年寫了40萬字,稿費足夠養活我自己乃至全家,都是被他罵出來的。失業引起的焦慮大大減輕,輕到幾乎沒有,而我的病漸漸好轉,愈發自信。
我也一路陪他走過艱難的兩年半,一直走到他博士畢業。原想與子偕老的,我浪漫地幻想過,還寫了如此的文章發表,可是現在聯系越來越少,越來越少。以前,一天發的短信塞爆信箱,得不停地刪,現在一個星期的短信也不過短短三五條,越來越淡……也失落過,自問過為什么?后來感覺大家的前路都天寬地闊,逐漸明白,無論我對他還是他對我,就是朋友罷了,很好的朋友——其實,也夠了。
“我們在黑暗中摸索,絆倒在物體上,我們抓牢這些物體,相信它們便是我們所擁有的唯一的東西。光明來臨時,我們放松了所占有的東西,發覺它們不過是與我們相關的萬物之中的一部分而已。”泰戈爾的話多涼啊,原來他早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經歷過。
有時想,朋友就是一曲音樂,在滾滾紅塵為粱謀的時候,可以對市儈、庸俗、計較起一種適當有效的屏蔽,讓自己在生計之外的精神層面,有一個較為自由順暢的呼吸,如同菊花丘山之于陶五柳,鱸魚莼菜之于張季鷹。但音樂不是全部,朋友不能終老。一曲終了,該干什么還干什么。鐘子期死了,俞伯牙干脆把琴都摔了,這樣不好。風云際會固然可喜,無風無云的時候,還得學會彈一曲瑤琴,給自己聽。
可是天寬地闊,為什么一邊聽歌一邊寂寞,縱然看得開放得下,終究是欲舍難舍。朋友啊,就算我再也不知道你們現在何方,做著什么,有何種憂樂,可是你們的一顰一笑,一言一語,仍如楊花亂舞,點點都在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