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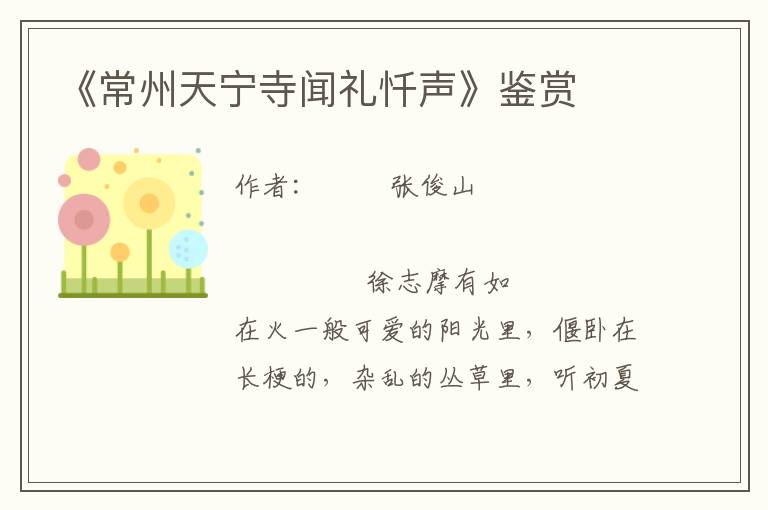
作者: 張俊山
徐志摩
有如在火一般可愛的陽光里,偃臥在長梗的,雜亂的叢草里,聽初夏第一聲的鷓鴣,從天邊直響入云中,從云中又回響到天邊;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里,月光溫柔的手指,輕輕的撫摩著一顆顆熱傷了的砂礫,在鵝絨般軟滑的熱帶的空氣里,聽一個駱駝的鈴聲,輕靈的,輕靈的,在遠處響著,近了,近了,又遠了……
有如在一個荒涼的山谷里,大膽的黃昏里,獨自臨照著陽光死去了的宇宙,野草與野樹默默的祈禱著,聽一個瞎子,手扶著一個幼童,噹的一響算命鑼,在這黑沉沉的世界里回響著;
有如在大海里的一塊礁石上,浪濤象猛虎般的狂撲著,天空緊緊的繃著黑云的厚幕,聽大海向那威赫著的風暴,低聲的,柔聲的,懺悔他一切的罪惡;
有如在喜馬拉雅的頂顛,聽天外的風,追趕著天外的云的急步聲,在無數雪亮的山谷間回響著;
有如在生命的舞臺的幕背,聽空虛的笑聲,厭世與自殺的高歌聲,在生命的舞臺上合奏著;
我聽著了天寧寺的禮懺聲!
這是那里來的神明?人間再沒有這樣的境界!
這鼓一聲,鐘一聲,磬一聲,木魚一聲,佛號一聲……樂音在大殿里,迂緩的,漫長的回蕩著,無數沖突的波流諧合了,無數相反的色彩凈化了,無數現世的高低消滅了……
這一聲佛號,一聲鐘,一聲鼓,一聲木魚,一聲磬,諧音磅礴在宇宙間——解開一小顆時間的埃塵,一收束了無量數世紀的因果;
這是那里來的大和諧——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籟,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動,一切的擾攘;
在天地的盡頭,在金漆的殿椽間,在佛像的眉宇間,在我的衣袖里,在耳鬢邊,在官感里,在心靈里,在夢里……
在夢里,這一瞥間的顯示,春天,白水,綠草,慈母溫軟的胸懷,是放鄉嗎?是故鄉嗎?
光明的翅羽,在天極中飛舞!
大圓覺底里流出的歡喜,在偉大的,莊嚴的,寂滅的,無疆的,和諧的靜定中實現了!
頌美呀,涅槃,贊美呀,涅槃!
“涅槃”是佛教宣示的最高生命境界。這種境界是教徒經過長期修道,終于覺悟到平等周滿,毫無缺漏的教義真諦(此即佛教所謂“圓覺”),從而實現脫離一切煩惱,進入自由無礙的精神天地的生命狀態。可以看出,徐志摩在這篇散文詩里傾力描繪的就是佛教的這種修煉境界。
作品是通過狀寫常州天寧寺的禮懺聲來展現涅架境界的。正當寺內佛事進行之際,從寺里傳出“鼓一聲,鐘一聲,磬一聲,木魚一聲,佛號一聲……”綿綿不絕,如夢如幻。那眾多的聲音在大殿里“迂緩的,漫長的回蕩著”,又“磅礴在宇宙間”,顯得無比和諧,宏大而彌漫。在聞者的聽覺中,這和諧的音響使“無數沖突的波流諧合了,無數相反的色彩凈化了,無數現世的高低消滅了……”,以至感到靈魂超脫肉體而升華,“大圓覺底里流出的歡喜,在偉大的,莊嚴的,寂滅的,無疆的,和諧的靜定中實現了!”詩人對于身臨的這種佛事境界可謂體察細微,參悟透徹。因此,可以說詩人此情此境,獲得了一次獨特的生命體驗。這種生命體驗無關世事凡俗,而是全身心投入的宗教情緒,所以他在詩篇結尾才那么忘情地“頌美”涅槃,“贊美”涅槃!
詩人在詩篇里表現出善于捕捉和表現感覺的才能,甚至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在這里,佛事的禮懺聲不僅僅是多種聲音的交混回響,而且被描繪為一種意境,那濃郁的宗教氛圍給人以浹肌淪髓的強烈感染,猶如身臨其間,油然興起皈依的向往。由于詩篇著意于渲染一種“境界”,所以開篇用六個段落對禮懺聲進行博喻。雖然每一個比喻都有獨特的意境呈現,但它們共通的境界效果卻是那種沉響的幽渺、悠遠和終如大音希聲般的寂寥。以這種博喻創造的氛圍最終統一于“天寧寺的禮懺聲”,這就為下文展開描繪涅槃境界鋪墊了韻味十足的張本。博喻來自宏富的想象,感覺依仗敏銳的神經,詩人就是以其藝術創造的奇才孕育了這篇彌滿宗教氣息的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