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華文文學(xué)的發(fā)展與繁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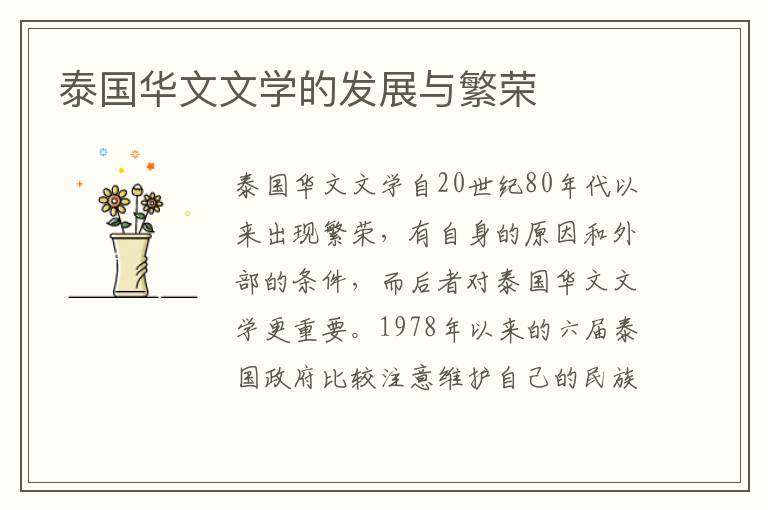
泰國華文文學(xué)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xiàn)繁榮,有自身的原因和外部的條件,而后者對泰國華文文學(xué)更重要。1978年以來的六屆泰國政府比較注意維護自己的民族利益,奉行了比較開明的內(nèi)外政策;國內(nèi)政治氣候漸趨寬松,對文藝創(chuàng)作特別是對華文報刊的限制減少;1990年又廢除了實行了22年的限制人民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十七條”,1992年3月又解除了限制華文教育的禁令,泰國漸漸出現(xiàn)了中文熱。
泰國國內(nèi)政策的這個變化和國際大環(huán)境以及中泰關(guān)系都有密切聯(lián)系。
冷戰(zhàn)之后,世界從兩極漸漸走向多極。舊的秩序打破了,新的格局還未形成。世界經(jīng)濟趨向一體化,地區(qū)性經(jīng)濟聯(lián)系日趨緊密,中泰間共同利益增多,兩國關(guān)系日益密切,各方面的合作和交流達到了空前的規(guī)模。中國聯(lián)合國席位的恢復(fù),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在世界的影響,對外聯(lián)系的增加又使中文在國際上的使用價值大大提高,這一切都給泰華文學(xué)的復(fù)興和發(fā)展造成了比較適宜的外部環(huán)境。
從文學(xué)的自身因素看,泰國也需要華文文學(xué)。泰國現(xiàn)有6000多萬人口,華人究竟有多少,歷來沒有也不可能有精確的統(tǒng)計。據(jù)估計總數(shù)恐怕不下于500萬;如果把有華人血統(tǒng)的都算上,總數(shù)大概在1000萬。華人的子女雖然大多都已泰化,但懂得中文的成年人仍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中華民族文化傳統(tǒng)在他們身上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沒有中華文化的精神食糧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想象的,這批人又可以說是泰國華文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者、需求者和推動者。另外,改革開放以后泰國又增加了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還有一批從事經(jīng)濟、貿(mào)易、文化、體育在泰國長駐或短期的居留者,以及不斷增加的中國游客,這些人數(shù)量不可低估,而且絕大多數(shù)不識泰文,不會講泰語,中文讀物包括文學(xué)讀物是他們閱讀上的第一需要。
1983年泰華寫作人協(xié)會成立,1990年改名為泰國華文作家協(xié)會。該協(xié)會以團結(jié)作家、反映泰華社會生活、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開展了一系列活動,工作搞得有聲有色。華文報紙《新中原報》《中華日報》《星暹日報》和《世界日報》和1994年創(chuàng)刊的《亞洲日報》都辟有文藝副刊。《亞洲日報》還出了柬埔寨版,把報刊發(fā)行到了柬、老、越三國。這些副刊,成了泰華文學(xué)作品的主要園地。20世紀80年代初,人們還在憂心忡忡地談?wù)撎┤A報紙的命運,認為終有一天它會絕種,因為懂中文的都已是白發(fā)人,掐死了華文教育,也就是掐死了中文。華文教育的復(fù)興,給中文報刊事業(yè)注入了活力,也給泰華文學(xué)培養(yǎng)了新的讀者和作家。泰華作協(xié)已有了第一批年輕的會員。
泰華文學(xué)的內(nèi)外交流搞得也頗有成績。過去的泰華文學(xué)圈子狹小,處于一種半封閉狀態(tài),華文作家不大關(guān)心泰文文學(xué),泰文的讀者更不知道有華文文學(xué)。其實,絕大多數(shù)的泰華作家是精通泰文的。現(xiàn)在,他們在創(chuàng)作的同時,也翻譯和介紹泰文文學(xué),在這方面做得最有成績的是沈逸文先生,他在泰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內(nèi)地出版的翻譯作品已有十余本。其他人,如饒公橋、林牧、張望、小民、修朝、老羊、征夫、魯純等也在翻譯上做出了成績。與此同時,華文作家的作品也被譯成了泰文,如20世紀60年代泰華著名的由8位作家合作寫出的接龍小說《風(fēng)雨耀華力》就被譯成了泰文,而且拍成了電視劇播出。華文作家的作品也常被譯載在著名的雜志上。這表明了泰國國內(nèi)對華文文學(xué)的接納和承認。這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文學(xué)現(xiàn)象是華裔泰文作家描寫華人生活的作品所受到的重視和歡迎,遠一點的如牡丹的長篇小說《泰國的來信》,友·布拉帕的《和阿公在一起》《排屋里的孩子》都是國家級的獲獎作品。20世紀90年代這類紀實性文學(xué)作品更加走紅,這至少反映了數(shù)目眾多的華裔對自己文化的探求和對根的追尋。所有這些都證明了華人和泰人在精神上加強了溝通和聯(lián)系。這對整個泰國文學(xué)的發(fā)展都是大有益處的。
泰華文學(xué)受著泰國社會生活的哺育,沒有泰國,當(dāng)然就沒有泰華文學(xué);但泰華作家又是華人,使用的是中文,因此他就無法割斷與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學(xué)傳統(tǒng)的聯(lián)系,二者的融合和統(tǒng)一,正是泰華文學(xué)興旺發(fā)達的基礎(chǔ)。正因為認識到這一點,泰華文學(xué)的對外交流特別是和母語文學(xué)的交流搞得很活躍,東盟國家華文作家間的交流通過“亞細安文藝營”的形式也有加強。這些使用同一語言創(chuàng)作的作家間的頻繁接觸、座談和討論,不但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誼,對雙方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也都是一種促進。
泰華文學(xué)近年來在創(chuàng)作上所取得的成績是令人矚目的。散見于報紙副刊的作品不算,僅1988~1996年這9年的時間里泰華作家所出版的作品集就有七八十種,無論從數(shù)量還是質(zhì)量上看,都應(yīng)該說是登上了一個歷史的新高度。這些作品大多富有激情,反映著作家對生活的獨特感受;筆觸伸向了社會的各個方面,說明泰華作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捕捉力;筆調(diào)比較清新質(zhì)樸,說明有一個健康良好的文風(fēng)。大多數(shù)作家仍然遵循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就當(dāng)前泰華文學(xué)整體來說,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前進了一大步。
泰華的散文創(chuàng)作所取得的成就突出,這種體裁的作品數(shù)量較大,質(zhì)量也較高。泰文文學(xué)的散文并不發(fā)達,并且把它混在短篇小說之中,沒有形成獨立的文體,泰華作家擅長散文有兩個原因,一是受到了中國散文優(yōu)秀傳統(tǒng)的直接影響,二是散文的題材不拘,寫起來比較自由,這就很適合于泰華作家商務(wù)繁忙、業(yè)余創(chuàng)作時間少的特點。泰華的散文佳作極多,像司馬攻的《故鄉(xiāng)的石獅子》《明月水中來》《荔枝奴》;夢莉的《李伯走了》《煙湖更添一段愁》《在月光下砌座小塔》;饒公橋的《祖母的微笑》《金魚與烏龜》《人妖》;姚宗偉的《雞啼天未曉》《小河之戀》;陳博文的《海憶》《雨聲絮語》;白翎的《滿載秀色滿載情》《蓮花·母親》;年臘梅的《迷失的八哥》《花緣》;黃水遙的《琴與花朵》《話酒》;白云的《架起回鄉(xiāng)的長橋》,白令海的田間野趣的系列散文等,都各具特色。其中有些篇章即使列入世界華文最優(yōu)秀的散文之列,也是毫無愧色的。泰華名家的散文已形成自己獨特風(fēng)格。司馬攻的散文清新雋永,回味深長,讀他的散文就像嚼一枚有滋有味的橄欖。他的散文集《明月水中來》在海內(nèi)外獲得了一致的贊譽;夢莉是一位專寫散文的女作家,讀她的散文會想起“低眉信手續(xù)續(xù)彈,說盡心中無限事”的詩句,她的散文凄清婉麗,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愁思,她的散文在中國8次獲獎,她已出版兩本散文集。饒公橋的散文質(zhì)樸剛健,有一種深沉豪放的氣勢;姚宗偉的散文老道、洗練、明快,好像在和朋友話家常;白翎的散文感情濃烈,文思優(yōu)美;黃水遙的散文自然脫俗……說散文自由,并不等于信手拈來,即成佳構(gòu)。寫好散文并不比其他體裁的作品容易。沒有對生活的獨特感受,沒有深厚的藝術(shù)功力,是難以進入這個藝術(shù)殿堂的。
從數(shù)量上說,泰華的小說創(chuàng)作不如散文多,但也出現(xiàn)了不少有特色的作品。比如黎毅的短篇小說就有其獨到的成就,他把故事型小說和生活型小說糅在一起,取二者之長,在注意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的同時,又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讀性,在人物的塑造上神形兼?zhèn)洌Z言上有很深的功夫。他的近作《瞬息風(fēng)云》構(gòu)思巧妙,起伏跌宕。作者設(shè)計了許多巧合,卻奇而不謬,真實可信。去世不久的女作家年臘梅,也很擅長寫短篇小說。她一生出了三部小說集,她的《春風(fēng)吹在湄江上》是一篇回腸蕩氣的小說,作品“記錄”了一代華人的悲歡離合,它的突出之處是不僅用歷史的眼光透視了人物的心理,而且在人物命運的處理上不落窠臼,小說的細節(jié)描寫、氣氛烘托都有妙筆。饒公橋的《人與狗》是1988年《新中原報》舉辦的小說比賽一等獎的獲獎作品,它主題鮮明,有巨大的社會意義和藝術(shù)感染力。小說通篇以形象說話,在題材的選取和開掘,主題的提煉和升華都有獨到之處。陳博文也是執(zhí)著于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位作家,他已出版了三部短篇小說集,他的《最后一擊》洋溢著一種恢宏的氣勢,有一種壯美的風(fēng)格。他用大刀闊斧的筆觸塑造了一個拳臺英雄,卻沒有把筆局限于拳臺,從而寫出了拳擊場下的金錢交易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卑鄙齷齪,從而賦予了這篇作品以更大的社會意義。
1990年以來,泰華文壇又掀起了小小說熱,出現(xiàn)了不少精品,取得成就最大的要首推司馬攻,他在1992年就出版了小小說的集子《演員》,他的作品構(gòu)思精巧,立意新穎,語言洗練,耐人尋味。司馬攻還是泰華文學(xué)界小小說的倡導(dǎo)者,1996年在曼谷又主持召開了第二屆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討會,對世界華文小小說的創(chuàng)作也有貢獻。陳博文的《晚霞滿天》小說集收錄了24篇小小說,他的作品行文有色彩,情節(jié)有曲折,結(jié)尾不突兀。小小說的重要作家還有黎毅、劉揚、曾心、曾天等。小小說這種形式比較適合泰華的社會環(huán)境和發(fā)表園地,前景是相當(dāng)廣闊的。
總的來說,現(xiàn)時的泰華小說已沖破20世紀50年代的小說模式,正向多樣化發(fā)展。但小說數(shù)量減產(chǎn),高質(zhì)量作品難尋,也是當(dāng)前小說創(chuàng)作的突出問題。
泰華文學(xué)中變化最快的要算是詩歌了。中國臺灣的現(xiàn)代派詩、中國大陸的朦朧詩都像在平靜的水面投下一個石子,在泰華詩壇上激起過波瀾,引起過爭論和討論。詩人們的意見雖不能一致,但討論和爭論的結(jié)果是深化了對詩的認識。文學(xué)本來不能整齊劃一,所以詩也絕不可以“一統(tǒng)”。詩是最有個性的東西。現(xiàn)在的泰華詩壇可以說是百花齊放,但詩“向內(nèi)轉(zhuǎn)”似乎是一種趨勢。泰華寫詩的人頗多,有成績的詩人也不少,如嶺南人、姚宗偉、李少儒、饒公橋、張望、林牧、子帆、張燕、李經(jīng)藝、曾天等。有的專寫古詩,而且頗有成就;有的詩注重通達曉暢,有的注重意蘊;有的詩顯得空靈,難懂一些;有的詩實在,追求的是情感;有的詩注重形式,有的詩則強調(diào)感情不受束縛;有的詩有韻,有的詩無韻。但應(yīng)該說,這些詩的傾向大多數(shù)是好的。但泰華的新詩也和中國的新詩一樣,仍然處在發(fā)展變化之中。詩應(yīng)該有意境,有情致,有詩味,能把讀者重新拉回到自己的身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雜文的創(chuàng)作成績也不小。泰華作家許多人都寫雜文,成績突出的當(dāng)屬劍曹(司馬攻)的《冷熱集》和《踏影集》。從內(nèi)容上說這兩個集子是豐富多彩的,近200篇的小雜文寫出了一個大世界。從藝術(shù)上說,這些文章也是雜文藝苑中的上品,它短小精粹、結(jié)構(gòu)嚴謹、意蘊深邃、耐人思考、詼諧幽默、妙趣橫生。陳博文的《暢言集》也有自己的特色,他把抒情和說理熔于一爐,對雜文的創(chuàng)作也頗有心得。此外姚宗偉、黎毅、胡惠南、老羊等人也都有雜文的佳作。
泰華文學(xué)已有80多年的歷史,它像一棵小草,在大石的壓迫下只能在縫隙中曲曲折折地生長。初期的泰華文學(xué)只能算是僑民文學(xué),應(yīng)該說是中國文學(xué)的一支。20世紀50年代以后,隨著華人的歸化和作品內(nèi)容的當(dāng)?shù)鼗殉蔀樘﹪膶W(xué)的一部分。現(xiàn)在的泰華文學(xué)雖在走向繁榮,作家的創(chuàng)作熱情很高,但也有隱憂。泰華文學(xué)的發(fā)展和繁榮首先取決于泰國國內(nèi)的政治環(huán)境。在歷史上它多次受到暴風(fēng)雨的襲擊,遠的如抗日戰(zhàn)爭時期1958年以后,近的如1976年,嚴酷的政治氣候幾乎使它無法生存,將來如何,命運并非完全掌握在泰華作家手里,誰都不能未卜先知。其次,泰華文學(xué)的基礎(chǔ)在于華文教育,這是培養(yǎng)作家、產(chǎn)生讀者的先決條件。歷史上華校最多時曾達到近400所,由于一再受到摧殘和限制,20世紀90年代初僅剩下十幾所而已,而且孩子學(xué)中文只能到小學(xué)四年級為止,學(xué)生既不能讀,更不能寫。現(xiàn)在泰國政府雖對華教開禁,但幾十年的斷層,要接上班,也不是短期內(nèi)能做到的。目前泰國華人中間對中文在泰國的前途仍有悲觀和樂觀的兩種看法,但不管什么看法也罷,問題是客觀存在的。所以泰華文學(xué)要發(fā)展,要繁榮,還要克服巨大的困難,還要爭取新的生存空間。
簡而言之,泰國華文文學(xué)要繁榮必須有內(nèi)外兩個方面的支撐。首先是泰國國內(nèi)對華文教育的政策,其次是中國經(jīng)濟實力、文化輻射力所能達到的程度。一種語言文字越來越“有用”,學(xué)的人會越來越少嗎?有了蓬勃發(fā)展的華文教育,還愁華文沒有讀者和作家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