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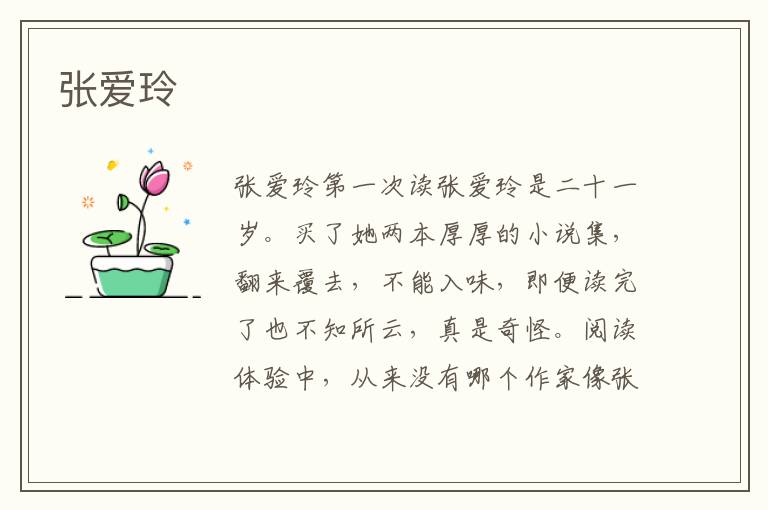
張愛玲
第一次讀張愛玲是二十一歲。買了她兩本厚厚的小說集,翻來覆去,不能入味,即便讀完了也不知所云,真是奇怪。閱讀體驗中,從來沒有哪個作家像張愛玲這樣讓我走神,直到今天,雖然斷斷續(xù)續(xù)讀了她不少作品,談不上喜歡,也不能說討厭。對我而言,張愛玲就是張愛玲,張愛玲不過張愛玲。
張愛玲小說我讀了感覺隔,她的照片看了卻喜歡,有舊時代風情。張愛玲算不得十分好看,透過紙本依稀可尋的舊風情卻足夠迷人。
民國那批女作家,廬隱、蕭紅、凌叔華、林徽因、冰心、丁玲,她們的樣子,各有各的性情分量,各有各的命運前途。廬隱端莊秀麗,蕭紅的眼神里有卓絕與閃爍的不安,林徽因有樸素,也有貴氣,凌叔華書卷味十足,冰心的樣子溫婉智慧,丁玲年輕時候桀驁不馴中藏著可人。但沒有誰的照片,有年輕的張愛玲骨子里傾國傾城的秉性。
有幅照片,張愛玲身穿大襖,大襖太大,襯得旗袍太小,于是只見大襖,不見旗袍。張愛玲低眉凝眸,置之度外,斯文通脫。第一次看見張愛玲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嘆她氣質(zhì)非凡。張愛玲的身材也不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張愛玲寫信給鄺文美,要她幫自己做旗袍,其中標注了三圍,換算成市尺的話,是“二尺四寸、二尺、二尺八寸”,稱得上窈窕了。
張愛玲的相貌雖然生得不俗,但按照中國的相術(shù)分析,卻是典型的福薄之相:下巴過尖,顴骨略高,山根太低。這些都影響人生氣數(shù)。某年在鄉(xiāng)下,有看相方士走江湖,我將一本書上印刷的張愛玲相片給他看,他甩下一句:“這個女人命不好。”或許真有天數(shù)。
張愛玲出版過一本《對照記》,展示了五十四張照片,配有文字說明,都是與張愛玲關(guān)系密切的親友和她本人的。在現(xiàn)代作家中,公開出版自己相片集的,張愛玲是第一人。
有人說《對照記》捧在手中一頁頁地掀,如同亂紋中依稀一個自畫像:稚雅,成長,茂盛,荒涼……此書一九九四年六月在臺灣出版,次年,張愛玲離開人世。離群索居幾十年之后,想想她晚年的處境與心態(tài),臨死前拋出這么一本圖解自傳,頗讓人尋味。我一方面喜歡這組照片,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內(nèi)心里是不忍看這組照片的。
翻開《對照記》,想想那個風華早絕、滿臉皺紋的張愛玲面對過去的青蔥歲月,內(nèi)心里想必會有幾分“人生如霧亦如夢,情如朝露去匆匆”的感慨吧。時光就是這樣,繁管急弦之際,容不得從容回味,已曲終人散。生命的大樹一枝一葉黯淡下來,如同泛黃的照片,那些風華正茂的照片依舊風華正茂,相中人在經(jīng)過風風雨雨后臉上卻爬滿了歲月不堪的痕跡,這是生之大苦。任何一個人最終都會輸給時間,輸給生活。
張愛玲語言好,美艷似罌粟花,又繁復(fù)得如同老式拔步床。我有個收藏舊家具的朋友,每次去她那里玩,總喜歡在拔步床上坐坐躺躺。那架床整體布局猶如房中又套了一座小房屋,床下有地坪,帶門欄桿,有床中床、罩中罩的意思,況味仿佛讀張愛玲小說。繁復(fù)的美艷成了張愛玲的美學(xué),語言簡直像迷宮。從張愛玲中篇《沉香屑》的白描中,可見一斑:
山腰里這座白房子是流線型的,幾何圖案式的構(gòu)造,類似最摩登的電影院。然而屋頂上卻蓋了一層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綠的,配上雞油黃嵌一道窄紅邊的框。窗上安著雕花鐵柵欄,噴上雞油黃的漆。屋子四周繞著寬綽的走廊,當?shù)劁佒t磚,支著巍峨的兩三丈高一排白石圓柱,那卻是美國南部早期建筑的遺風。從走廊上的玻璃門里進去是客室,里面是立體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幾件雅俗共賞的中國擺設(shè),爐臺上陳列著翡翠鼻煙壺與象牙觀音像,沙發(fā)前圍著斑竹小屏風,可是這一點東方色彩的存在,顯然是看在外國朋友們的面上。
這樣的文字讓人眼前一亮,行文如此細致精美耐煩。
張愛玲寫《金鎖記》《傾城之戀》《心經(jīng)》的時候,才華不僅橫溢,簡直沖天,那種巨大的想象力與生僻奇崛的行文,讓人如入寶山。當代有很多人模仿張愛玲,時過境遷,沒有她的時代,沒有她的才華,徒然一紙模式堆砌,甚至是滿目尖酸刻薄。在文學(xué)藝術(shù)上學(xué)習(xí)一個人,學(xué)神活,學(xué)形死,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更沒有兩個相同的大腦。
張愛玲有靈氣有邪氣,靈氣以邪氣做底子,見人所未見,察人所不察。張愛玲的世俗氣也值得一提,她俗得飽滿充沛,俗出了包漿,她的俗是宋朝舞娘的記賬本,認識社會的價值在明清書法之上。
張愛玲文成一家,背后又有《紅樓夢》傳統(tǒng)。其人是一朵詭異之花,炫目多彩,有著說不盡的傳奇。不過她的個性和為人處世的態(tài)度,限制了她在文學(xué)上的個人成就。身為小說家,張愛玲固有獨特之處,但比起魯迅的洞察,沈從文的厚樸,老舍的從容,稍微顯得小家子氣了。
離開胡蘭成后,原本的自信沒有了,原本的傲氣也沒有了。愛情對一個女人,特別是對張愛玲這樣的女人來說,實在太重要。沒有愛情,就沒有藝術(shù),甚至連生命個性的光芒都會減弱。張愛玲太內(nèi)秀,太內(nèi)秀的女人通常缺乏生存智慧,缺乏對世事的洞察。在《花凋》里她說:“笑,全世界便與你同聲笑;哭,你便獨自哭。”這大概也可視為自我心境的表白。張愛玲的弟弟說:
她的脾氣喜歡特別:隨便什么事情總愛跟別人兩樣一點。她曾經(jīng)對我說:“一個人假使沒有什么特長,最好是做得特別,可以引人注意。我認為與其做一個平庸的人過一輩子清閑生活,終其身,默默無聞,不如做一個特別的人做點特別的事,大家都曉得有這么一個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壞,但名氣總歸有了。”這也許就是她做人的哲學(xué)。
一個人過早涉及文藝,并不是件好事。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張小姐的確出名很早,但沒有享受盛名之下的快樂,卻為名所累,不可免俗地多了應(yīng)酬敷衍,這些為她日后的孤寂埋下了伏筆。現(xiàn)代派的代表人物劉吶鷗、穆時英,更是因為過早品嘗成名的滋味,在洋場惡少的路子上越滑越遠,最終卷進汪精衛(wèi)政權(quán),遭人暗殺,死的時候都不到四十歲,可惜是真可惜,活該也真活該。傅雷曾說:“奇跡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下場。”這話原是警示張愛玲的,希望她好自為之。我覺得任何人都應(yīng)該把這話掛在心頭,能多一份自律。
張愛玲的創(chuàng)作人生,其實只有短短兩年繁華。繁華過去,繁花匝地。自后張愛玲的創(chuàng)作順流直下,陷入困頓之境,雖然仍有少量佳作問世,總的來說,已是強弩之末了。遠涉大洋后,張愛玲沒有遇見一個適合她的文學(xué)時代。褪去作家的旗袍,成為蕓蕓眾生中的普通一員,甚至,連做個小富即安的普通婦人也不行,終日為生活奔波勞累。
移居美國后,張愛玲充分感受到在異國生存的艱難。在美國,有種組織叫文藝營,專門向那些有才華的藝術(shù)家免費提供為期三個月的短期住宿。經(jīng)別人幫助,張愛玲進入其中,分到了宿舍,而且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在這里,三十多歲的張愛玲認識了一個六十五歲的美國老男人賴雅。
孤身一人漂泊異國他鄉(xiāng),舉目無親,寂寞苦悶,而賴雅則是第一個從精神等各方面關(guān)懷張愛玲的男性。張愛玲可能把賴雅誤認作一個能幫助她進入主流英文文學(xué)世界的導(dǎo)師和經(jīng)濟的靠山,于是這一對不同國籍的老少作家戀愛了。得知張愛玲懷孕后,賴雅同意結(jié)婚,但是要張愛玲墮胎。
賴雅是個過氣作家,事業(yè)上開始走下坡路,生存都十分困難。貧賤夫妻百事哀,寫作不能出頭,生活異常困窘。婚后不久,賴雅中風,張愛玲只得放棄回香港發(fā)展的機會,一邊工作掙錢,一邊照看他,直至一九六七年賴雅去世。此后,張愛玲的生命中再也沒有一個女人應(yīng)有的感情寄托了。
張愛玲的小說里,性的意味是極常見的,但她用曹雪芹的手法一筆帶過了香艷。對性的回避,說明了張愛玲性愛觀有著避世的一面。常常想,張愛玲或許有些性冷淡,若不然一個如花少婦怎么可能會嫁給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在自傳體小說《小團圓》中有這樣的句子:“食色一樣,九莉?qū)τ谛砸部偸侨魺o其事。”有次在寫到一場性事之后,張愛玲如此自白:
他睡著了。她望著他的臉,黃黯的燈光中,是她不喜歡的正面。
她有種茫茫無依的戚覺,像在黃昏時分出海,路不熟,又遠。
現(xiàn)在在他逃亡的前夜,他睡著了,正好背對著她。
廚房里有一把斬肉的板刀,太沉重了。還有把切西瓜的長刀,比較伏手。對準了那狹窄的金色背脊一刀。他現(xiàn)在是法外之人了,拖下樓梯往街上一丟。
此時的性事,對兩人非常不愉快了。在男人就要逃亡的前夜,歡娛之后,女人對著他熟睡的脊背,動了殺機。
由于語言不通和文化差異,張愛玲在美國失意潦倒。沒朋友不說,自理能力也差。劉紹銘有篇文章叫《落難才女張愛玲》,名字看了就讓人心酸,才女落難猶如鳳凰折翼。劉紹銘寫他們第一次見面:“那天,張愛玲穿的是旗袍,身段纖小,教人看了總會覺得,這么一個‘臨水照花’女子,應(yīng)受到保護。”讀這樣的句子,聯(lián)想到張愛玲的后半生,越發(fā)讓人覺得造化弄人。
張愛玲最重要的作品是《傳奇》與《流言》,而這個女人,也真是生得傳奇跌宕,生得流言不斷。
一九九五年九月初,張愛玲在美國辭世,終年七十五歲。無兒無女,無親無友,一個人孤獨地離開塵世。幾天后,公寓管理員發(fā)現(xiàn)了她的遺體。
張愛玲臨終前,躺在房間的地板上,面對生命體征一點點流逝,會想到什么呢?或許已經(jīng)毫無依戀了,欣然自行。生于九月,死于九月,生于秋死于秋,張愛玲的景色也一生如秋,秋聲凄涼不忍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