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個中國人,他有點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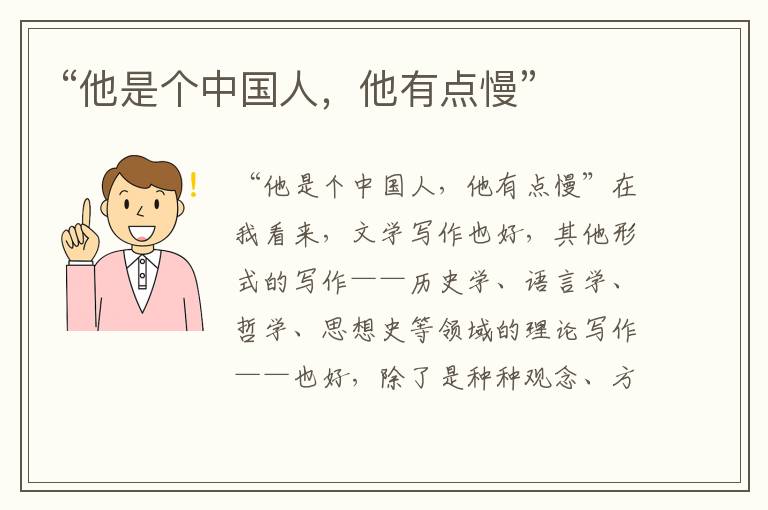
“他是個中國人,他有點慢”
在我看來,文學寫作也好,其他形式的寫作——歷史學、語言學、哲學、思想史等領域的理論寫作——也好,除了是種種觀念、方法和材料的相互交織,也是個人自傳與社會成見、心靈拷問與話語時尚的奇特混合。就話語時尚來說,無論我們將其視為風格變遷的標記,還是更多地將其看作是踐行的產物,回響其中的都是拉康的著名斷言——“現實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詞語的。”這是一個得風氣之先,且預示了某種知識癥候的斷言,但它是不祥的:詞的及物性如此迫切,以至我們已無法辨認詞語世界與物質世界、寫作與生存的真實聯系。肉體存在變輕了,詞卻取得了重量。詭異的是,這一重量不是由“寫”構成的,而是由對它的放棄構成的。在形形色色的理論思潮和話語時尚中,我們越來越看不到“寫”。也許對于一個生活在詞的世界的人來說,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了。是不是生活本身變快了?
全球化步伐中的亞洲速度是近年來世人談論甚多的一個熱門話題。尤其是東亞,建設開發之快,經濟增長之快,花樣翻新之快,令人神迷目眩。人們把這種快稱之為發展。其潛臺詞是:往前走,千萬別停下來,否則就會被時代潮流無情地拋棄。這種快對現實來說既不是客觀的,也不是主觀的,它只能說是對現實的一種塑造。方便面和易拉罐使我們的吃喝變快了,也使消化與排泄、餓與渴變快了。時裝工業將美提前一個季度預訂一空,短暫地風靡一時的美,哪來那么多的時間讓人把一件衣服穿舊?影視工業使夢想的兌現變得像取消一樣快。不消說信息和新聞快了,“本地報紙還沒有印出來,有人已在別處讀到了它。”男歡女愛當然也注定是快的,“快”樂嘛,庸俗小說把情呀愛的用流水作業的速度寫了出來,剛讀到一半,生活中的愛情就耗盡了:這一百來頁厚的、用一個晚上就能翻過去的愛情。流行歌曲則在幾分鐘內把剩下不多的舊情唱沒了,曲終人散,你在這兒還來不及卡拉,他者在那兒就已經OK了。真的,在全球化腳步的催促下,日常現實一下子變快了。金錢快得幾乎可以用來殺人,美元是快的,日元是快的,港幣臺幣無一不是快的,人民幣又何嘗不快?升值快,貶值快,流通快,掙得快,花得也快,似乎富日子窮日子都是快的。上哪兒都有出租車可打,“打不起夏利,還打不起一輛面的嗎”?面的也打不起的話,有的是中巴公共汽車可以坐,沒了座位,就站著唄,反正站著坐著,輪子都照樣快。零件、石油、噪音、紅綠燈、計費器、交通事故,所有這些全都匯集到了這樣一種快上來。甚至死亡也不例外,車禍和空難使現代人的死亡變得猝不及防,如果車子是掛在五擋上,其速度就正好符合我們對死亡的看法,剎車是剎不住的。
我們有沒有問過自己:這是要上哪兒去,有必要這么快嗎?如果是去天堂,與其乘高速電梯去,不如沿著老式樓梯一步一步悠悠地往上攀登,累了,不妨停下來歇口氣。本要去的地方是四十樓,但沒準你會發現,天堂其實就在第十層樓上。快,會錯過貝雅特里齊的美麗容顏。如果你正在去的地方是歐洲的某個城市,亞洲速度是否恰當呢?在影像中,在詞的意義上,我們之中誰沒去過歐洲——那個被拍成電影和照片,被寫出來,被翻譯成漢語的歐洲,不需要簽證就能去的紙歐洲。不過,要是你拿到簽證,真的飛去了歐洲,你會發現,大半個歐洲又舊又慢,就像是一盒慢速播放的錄像帶。陽光慢慢在那兒曬,把白天的勞作、思想、景色曬沒了,夜里似乎還在反面曬。風也是慢的,四月的風五月才開始吹。“寫”在歐洲從來是慢的,讀也只好跟著慢下來,海德格爾說過——讀,就是和寫一起消失。寫,就像是青草自己在生長,你不能用分鐘和小時去丈量它:寫下來的東西有它自己的生命,它自己的時間刻度,它會呼吸。你能在瓦格納、布魯克納的音樂中聽到這種緩慢舒展開來的、整個歐洲大陸的肺活量。你能從高迪的建筑作品看到老派歐洲人的那種沒一根直線的時間觀念,一座教堂建了上百年還沒建完,恐怕還得建上一百年。
當代詩人張棗將茨維塔耶娃說過的一句話“他是個中國人,他有點慢”作為題辭,放在他的重要作品《跟茨維塔耶娃的對話》前面。這句話來自茨維塔耶娃傳記中一個意味深長的片斷。一次茨維塔耶娃在巴黎某商店排隊購物,排在她前面的一個法國人對更前面的一個啰唆購物的華人極不耐煩,茨維塔耶娃當時用法語說:他是個中國人,他有點慢。在我看來,這話說得頗為傳神。中國是一個多么古老、多么遲慢的國家,慢了這么多個世紀,到20世紀90年代突然一切都快了起來。表面上這快是由物質世界的變化帶動起來的,但在物的后面其實潛藏著詞的推進器。當年茨維塔耶娃為使自己的寫作慢下來。曾斷然放棄詩的寫作,轉而從事散文寫作,布羅茨基稱之為“換擋”。茨維塔耶娃的詩歌作品具有驚人的超語速,我想,那樣的速度或許符合她對死亡的看法,但當她回過頭來注視生活時,卻感到了快所帶來的恐懼、暈眩和深刻的無力感。也許她在巴黎排隊購物時看到的那個中國人的慢,是促使她在詞的世界換擋減速的一個決定性瞬間。“中國人的慢”對茨維塔耶娃是個開關,她在其中關掉了詩歌,打開了不那么快的散文寫作。而在當今中國,散文、詩、小說,以及理論的寫作,樣樣都是快的。不僅寫是快的,閱讀和批評又何嘗不是快的。我不是指行文語氣、觀念和方法更新上的快,而是指詞的及物性的快,思潮更迭的那種變色龍性質的快,詞之權力轉化為世俗權力的快。對寫作而言,這種快一旦內化為某種知識品質,我們時代的精神生活中的某只輪子就會轉動得極度瘋狂。這恐怕是我們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