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文琪《緬懷扎里爾》東方文學名著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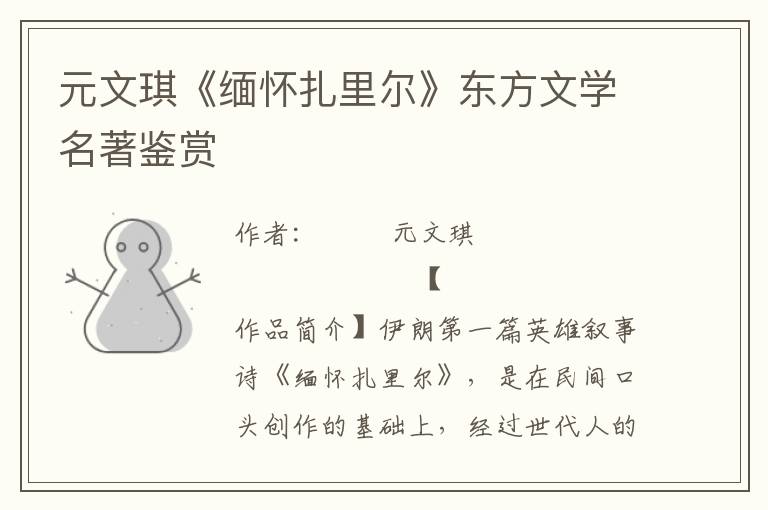
作者: 元文琪
【作品簡介】伊朗第一篇英雄敘事詩《緬懷扎里爾》,是在民間口頭創作的基礎上,經過世代人的口耳相傳,發展演變,后于5世紀未6世紀初定型的。早在安息王朝時期(公元前247—公元226年),民間就流傳著有關扎里爾的敘事詩。據西方學者考證,它本自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公元前550—330年)伊朗東北部廣為流傳的一則古老的愛情故事,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名叫扎里亞德雷斯。扎里爾的名字還出現在波斯古經《阿維斯塔》頌詩里。《阿邦·亞什特》提到他向江河女神阿娜希塔“供奉百匹馬、千頭牛和萬只羊”,祈求神靈保佑他“在遼闊無垠的戰場上,擊敗偽信者阿爾賈斯布”。安息時期的民間敘事詩《緬懷扎里爾》,到薩珊王朝(226651年)后期,瑣羅亞斯德教祭司根據國內外政治斗爭的需要,插手篡改,將其編定為帕拉維語(中波斯語)英雄贊歌。由于解釋性詞句的羼入,以致長期以來被誤認為是散文作品;后經西方學者校勘,剔除后加的衍文,還其敘事詩的本來面目。
《緬懷扎里爾》是古波斯敘事詩的代表作,在伊朗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譽為橫架在波斯古經《阿維斯塔·亞什特》神話詩和伊斯蘭時期英雄史詩《王書》之間的一座橋梁。菲爾杜西(940—1020年)創作卷帙浩繁的史詩《王書》時,收錄了薩曼王朝宮廷詩人達吉吉(卒于977年)所寫的《古什塔斯布傳》,其內容與《緬懷扎里爾》大同小異,相差無幾。由此可見,這篇帕拉維語英雄贊歌,在主題思想和題材內容等方面,對伊斯蘭時期的波斯語古典詩歌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緬懷扎里爾詩選》,元文琪譯,收入《東方文學作品選》,季羨林主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作品節選】
戰爭動員
古什塔斯布命令扎里爾,
在山頂燃起熊熊的篝火,
傳圣旨于全國每個角落:
除了拜火祠堂的穆岡,
男人們務必在兩個月內,
到古什塔斯布王宮集合,
無論他是十歲的幼童,
還是年過八旬的長者;
若違抗圣旨逾期未到,
必將處以絞刑定殺不赦!
戰鼓聲響,軍號嘹亮,
人如潮涌來自四面八方。
大象隊、駱駝隊和戰車隊,
隊隊行行整齊而雄壯。
士兵們高擎斧鉞腰掛箭囊,
銅盔鐵甲閃耀著金光。
扎里爾戰死疆場
驍勇的統帥扎里爾,
飛身上馬沖向戰場,
猶如一團熊熊的烈火——
借助風勢燃著蘆葦塘。
他揮舞閃光的利劍,
奮勇劈殺,銳不可擋,
隨著每一次手起劍落,
管叫十名敵兵把命喪。
希翁人兵敗如山倒,
扎里爾殺得心歡意暢。
此情此景看在眼,
阿爾賈斯布惶恐不安。
忙問一聲眾將官:
哪個有膽量出陣交戰?
若把扎里爾斬于馬前,
孤王將封他為大臣,
并恩賜美麗的公主——
蓋世無雙的扎蕾絲坦。
否則,照這樣打下去,
希翁人敗陣如鳥獸散,
你我的性命也難保全!
維德拉弗什挺身而出,
急令部下備好坐騎。
他手執帶毒的魔槍,
要與扎里爾拼個高低。
經過一番激烈的搏斗,
自知不是扎里爾的對手,
維德拉弗什撥轉馬頭,
悄然溜到扎里爾身后,
用他那帶毒的魔槍,
把伊軍統帥的鎧甲刺透!
頓時喊殺聲嘎然而止,
空中不再見流矢交墜。
伊軍將士個個呆若木雞,
只因統帥扎里爾倒下馬去。
巴斯塔瓦爾替父報仇
狡詐的維德拉弗什,
手執一桿帶毒的魔槍,
縱身上馬前去迎敵。
巴斯塔瓦爾大喝一聲:
呔!不信神的異教徒,
快上前來,決一雌雄。
別看我胯下有駿馬,
年少騎術欠佳;
休道我囊中有利箭,
力虧硬弓難拉。
只因我父親慘遭毒手,
今番特來替父報仇,
不殺你,我誓不罷休!
【作品鑒賞】《緬懷扎里爾》是一篇洋溢著愛國主義熱情的英雄頌歌,它記述了傳說中的伊朗和鄰國突朗之間因宗教信仰分歧而發生的一場戰爭。作者通過對戰爭起因、戰爭動員、戰爭經過和戰爭結局的生動描繪,謳歌了凱·古什塔斯布國王的兄弟,伊軍統帥扎里爾為堅持瑣羅亞斯德教的信仰,為捍衛國家的獨立和尊嚴,而英勇殺敵,為國捐軀的英雄壯舉;贊揚了以扎里爾的幼子巴斯塔瓦爾,旗手格拉米·卡爾特和王子埃斯梵迪亞爾為代表的伊軍將士浴血奮戰,全殲敵軍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同時嘲諷了突朗國君阿爾賈斯布及其將領維德拉弗什的飛揚跋扈、陰險狡詐的丑惡嘴臉,因而深刻地闡明了這樣一個主題:為祖國的榮譽和民族信仰而戰必勝,倒行逆施、胡作非為者必敗。
《緬懷扎里爾》堪稱思想性和藝術性兼優的佳作,在扎里爾父子英雄形象的塑造和戰爭場面的描繪方面確有獨到之處。它以伊朗和突朗(希翁)之間的戰爭為主線,以表現扎里爾父子為代表的伊軍將士的“忠”和“勇”為旨趣,寫得既層次分明,井然有序;又跌宕起伏,變化莫測,顯示出高超的藝術技巧。
詩一開頭,首先簡明扼要地交待了戰爭發生的背景和緣由。古什塔斯布國王在位期間,伊朗改宗瑣羅亞斯德教,這引起突朗國君阿爾賈斯布的憤怒,特派使者赴伊朗以武力要挾,硬要伊朗改弦更張,拋棄自己的民族信仰,否則就將“舉兵討伐”。伊軍統帥扎里爾面對強敵,毫無懼色,義正詞嚴地回答:“休得口出狂言,自吹自擂,/來日戰場咱們再分高低。/看刀光劍影,戰馬嘶鳴中,/虔誠的正教徒怎樣把魔鬼崇拜者殺得一敗涂地!”挑戰者暴戾恣睢,應戰者大義凜然,孰是孰非,不言自明。
戰爭前夕,古什塔斯布國王從睿智的老臣賈馬斯布的預言中得知,伊軍將領至少有23人將在戰爭中獻身,其中包括統帥扎里爾。這時國王產生動搖,到底應戰與否,心里拿不定主意。扎里爾明知來日出戰兇多吉少,仍斬釘截鐵地表示:“明日交戰我將一馬當先,/痛殲希翁頑軍一十五萬!”他終于說服國王,堅決抵御外侮,與突朗決一死戰。在賈馬斯布的預言所引起的這場風波中,再次展現出扎里爾視死如歸報效國家的英雄氣概。
如果說在戰爭起因和戰爭動員階段著意表現扎里爾的“忠”,即忠于祖國,忠于民族信仰,那么在戰爭經過的描述中,則主要寫扎里爾的“勇”,即英勇殺敵,不怕犧牲。他“猶如一團熊熊的烈火”,在敵陣中“左右劈殺,銳不可擋”。扎里爾勇武壓群敵,豪氣吞萬里的雄姿,被惟紗惟肖地勾畫出來。扎里爾的“勇”來源于他的“忠”;扎里爾的“忠”見諸于他的“勇”。作者以“忠”“勇”結合,虛實相生的藝術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伊軍統帥扎里爾的光輝形象。
描寫刀來槍往的戰爭場面,容易流于平鋪直敘,單調乏味。然而,詩人運用巧妙的構思和敘事兼抒情的筆法,把戰爭經過寫得潮汐漲落,有起有伏,讀來趣味盎然。所向披靡的扎里爾不幸被陰險狡詐的希翁主將維德拉弗什刺下馬來,“頓時喊殺聲嘎然而止”,伊軍將士全被驚呆了。兩軍交戰,主帥陣亡,這對伊軍說來該是何等沉重的打擊!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扎里爾的幼子巴斯塔瓦爾殺出陣來。當發現父親的尸體倒在血泊之中,少年不覺心似刀絞,淚流滿面,他按捺不住內心的悲痛,放聲哭訴道:
呵,我聲名顯赫的父親,
你怎么會倒在血泊里?
呵,神鷹般矯健的英雄,
是誰掠走了你的坐騎?
你曾發誓要殲滅希翁大軍,
如今何以落到這步田地?
呵,你的須發被風吹亂,
你純潔的身軀慘遭蹂躪!
失去往日的神彩和威嚴,
父親的面頰布滿了灰塵。
巴斯塔瓦爾的哭悼,字字血,聲聲淚,情見于辭,感人至深。他強壓怒火,再次請戰上陣,誓為父親扎里爾報仇雪恨。
巴斯塔瓦爾正待要出擊,
忽聽得亡父在天之靈言道:
孩兒呀!快把長矛丟棄,
對付邪惡奸詐的異教徒,
弓箭才是最有效的武器!
少年人這才恍然大悟,
急忙取箭,舉弓怒射,
維德拉弗什應聲倒地。
此處對扎里爾死后顯靈的富于浪漫色彩的描寫,再次突現出主人公那肝膽照天地,精神泣鬼神的高大形象。這不禁令人聯想起我國古代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在《國殤》中對陣亡將士的禮贊:“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這場戰爭以伊軍的大勝告終。埃斯梵迪亞爾王子活捉了突朗國君阿爾賈斯布,當即令人“剁去他的手足,割掉他的耳朵”,將他“背朝前,臉朝后”地“倒捆在禿尾巴的毛驢上”,隨后意味深長地發話道:
就這樣滾回你的老家去,
也好給人以有益的啟發——
挑起戰爭終將自食惡果,
倒行逆施必定受到懲罰!
這樣的結尾,簡潔有力,幽默風趣,而且寓意深邃,耐人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