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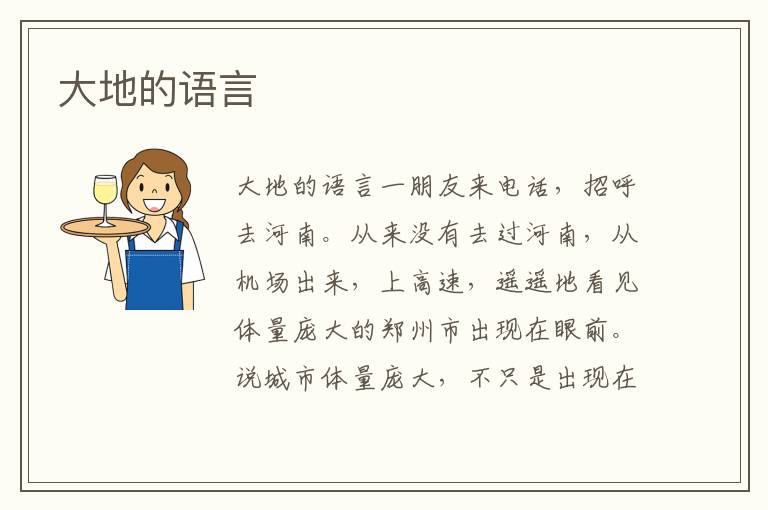
大地的語言
一
朋友來電話,招呼去河南。從來沒有去過河南,從機場出來,上高速,遙遙地看見體量龐大的鄭州市出現在眼前。
說城市體量龐大,不只是出現在視線中那些聳立的高大建筑,而是說一種感覺:那隱沒在天際線下的城市更寬大的部分,會彌散一種特別的光芒,讓你感覺到它在那里。聲音、塵土、燈光,混同、上升、彌散,成為另一種光,籠罩于城市上方。這種光,睜開眼睛能看見,閉上眼睛也能看見。這種光吸引人眺望,靠近,進入,迷失。但我們還是一次次剛剛離開一座城市就進入另一座城市。重復的其實都是同一種體驗:在不斷興奮的過程中漸漸感到悵然若失。我們說去過一個省,往往就是說去省會城市。所以,此行的目的地我也以為就是眼前已經若隱若現的這個城市。汽車拐上了另一條高速路,這時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下面的周口市,再下面的淮陽縣。
還在車上,熱情的主人已經開始提供訊息,我知道了將要去的是一個古跡眾多的地方。這些古跡可不是一般的古跡,都關乎中華文明在黃河在這片平原萌發的最初起源。這讓我有些心情復雜。當“河圖”“洛書”這種解析世界構成與演化的學問出現在中原大地時,我的祖先尚未在人類文明史上閃現隱約的身影。所以,當我行走在這片文明堆積層層疊疊的大地之上時,一面深感自己精神來源短暫而單一,一面也深感太厚的文明堆積有時不免過于沉重。而且,所見如果不符于想象時,容易發出“禮崩樂壞”的感嘆。
我愿意學習,但不論中國還是外國,都不大愿意去那種古跡眾多的地方。那種地方本是適于思想的,但我反而被一種莫名的能量罩住了,腦袋木然,不能思想。這也是我在自由行走不成問題的年代久久未曾涉足古中州大地的原因吧。
拜血中的因子所賜,我還是一個自然之子,更愿意自己旅行的目的地,是寬廣而充滿生機的自然景觀:土地、群山、大海、高原、島嶼、一群樹、一棵草、一簇花。更愿意像一個初民面對自然最原初的啟示,領受自然的美感。
在那些古跡眾多之地,自然往往已經破碎,總是害怕面對那種一切精華都已耗竭的衰敗之感。更害怕大地的精華耗竭的同時,族群的心智也可怕地耗竭了。所以,此行剛剛開始,我已經沒有抱什么特別的希望。
二
行車不到十分鐘,就在我靠著車窗將要昏昏然睡去時,超乎我對河南想象的景觀出現了。
這景觀不是熱情的主人打算推銷給我們這群人的。他們精心準備的是一個古老悠久的文化菜單,而令我興奮的僅僅是在眼前出現了寬廣得似乎漫無邊際的田野。
收獲了一季小麥的大地上,玉米,無邊無際的玉米在大地寬廣中拔節生長。綠油油的葉片在陽光下閃爍,在細雨中吮吸。這些大地在中國肯定是最早被耕種的土地,世界上肯定也少有這種先后被石頭工具、青銅工具、鐵制工具和今天燃燒著石油的機具都耕作過的土地。人類文明史上,好多閃現過文明耀眼光輝,同時又被人類自身推向一次次浩劫的土地,即便沒有變成一片黃沙,也早在過重的負載下茍延殘喘。
翻開一部中國史,中原大地兵連禍接,旱澇交替。但我的眼前確實出現了生機勃勃的大地,這片土地還有那么深厚肥力滋養這么茁壯的莊稼,生長人類的食糧。無邊無際的綠色仍然充滿生機,莊稼地之間,一排排的樹木,標示出了道路、水渠,同時也遮掩了那些素樸的北方村莊。我喜歡這樣的景象。這是令人感到安心的景象。
如今是全球化城市化時代,在我們的國家,數億農民耕作的田野,吃力地供養著越來越龐大的城市。農業,在經濟學家的論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統計中越來越被輕視的一個產業。在那些高端的論壇上,在專家們演示的電子圖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數據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線。問題是,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又不能直接消費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線。不能早餐吃風險投資,中餐吃對沖基金,晚間配上紅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產,盡管廚師也可以把窩頭變成蛋糕,并把巧克力蛋糕做成高級住宅區的縮微景觀,一叉,一座別墅,一刀,半個水景庭院。那些能將經濟高度虛擬化的賺取海量金錢的聰明人,能把人本不需要的東西制造為巨大需求的人,身體最基本的需求依然來自土地,是小麥、玉米、土豆,他們幾十年生命循環的基礎和一個農民一樣,依然是那些來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們并沒有進化得可以直接進食指數、期貨、匯率。但他們好像一心要讓人們忘記大地。這個世界一直有一種強大的聲音,在告訴人們,重要的不是大地,重要的不是大地哺育人類那些根本的東西。
一個叫利奧波德的美國人在半個多世紀前就質疑過這種現象,并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幾千年的人類歷史只發展出“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倫理觀念,一種人與財富關系的倫理觀念。并認為這種觀念大致構成兩種社會模式,一種用“金科玉律使個人與社會取得一致”,一種則“試圖使社會組織與個人協調起來”。“但是,迄今為止沒有一種處理人與土地,以及人與在土地上生長的動物和植物之間關系的倫理觀”。
倫理觀是關乎全人類的,不幸的是,我們并不生活在一個一切社會規則以全體人類利益為考量的世界上。現在的價值體系中,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資源。人是資源,土地也是資源。當土地成為資源,那么,在其上種植莊稼,顯然不如在其上加蓋工廠和商貿中心。這個體系運行的前提就是,弱小的族群、古老的生活方式需要為之付出巨大的犧牲。
農業需要作出犧牲,土地產出的一切,農民胼手胝足的勞動所生產出的一切,都是廉價的,因為有人說這沒有“技術含量”。幾千年才培育成今天這個樣子的農作物沒有技術含量,積累了幾千年的耕作技術沒有技術含量,因為古人沒有為了一個公司的利益去注冊專利。玉米、土豆在幾百年前從美洲的印第安人那里傳入了歐洲與亞洲,但墨西哥的農民還掙扎在貧困線上,他們離井背鄉,在大城市的邊緣地帶建立起全世界最大的貧民窟,只為了從不得溫飽的土地上掙脫出來,到城市里去從事最低賤的工作。我曾經在墨西哥那些被干旱折磨的原野上,在一株仙人掌巨大的陰涼下黯然神傷。我想起一本描述拉丁美洲如何被作為一種資源被跨國資本無情掠奪的書:《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如果書名可以視為一種現實的描述,那么,我眼前這片原野的確已經流盡了鮮血。眼前的地形地貌,讓我想起胡安·魯爾福的描寫鄉村破敗的小說《教母坡》中的描述:“我每年都在我那塊地上種玉米,收點玉米棒子,還種點兒菜豆。”但是,風正在刮走那些地里的泥土,雨水也正沖刷那些土地里最后一點肥力。
三
今天,在遠離它們故鄉很遠很遠的地方,我看見一望無際的玉米亭亭玉立,莖并著莖,根須在地下交錯,葉與葉互相摩挲著絮絮私語,它們還化作一道道的綠浪,把風和自己的芬芳推到更遠的地方。在一條飛速延展的高速公路兩邊,我的視野里始終都是這讓人心安的景象。
轉上另外一條高速路,醒目的路牌標示著一些城市的名字。這些道路經過鄉野,但目的是連接那些巨大的城市,或者干脆就是城市插到鄉村身上的吸管。資本與技術的循環系統其實片刻不能缺少從古至今那些最基本的物質的支撐。但在這樣的原野上,至少在我的感覺中,那些城市顯得遙遠了。視野里掠到身后,以及撲面而來的,依然是農耕的連綿田野。
我呵氣成霧,在車窗上描畫一個個漢字。
這些象形的漢字在幾千年前,就從這塊土地上像莊稼一樣生長出來。在我腦海中,它們不是今天在電腦字庫里的模樣,而是它們剛剛生長出來的時候的模樣,剛剛被刻在甲骨之上的模樣,剛剛被鐫刻到青銅上的模樣。
這是一個個生動而又親切的形象。
土。最初的樣子就是一棵苗破土而出,或者一棵樹站立在地平線上。
田。不僅僅是生長植物的土壤,還有縱橫的阡陌、灌渠、道路。
禾。一棵直立的植株上端以可愛的姿態斜倚著一個結了實的穗子。
車窗模糊了,我繼續在心里描摹從這片大地上生長出來的那些字:麥。黍。瓜。麻。菽。
我看見了那些使這些字具有了生動形象的人。從井中汲水的人。操耒犁地的人。以臼舂谷的人。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
眼下的大地,麥收季節已經過去了,幾百年前才來到中國大地上的玉米正在茁壯生長。那些健壯的植株上,頂端的雄蕊披拂著紅纓,已然開放,輕風吹來,就搖落了花粉,紛紛揚揚地落入下方那些腋生的雌性花上。那些子房顫動著受孕,暗含著安安靜靜的喜悅,一天天膨脹,一天天飽滿。待秋風起時,就會從田野走進了農家小小的倉房。
就因為在讓人心生安好的景色中描摹過這些形狀美麗的字眼,我得感謝讓我得以參加此次旅行的朋友。
就在這樣的心情中,我們到達了周口市淮陽縣。我是說到達了淮陽縣城,因為此前,已經穿過了大片屬于淮陽的田野。讓人心安的田野,莊稼茁壯生長的田野,古老的,經歷了七災八難仍然在默默奉獻的田野。還未被加工區、開發區、新城鎮分割得七零八落的田野。
四
沒想到此地有這么大個還活著的湖。
我說活著的意思,不只是說湖盆里有水。而是說水還沒有被污染,還在流動循環,晚上,住在湖邊的賓館里,瀏覽東道主精心準備的文化旅游菜單,就可以聞到從窗外飄來水和水生植物滋潤清新的氣息。
有了這份菜單上的一切,淮陽人可以非常自豪,對我而言,不要菜單上這一切的一切,我也可以說我愛淮陽。愛窗外廣大的龍湖。愛曾經穿越的廣闊田野。愛那些茁壯生長的玉米。想著這些的時候,電視里在播放新聞,是世界性糧食危機的消息。其實,不要這樣的消息佐證,我也深愛仍有人在勤勉種植,仍然有肥力滋養出茂盛莊稼的田野。但這樣的消息能讓人對這樣的土地加倍地珍愛。
席上,主人向我們介紹淮陽。太昊。伏羲。神農。八卦。陳。宛丘。雖然肉體不是華夏血脈,但精神卻受此文明深厚的滋養,但我更愿意這種滋養是來自典籍浩然的熏染,而不是在一個具體的地點去憑吊或膜拜。飯后漫步縣城,規模氣氛都是那種認為農耕已經落后、急切地要追上全球化步伐的模樣——被遠處的大城市傳來的種種信息所強制、所驅迫的模樣。是一個以農耕供養著這個國家,卻又被所忽視的那些地方的一個縮影。
晚上,在賓館房間里上網搜尋更多本地資訊。單獨的詞條都是主人熱心推薦過的,就是在本地政府網站上,關于土地與農業介紹也很簡略,篇幅不長可以抄在下面:
淮陽縣地處黃河沖積扇南緣,屬華北平原的一部分……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西北海拔高度50米,東南海拔高度40米,……全縣總土地面積220.18萬畝,其中耕地面積177.32萬畝,占總土地面積的80.53%,土壤主要有兩合土、砂土、淤土三大類。土質大都養分豐富,肥力較高,疏松易耕,適于多種農作物和林木生長。縣境內地勢基本平坦,但由于受黃河南泛多次沉積的影響,地面呈“大平小不平”狀態,造成了許多面積大小不等深度不一的洼坡地,其面積約48萬畝,占總耕地面積的27%。這些洼坡地昔日是大雨大災,小雨小災,“雨后一片明,到處是蛙聲”,十年九不收。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帶領全縣人民對洼坡地連年進行治理,現已是溝渠縱橫交錯,排水系統健全,歷史上的澇災得到了根治,昔日“十年九不收”的洼坡地已變成“糧山”“棉海”。
正是這樣的存在讓人感到安全。道理很簡單,中國的土地不可能滿布工廠。中國人自己不再農耕的時候,這個世界不會施舍給十幾億人足夠的糧食。中國還有這樣的農業大縣,我們應該感到心安。國家有理由讓這樣的地方,這樣地方的人民,這樣地方的政府官員,為仍然維持和發展了土地的生產力而感到驕傲,為此而自豪,而不因另外一些指標的相對滯后而氣短。讓這些土地沐浴到更多的政策性的陽光,而不是讓胼手胝足生產的農民都急于進入城市,不是急于讓這些土地被拍賣,被置換,被開發,被污染,并在其耗盡了所有能量時被遺棄。
我相信利奧波德所說:“人們在不擁有一個農場的情況下,會有兩種精神上的危險。一個是以為早飯來自雜貨鋪,另一個是認為熱量來自火爐。”其實,就是引用這句話也足以讓人氣短。我們人口太多,沒有什么人擁有寬廣的農場,我們也沒有那么多森林供應木柴燃起熊熊的火爐。更令人慚愧的是,這聲音是一個美國人在半個多世紀前發出來的,而如今我們這個資源貧乏的國家,那么多精英卻只熱衷傳遞那個國度華爾街上的聲音。
我曾經由一個翻譯陪同穿越美國寬廣的農耕地帶,為的就是看一看那里的農村。從華盛頓特區南下弗吉尼亞常常看見騎著高頭大馬的鄉下人,佇立在高速公路的護坡頂端,浩蕩急促的車流在他們視線里奔忙。他們不會急于想去城里找一份最低賤的工作,他們身后自己的領地那么深廣:森林、牧場、麥田,相互間隔,交相輝映。也許他們會想,這些人匆匆忙忙是要奔向一個什么樣的目標呢?他們的安閑是意識到自己擁有這個星球上最寶貴的東西時那種自信的安閑。就是不遠處,某一座小丘前是他們獨立的高大房子,旁邊是馬廄與谷倉。在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兩岸,那些農場一半的土地在生長小麥與大豆,一半在休息,到長滿青草的時候,拖拉機開來翻耕,把這些青草埋入地下,變成有機肥讓這片土地保持長久的活力。
就是在那樣的地方,突然起意要寫一部破碎鄉村的編年史《空山》。我就在印第安納大學旅館里寫下最初那些想法。看到大片休耕的田野,我寫道:“這是在中國很難看到的情形,中國的大地因為那過重的負載從來不得休息。”
在那里,我把這樣的話寫給小說里那個故鄉村莊:“我們租了一輛車,從六十七號公路再到三十七號。一路掠過很多綠樹環繞的農場。一些土地正在播種,而一些土地輪到休息。休息的地開出了這年最早的野花。”
從那里,我獲得了反觀中國鄉村的一個視點。
我并不拒絕新的生活提供的新的可能。
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城市制造出來的產品,或者關于明天,關于如何使當下生活更為成功更為富足的那些新的語匯,總是使我們失去內心的安寧。城市制造出來了一種蔑視農耕與農人的文化。從城市中,我們總會不斷聽到鄉村衰敗的消息,但這些消息不會比股指暫時的漲落更讓人不安。我們現今的生活已經不再那么靜好簡單了,以至于很多的東西不能用一個字來指稱,而要組成復雜的詞組。詞組的最后一個字都是“化”,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商品化。全球化。這個世界的商業精英們發明了一套方法,把將要推銷的東西復雜化,發明出一套語匯,不是為了充分說明它,而是將其神秘化,以此十倍百倍地抬高身價。
糧食危機出現了,但農業還是被忽視。這個世界的很多地方餓死人了,首先餓死的多半是耕作的農民。比如,我們談論印度,不是說旱災使多少農民餓死,多少農民離鄉背井,大水又淹沒了多少田野,對于這個瘋狂的世界,這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大概率事件。媒體與精英們最熱衷的話題是這個國家又為歐美市場開發了多少軟件,這些軟件賣到了怎樣的價錢。不反對談論軟件,但是不是也該想想那些年年都被洪水淹沒的農田與村落,談談那些天天都在種植糧食卻餓死在逃荒路上的人們?或者當洪水漫卷,國家機器開動起來救助一下這些劫難中的供養人時,城里人是不是總要以拯救者的面目像上帝一樣在鄉村出現?
五
平糧臺。
這是淮陽一個了不起的古跡。名副其實,這是一個在平原上用黃土堆積起來的高臺。面積一百畝。被認定為中國最古老的城池——宛丘。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
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從那么久遠的古代,原始的農耕就奉獻出所有精華來營造城市,營造由自己供養,反過來又懾服自己的威權了。這個龍山文化時期就出現的城市的雛形如果真的被確認,無疑會在世界城市史上創造很多第一,從而修正世界城市史。幾千年過去了,時常溢出河道的黃河水用巨量的泥沙把這片平原層層掩埋。每揭開一層,就是一個朝代。新生與毀滅的故事,陳陳相因,從來不改頭換面。但這個高丘還微微隆起在大平原上。它為什么不仍然叫宛丘,不叫神農之都,卻叫平糧臺?是不是某次黃水襲來的時候,人們曾經在這個高地儲存過救命糧食,放置過大水退后使大地重生的寶貴種子?在這個已然荒蕪的土臺上漫步時,我很高興這片土地仍然具有生長出茂盛草木的活力。那些草與樹仍然能夠應時應季開放出花朵。草樹之間,還有勤勉的村民開辟出不規則的地塊,花生向下,向土里扎下能結出眾多子實的枝蔓,芝麻環著節節向上的莖,一圈圈開著潔白的小花。
人類不同的歷史在大地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但大地的奉獻卻是一樣。我記起在俄羅斯的圖拉,由森林環繞的托爾斯泰的莊園中,當大家去文豪故居中參觀時,我沒有走進那座房子,看干涸的墨水瓶、泛黃變脆的手稿。我走進了旁邊的一個果園。樹上的蘋果已經收獲過了,林下的草地還開著一些花。淡藍的菊苣,粉紅的老鸛草,再有就是與中國這個叫平糧臺的荒蕪小丘上輪生著白色小花一模一樣的芝麻。人操持著不同的語言,而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一種語言。一種只要愿意傾聽,就能懂得的語言——質樸,誠懇,比所有人類曾經創造的,將來還要創造的都要持久綿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