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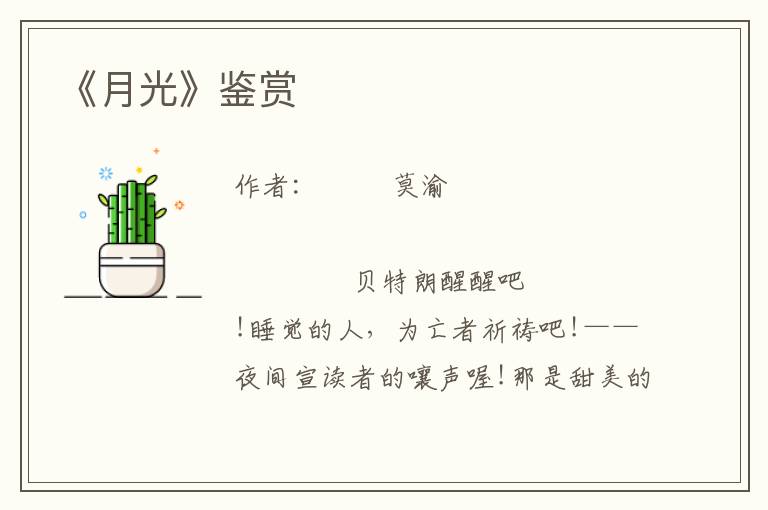
作者: 莫渝
貝特朗
醒醒吧!睡覺的人,
為亡者祈禱吧!
——夜間宣讀者的嚷聲
喔!那是甜美的,夜晚鐘響時,望著宛如金幣的月亮!
兩位麻瘋病人在我的窗下哀嘆,一只狗在十字路口吠叫,而我壁爐邊的蟋蟀低沉卜算。
不久,我的耳雜只聽得深沉的靜默。麻瘋患者走進他們的窩,重重鞭笞女人。
那只狗溜進小巷,停在被雨淋銹的長矛架前,因朔風而凍顫。
蟋蟀入睡了,這時,最后的小火花在爐火灰燼中,熄滅最后的微光。
而我,我覺得——那么多渴盼都支離破碎了!——月亮扮著鬼臉,伸長舌頭象個吊死鬼!
(臺灣 莫渝 譯)
本篇收進《夜中人加斯巴》又譯《夜晚的加斯巴爾》第3卷第5篇,寫作時間大約在1827或1828年間。本詩初稿曾發表于1828年的《外省人》雜志。初稿與本詩略有不同。
滿月之夜,是一個美好的時光,金幣閃閃般的月亮,令人興起甜美感受的無限遐思。這么好的良辰美景,該有佳人共伴,或者好友同聚;然而,作者的心理與周遭環境,破壞了氣氛。麻瘋病人臨窗哀嘆,即使回家,也要打罵妻子;孤單的野狗到處流浪;狂吠、凍顫;與詩人最接近的蟋蟀由低沉鳴叫到夜深入睡;壁爐里沒有一絲微光
由脹滿的有希望的圓月,到沒有微光的絕望,詩人已跌至人生谷底,所有的渴盼都支離破碎。月光不再是閃閃誘人的金幣,而象吊死鬼的長舌頭般的死白。
可憐的詩人,對圓月絕望透頂,對生命感到黯然無光。
詩人的創作受制于個人的心理與環境,環境會變,個人心理也有所變遷,二者之間的抉擇與輕重,個人心理因素居多。基本上,貝特朗是一個多愁善感、長期病患、置身逆境的落魄詩人,即使有心高歌,唱出來的聲音仍屬哀嘆、感傷。悲郁的詩人,常是如此。
貝特朗的每一篇散文詩,詩前均有別人、前人或經典、民諺的摘句,大體尚能結合詩人心態與詩的內容。本篇引錄的句子,類似更夫打梆時的驚語,提醒世人能給予死者一處安息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