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婭《靈魂歸來》東方文學名著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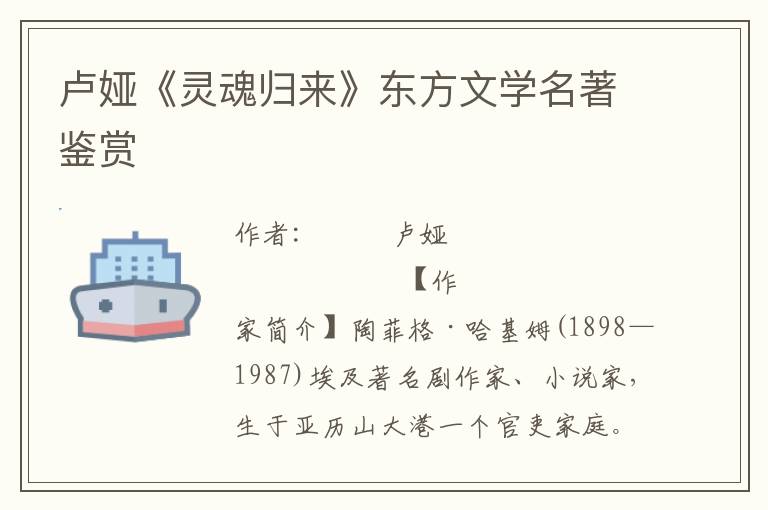
作者: 盧婭
【作家簡介】陶菲格·哈基姆(1898—1987)埃及著名劇作家、小說家,生于亞歷山大港一個官吏家庭。上中學時,就顯示出對音樂和戲劇的愛好及文學天才。1919年因參加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爭取民族解放運動而被捕。1924年在開羅法律學校畢業后赴法國深造。此間,他生活在純藝術的天地里,博覽古今小說,研究西方音樂和戲劇,探討歐洲歷代文化,尤其著重鉆研古希臘和法國戲劇藝術,立下了要成為小說家和戲劇家的志向。1928年回國后曾先后在檢察、教育、社會事務等部門任職。1943年一度辭去政務,專門從事文藝創作與研究。1951年出任埃及國家圖書館館長,后擔任了文學藝術社會科學最高理事會專職理事、埃及作家協會主席。鑒于他在文學上的突出成就,曾被埃及總統授予共和國勛章。1961年獲埃及國家獎,1978年獲地中海國家文化中心授予的最佳思想家、文學家稱號,次年又獲該中心授予的地中海國家文學獎。
陶菲格·哈基姆至今已出版11部長、中篇小說,76部劇本,以及大量的短篇小說、散文、隨筆、雜文,出版作品近100部,被譯成10余種文字,在世界上有廣泛的影響。陶菲格·哈基姆是在埃及思想文化戰線上新與舊、革新與保守的斗爭日趨激烈的新文學運動中登上文壇的,他始終自覺地站在文學革命的前列,力圖在文學作品中描寫社會生活真實的畫面和體現民族精神,從而創作了一批優秀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如標志著埃及長篇小說創作成熟的里程碑式作品《靈魂歸來》(1933)、反映民族精神的話劇《新女性》(1922)、《討厭的客人》(1922)、諷刺小說《鄉村檢察官手記》(1937)、《來自東方的小鳥》等等。陶菲格的最大貢獻還在于他在借鑒歐洲古典和現代戲劇的基礎上,從古代阿拉伯神話和希臘神話中汲取題材,融入伊斯蘭教哲學精神,創建了阿拉伯現代戲劇體系。悲劇《洞中人》、《夏哈爾扎德》、《皮格馬利翁的悲劇》等等都是以古代神話為題材,表現人類與時間、人類與物質、人類與地點以及操縱人類的某種隱然的力量的矛盾,從而表現出一種來自東方的深刻哲學思想,即相信有一種隱然的力量控制著人類和他們的活動,它懷疑理智和它的一切成果,但盡管如此,人類仍熱烈地向往理智,并力圖揭示這種隱然力量的秘密,尋找到戰勝它的力量。陶菲格劇作中這種哲學意味和優美的語言、細膩的描寫,使他在世界劇壇上占有獨特的位置。
《靈魂歸來》,陳中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
【內容提要】吃過午飯,家庭成員們各奔東西,澤努芭一個人聚精會神地用撲克牌算起卦來,沉浸在自己編織的愛情的夢幻中。
穆哈辛挾著書本,興沖沖地走了進來。他在開羅寄讀,住在叔伯家中。這是個獨特的家庭。一家之中有在小學當數學教員的伯伯哈納菲、正在大學讀書的叔叔阿卜杜胡、表叔賽力姆和仆人、姑姑澤努芭。穆哈辛與叔伯們五人同居一室,和睦相處。看見姑姑在算卦,穆哈辛以少年的純潔和戲謔的語調問她是否在給新郎算命?年近40歲的澤努芭臉紅了。的確,她正暗暗愛著住在樓下的一位男子穆斯塔發。為了掩飾自己的窘態,澤努芭提起鄰居蘇妮婭小姐掉在陽臺上的手帕不翼而飛,她料定偷手帕的人不是阿卜杜胡就是賽利姆。這下穆哈辛羞紅了臉,因為正是他偷偷藏起了蘇妮婭的手帕。
兩個月前,蘇妮婭到他家來找澤努芭,穆哈辛與叔叔阿卜杜胡、賽利姆從門縫里偷窺了這位少女,他們全被蘇妮婭如花似玉的美貌吸引了,都在想方設法得到蘇妮婭的愛。
上午八九點鐘,賽利姆像往常一樣坐在咖啡館門外,懷著豐富的感情,注視著蘇妮婭家的陽臺。坐在他后面的穆斯塔發饒有興趣地揣測著賽利姆的心情。
一個偶然的機會,澤努芭介紹蘇妮婭認識了穆哈辛,并告訴她穆哈辛有副好嗓子。蘇妮婭邀請穆哈辛到她家去,并為穆哈辛伴奏。穆哈辛以洪亮、圓潤、悅耳的嗓音唱起了歌。從此,每天下午,穆哈辛都到蘇妮婭家中去教她唱歌,他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
蘇妮婭家的電線壞了,澤努芭讓阿卜杜胡去修理。阿卜杜胡喜出望外,他對著鏡子極其興奮地把自己修飾一番,準時來到蘇妮婭家。他聽到了悅耳的鋼琴聲,琴房中衣裙的窸窸聲,從半掩的兩扇門扉間看到了蘇妮婭那一片令人眩目的連衣裙的湖綠色,目光觸及到一雙迷人的黑眼睛。阿卜杜胡容光煥發地登上修理電線的木梯,心猶如正在攀登愛情的高峰。
蘇妮婭的鋼琴出了點故障,略懂樂器知識的賽利姆當仁不讓地去給修理。他的臉上綻著微笑,穿上平時最喜歡的衣服來到蘇妮婭家。他請蘇妮婭彈琴,以便找出琴鍵的毛病。他被琴聲、更被蘇妮婭小姐美麗的面龐迷住了,全身心地沉浸在愛的甜蜜中。
穆哈辛接到父母從鄉下寄來的信,讓他利用假期回家探親。穆哈辛去蘇妮婭處告別,發現她正依著陽臺窗戶,目光投向咖啡館,順著她的目光望去,竟是穆斯塔發的笑臉!穆哈辛心里突然涌起一陣遭到冷遇后的絕望。他拿出珍藏著的蘇妮婭的手帕遞給蘇妮婭,眼里滾動著淚花。
穆哈辛坐火車回到家中,有錢的父母熱烈地歡迎兒子。穆哈辛吃著豐盛的飯菜,睡在自己專用的臥室里,一陣陣傷感襲上心頭,他懷念與叔伯們五人同居一室的生活,覺得那才是一個幸福的集體,那種集體生活縱然有種種煩惱和不幸,但卻是一種十分美好的生活。
穆哈辛到莊園去訪問,他心曠神怡地奔向田野,在天真無邪的萬物中發現了愛的存在,心中的煩惱頓時消散。他走進農舍,和農民聊天,看到農人與動物間那種質樸的感情,這一切深深激動了穆哈辛,他了解到埃及人圣潔的、天使般美好的心靈,農民中那休戚與共,同舟共濟的團結精神……
假期結束了,穆哈辛帶著豐盛的禮物回到開羅。全體家庭成員到車站來接他。他們帶給穆哈辛一個消息,就在他回家探親的這段日子里,蘇妮婭已經和樓下的穆斯塔發戀愛了!仿佛受到了致命的打擊,穆哈辛眼前一片漆黑!
阿卜杜胡全身心投入到了學習中,賽利姆再也不去咖啡館。虛假的歡樂已經煙消云散,悲哀和失望沉淀在他們心中,他們理解穆哈辛,千方百計地安慰他,希望能減輕他的痛苦。
澤努芭對蘇妮婭搶走自己的意中人懷恨在心,竟然讓仆人半夜往穆斯塔發的陽臺上扔雜物,以破壞他們的相會,但這未能阻止這對青年男女的熱戀。蘇妮婭的父母應允了穆斯塔發的求婚。消息傳出,穆哈辛和全體家庭成員沉浸在痛苦之中。
就在此時,革命爆發了。家庭成員們從個人感情的狹小天地中解脫出來,同時振作起來,投身于轟轟烈烈的革命洪流之中。穆哈辛和阿卜杜胡在學校里都成了帶頭人,每次示威游行都走在最前列。哈納菲、賽利姆也不例外,連仆人也加入了斗爭隊伍。他們家曬臺的小屋變成了秘密貯藏室,堆放著大捆大捆的革命傳單。一天,穆哈辛與阿卜杜胡正在咖啡館散發傳單時,幾名英國軍官和警察逮捕了他們,接著,又逮捕了除澤努芭之外的全體家庭成員。
五人被關進了同一間牢房。穆哈辛的父親為兒子的釋放四處奔走,而穆哈辛則明確表示,絕不愿意一個人出獄,而讓叔伯們留在這里。他以與室民同伴同甘共苦為樂。痛苦無論多大,只要五人同在,痛苦就會變小。最后,經過父親四處活動,五人同被送進了監獄醫院。他們就像在家里生活一樣,把五張床整齊地并排放在一起。
澤努芭來探望他們,告訴他們,穆斯塔發與蘇妮婭決定將在革命勝利后結婚。這樣,穆哈辛和同伴們出獄的日子便同蘇妮婭他們的喜期不謀而合了。
【作品鑒賞】陶菲格·哈基姆在談到自己的經歷時曾經說過,《靈魂歸來》中所描繪的澤娜卜區賽拉姆大街的那套住宅,書中的哈納菲、阿卜杜胡、澤努芭等都實有其人。而小說中的青年主人公穆哈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少年陶菲格。陶菲格在開羅上中學時,曾與兩個叔叔住在一起,一個是中學教員、一個是工程學校的學生,另外還有一個姑姑與他們同住。作品以他所熟悉的家庭生活為背景,但并不局限于真人真事的煩細描寫。
陶菲格早在法國讀書期間,就曾留心研究過歐洲小說是怎樣體現民族精神和人們的心理活動及社會情況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埃及社會正處于大動蕩中。謀求新思想的思想解放運動,激發了埃及人民的愛國之心和民族自豪感;爭取民族獨立的革命斗爭喚起了埃及人民的更大覺醒。在這種時代精神的感召下,陶菲格在創作《靈魂歸來》時,便以現實主義的筆法把一個家庭的生活與1919年的埃及大革命緊密聯系在一起,通過描寫普普通通人物的思想感情,挖掘出源遠流長的埃及民族精神(即靈魂。在阿拉伯語中,精神和靈魂是同一個詞)并熱切呼喚這種民族精神的歸來,因此,這是一曲民族精神的贊歌。
作品中描寫人們思想感情的第一個層次是男女之愛。陶菲格寫愛情,不是男女之間生死不渝的愛的故事,而是戀愛中的人們的情感。小說構筑了四個男子同時愛上一個姑娘這種眾星捧月般的愛情格局,揭示愛的不同情感體驗。少年穆哈辛愛蘇妮婭,這種愛是一個初陷情網的少年純潔真摯的愛。這愛中,有對未來生活美好的憧憬,也有少年男子那種特有的羞澀和含蓄。他偶然拾到了蘇妮婭的手帕,便精心保存起來,把它視為蘇妮婭的化身,對著手帕傾訴心中的愛。他去蘇妮婭家唱歌,激動不已,美好的時光使他忘卻了一切。在鄉下度假,他坐臥不安地盼望著蘇妮婭的來信,心中編織出無數愛的夢幻曲,愛情占據了穆哈辛的全身心。
阿卜杜胡也把蘇妮婭視為愛與美的天使,蘇妮婭衣裙那令人眩目的湖綠色在他心中幻化成愛的希望。這愛使他的生活充滿了勃勃生機,體內蘊藏著一種非同尋常的活力,他展開想象的翅膀,在愛情的王國里自由翱翔。
賽利姆對蘇妮婭的愛既直率又執著,從他第一次見到蘇妮婭起,就被她的美麗所吸引,以后,他每天坐在咖啡館里,盼望著能見到他心中可愛的姑娘。給蘇妮婭修鋼琴,他認為是天賜良機,便不失時機,大膽地給蘇妮婭寫情書,直言不諱地表白自己的愛情。
穆斯塔發的愛充滿了一個男子的激情。在愛中,他體會到了一種高尚的精神,這精神令他振奮和振作,從而改變了過去無所事事的平庸生活。
其實,四個人中除了穆斯塔發之外,誰也沒得到蘇妮婭的愛情,但是他們共同的追求卻表明,愛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是最美好的感情,體會到了這種愛心的人是幸福的人。
接著,陶菲格便把這種愛心進一步擴展,描寫了穆哈辛與叔伯之間所體現出來的深切的友愛。這個特殊的家庭是個和睦融洽的小團體,每個人都以能在這樣的家庭中與他人共同生活而感到由衷的喜悅。在這個小集體中,雖然也有過爭吵、嫉妒、煩惱,但仁慈、友愛是維系這個集體的無形的力量。每個人都愿意獻出自己的一份愛心,每個人又都享受了他人給予的愛。在小說的開頭和結尾,作者有意識地安排了一個前后照應的場面:一間居室,并排放著五張床,五個人同住在這里,生著同樣的病,躺在同樣的床上。前來看病的醫生對此大惑不解,而他們卻異口同聲地說:“我們喜歡這樣!”書中寫道:“你若能體會到這一點,那就一定能從他們蒼白的臉上發現一種隱而不見的、因為在一起患病而感到幸福的光芒。他們萬事與共,吃同樣的飯,也能吃同樣的藥,他們有共同的命運和遭遇。”這種家庭構成和生活看似特殊,其實卻是淳樸的埃及人民休戚與共、風雨同舟、團結友愛精神的縮影。作品中一再強調這種精神:“在我們這里,不管是科卜特人還是穆斯林,我們都親同手足。”在埃及各階層之間廣泛使用的“伊斯蘭精神”一詞,“它的詞義只是指仁慈為懷,與人為善、心靈交融的感情,人們可以在埃及發現這種感情。穆哈辛回鄉探親一段,便是陶菲格對源遠流長的民族精神詩化的描寫空氣是一塵不染、純潔的、充滿愛的氣息,田野是貞潔無瑕、天真無邪的萬物,處處有愛的存在。農舍中,漂亮的小牛與胸無邪念的乳兒同在母牛腹下吃奶。大地上,收割的農民融于綠色的波浪,他們吟唱著埃及古老的民歌,眾口一詞,每個人的臉上都滿懷希望,心中有著同樣的感情和信仰……人與人之間、人與大自然之間、人與動物之間,構成了一幅和諧的圖畫,這宇宙渾然一體的感覺,“是天使們的感覺,也是古埃及人這個古老的人民的感覺”,“具有圣潔心靈的天使般的埃及人難道不是還生活在埃及嗎?他們不是在世代相襲地、不知不覺地繼承了萬物一致的感情嗎”?作者頗為自豪地宣稱:這團結一致,同種同類,甘愿受苦,甘愿犧牲的人民,除了金字塔之外,還會創造出其它奇跡!
這種精神是民族的凝聚力。當1919年埃及革命爆發之后,穆哈辛與叔伯們這些普普通通的人立即投入了保衛祖國的革命洪流中。情愛、友愛,種種愛的情感升華為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正在失戀痛苦中的穆哈辛立即從個人情感中擺脫出來,“他內心里因為受到殘忍對待而破滅的全部愛情,已經變成熾熱的愛國主義熱情……他準備為心里的神靈作出犧牲的那種感情,全部變成了甘愿為祖國的神靈作出大膽犧牲的感情”。阿卜杜胡和賽利姆也同樣,他們的郁悶和孤寂一掃而光,代之以關注,奮斗和熱情。在轟轟烈烈的革命面前,愛國主義的強烈感情占據了他們整個心靈,他們顧不上任何其它事情,甚至顧不上這危機環境里的安全。平時埋頭書本中的哈納菲先生毫不猶豫地參加游行,他們的仆人也加入了保衛祖國的行列,搗毀路障、挖戰壕,用大棒小刀把自己武裝起來。整個埃及沸騰了,人們表現出非凡的英雄氣概,用生命和熱血,譜出了一曲同仇敵愾的愛國主義頌歌。
陶菲格力圖證明,埃及人民蘊藏著創造奇跡的巨大力量,這種力量,使他們能夠永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靈魂歸來》是埃及長篇小說創作成熟的里程碑,標志著埃及小說“黎明時期的結束”。作品無論從內容到形式較當時的文學作品都有重大突破。首先,它一反當時埃及文壇上盛行的懷古傷感和虛無主義的傾向,以現實主義的筆法,通過對生活的真實描繪而挖掘出深刻的內涵,從而把寫實與理性的思考巧妙地融于一體。如穆哈辛回鄉探親一段,作者把一幅幅真實的生活畫面與穆哈辛的思考連在一起,以夾敘夾議的方法進行描寫,這些議論無乏味冗長之感而具畫龍點睛之妙,既推動了情節的發展,又把思考引向深入,從而突現作品的主題。
另外,作者還善于構想富有戲劇性的情節和場面。穆哈辛、阿卜杜胡、賽利姆偷戀蘇妮婭,又分別以唱歌、修電線、修鋼琴得以與蘇妮婭會面,頗具戲劇性。三家相鄰的陽臺上所導演出的一個個愛情故事,更像是戲劇中一幕幕場景,富有立體感和形象感。小說的語言平實、質樸。
《靈魂歸來》自1933年出版以來,曾被譯為法、意、英、俄、德等多種文字,引起西方文壇的高度重視,成為世界聞名的阿拉伯文學作品,陶菲格·哈基姆也因此被尊稱為“埃及現代小說的先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