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解讀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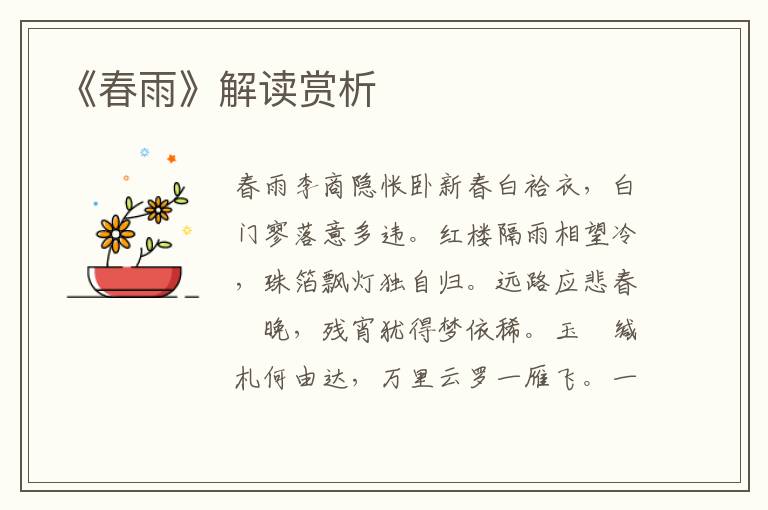
春雨
李商隱
悵臥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
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dú)自歸。
遠(yuǎn)路應(yīng)悲春晼晚,殘宵猶得夢(mèng)依稀。
玉珰緘札何由達(dá),萬里云羅一雁飛。
一
穿著素服惆悵躺臥新春之夕,白門客居諸事不順情緒低迷。
隔著細(xì)雨遙望紅樓備覺凄冷,云母燭光透出雨簾伴我獨(dú)歸。
春日將暮流年似水君門萬里,拂曉醒來短暫相會(huì)夢(mèng)也迷離。
玉般情意如何寄到你的身邊,山高路遠(yuǎn)陰云密布一雁孤飛。
二
李商隱(約813—858),字義山,號(hào)玉溪生。祖籍懷州河內(nèi)(今屬河南),生于河南滎陽(今河南鄭州)。九歲,父親去世,守孝三年。為了養(yǎng)家,幫人家抄書,給人家舂米,維持一家的生活。同時(shí),他仍然堅(jiān)持苦讀,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
十九歲,李商隱遇到人生第一個(gè)恩師太平軍節(jié)度使令狐楚,并在他的指導(dǎo)下寫作社會(huì)流行的駢文。二十六歲,得到河陽節(jié)度使王茂元的賞識(shí),娶了王茂元的女兒。這卻觸犯了當(dāng)時(shí)“牛李黨爭(zhēng)”的大忌。
李商隱的恩師令狐楚屬于牛黨(領(lǐng)袖人物是牛僧孺),而岳父王茂元?jiǎng)t屬于李黨(領(lǐng)袖人物是李德裕)。李德裕是唐武宗時(shí)的宰相,比較有理想、有作為,提拔了包括王茂元在內(nèi)的不少孤立無援的寒門后進(jìn),并削弱宦官的權(quán)力與藩鎮(zhèn)軍隊(duì)的勢(shì)力。后被貶崖州(今海南)。
令狐楚一派對(duì)李商隱頗為不滿,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绹后來做了宰相,對(duì)李商隱從不加以援手。
令狐楚、王茂元先后卒,李商隱長(zhǎng)期在幕府之中做事,給地方長(zhǎng)官寫公文和應(yīng)酬的文字,以此為生。
公元849年秋天,李商隱赴武寧節(jié)度使(駐徐州)盧弘止幕下,任入幕以來最高職務(wù)“侍御史”。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春天,賞識(shí)李商隱的盧弘止在任上病逝。此時(shí),李商隱的妻子王氏也病危,隨后在春夏間病逝。這首詩當(dāng)是作于春天盧弘止去世與王氏病逝之間。
“虛負(fù)凌云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李商隱胸懷遠(yuǎn)大的政治抱負(fù),但時(shí)代卻沒有給他實(shí)現(xiàn)的機(jī)會(huì)。他寄人籬下二十年,一生糾結(jié)于政治派別的苦痛中,始終過著輾轉(zhuǎn)漂泊、遠(yuǎn)離家人的生活。公元858年病逝,時(shí)年四十七歲。
三
這首詩是李商隱在一個(gè)飄雨春日的自語,由于它在詩集中未系編年,如同李商隱眾多撲朔迷離的無題詩一樣,更給賞析增加了難度。
“悵”,是詩人的心理定位。一個(gè)“悵”字,表現(xiàn)出悵惘哀傷的感情格調(diào),統(tǒng)領(lǐng)全篇惆悵的詩意。“悵望江頭江水聲”。
“臥”,是作者的物理定位。“臥”表動(dòng)作,說明早上未起,將起未起之時(shí)。臥,必不是晚上,以李商隱詩心,不會(huì)把正常的動(dòng)作,夜間之臥入詩。詩人習(xí)慣用這個(gè)字來表示自己那種無可奈何、身不由己的無力感:“有人惆悵臥遙幃”、“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后清宵細(xì)細(xì)長(zhǎng)”。
一“悵”一“臥”,卻是在生機(jī)勃發(fā)的“新春”,正形成鮮明的對(duì)比。也許外面寒冷,怕冷而不起床,欲起之時(shí),所以著袷衣?lián)肀欢ɑ蛘吲P)。
“袷衣”,即單衣。《說文》:“袷,衣無絮。”“白”,有寒冷的色調(diào)。“白袷衣”,是在床上仍著單衣,亦是初春乍暖還寒的樣子。“白袷衣”,還提供了另一個(gè)重要線索,這就是歷代注家沒有注意到它是指喪服。據(jù)元代馬端林《文獻(xiàn)通考》載:“拜陵則黑介幘,服無定色。舉哀臨喪,白袷單衣,亦謂之素服。”當(dāng)然這是元代習(xí)俗,唐未必如此,姑存此待考。
“白門”,點(diǎn)出地點(diǎn),而兩用“白”字,不避重復(fù),必實(shí)有其地,且愈顯其冷。“白門”何在?歷代注家沒有達(dá)成共識(shí),有金陵(今江蘇南京)、徐州以及“男女幽會(huì)之地”幾種說法。細(xì)察作者生平與詩意,此處“白門”似指徐州。
“青樓”,漆成青色的樓,為古代女子居處的通稱。作為紅樓實(shí)體前身的“朱樓”,在六朝時(shí)已出現(xiàn)在金陵石頭城。南北朝時(shí)期謝脁有《入朝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南朝時(shí)候富貴人家用“紅樓”。“紅樓”,當(dāng)時(shí)富貴人家居住之所。林徽因曾考證,中國(guó)唐代建筑的外觀與色彩,在木構(gòu)部分一律刷紅。在詩詞中,紅樓一詞最早也是出現(xiàn)在唐詩。李白在年少漫游金陵時(shí)也寫道:“地?fù)斫鹆陝?shì),城回江水流。當(dāng)時(shí)百萬戶,夾道起朱樓。”由此可見,南北朝時(shí)期金陵已是處處紅樓畫梁雕棟的繁華之地,紅樓是當(dāng)時(shí)金陵豪富之家修建的豪宅。
“珠箔”,珠簾,以珠子串線,織組成簾。是用云母做出來的珍珠顏色的燈,蠟燭點(diǎn)在中間,常常是在有風(fēng)雨的夜晚,因?yàn)樗容^不容易被風(fēng)吹滅。《紅樓夢(mèng)》里,賈寶玉去看薛寶釵,林黛玉也過去,臨行點(diǎn)的燈就是這種“珠箔”。
“萬里云羅一雁飛”。詩人雖身處逆境,也不甘沉淪,有這樣一種精神。
四
在新春初至乍暖還寒時(shí)候,偏偏又飄起了細(xì)雨。詩人穿著單薄的白色喪衣,舉哀臨喪完畢回到寓所,不堪春寒,悵臥床上。
春雨細(xì)密,在燈光的映照下,雨絲猶如飄動(dòng)的珠簾。春雨也是時(shí)間的表征,是“意多違”的觸媒,是紛亂如雨的思緒。一生漂泊,好不容易安頓下來,賞識(shí)自己的幕主卻遽然離世,而聚少離多的妻子也傳來病危的消息,青年時(shí)期的好友令狐絢身居相位卻始終帶著對(duì)自己的誤解不加援引。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怎能不感到十分的落寞與無奈。
回想起白天在幕府紅樓送葬黯然歸來,白衣與紅樓,對(duì)比多么鮮明,觸目何等凄涼。紅樓隔雨,隔開的不只是空間距離,也是生死永隔。曾經(jīng)賞識(shí)自己的令狐楚、王茂元、盧弘止都走了。
人去樓空,艷麗的紅樓在春雨中顯得如此冷漠。雨打在身上很冷,可是心上更冷。這“冷”是離別的悵惘,心境的寥落,前途的迷茫,更是相思的凄楚與絕望。
山高路遠(yuǎn),天意難問。人間之路,再遠(yuǎn)亦能到達(dá),可是黃泉路遠(yuǎn)呢?今年正好是不惑之年,年歲已長(zhǎng),還在跋涉。春日遲暮和“年歲之不我與也”的惆悵無法排遣,只有借助依依不舍的夢(mèng)境相會(huì)才能稍慰思念。可是夢(mèng)里關(guān)山萬里,卻難到達(dá),何況醒來?
古人只要意氣相投,就能解佩相贈(zèng)。可是,“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依之親”,自己就像失群的孤雁,即使解下佩玉封好書信,又能穿過層層云羅帶去無奈而又無盡的思念嗎?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春雨》由春雨生發(fā),卻不僅僅寫春雨,傷春傷時(shí)更自傷身世,里面有李商隱的生命與精神,包含了他一生漂泊的全部感受。
五
由于情感方面的悵惘哀傷和表現(xiàn)手法上的惝恍迷離,李商隱詩素以難解著稱。前人曾慨嘆,“一篇錦瑟解人難”,“詩家總愛西昆好,獨(dú)恨無人作鄭箋”。
李商隱的錦瑟,蘇軾、黃庭堅(jiān)、元好問、王士禎都搞不清意思。李商隱晚年編輯自己著作的時(shí)候,把這首詩置于卷首,看出對(duì)這首詩的珍愛。張采田說:“此為全集壓卷之作。”有以詩代序的意味。
一篇《錦瑟》解人難,我們?cè)囉谩洞河辍穪碜鹘忾_李商隱心靈世界的一把鑰匙。
正如《春雨》一會(huì)兒早上,一會(huì)兒下午,一會(huì)兒晚上,乃是一天到晚,甚至夢(mèng)中,思念不停。《錦瑟》實(shí)跨春夏秋冬四季,為李商隱一生縮影。《春雨》是《錦瑟》的一面鏡子。
李商隱在《錦瑟》中確實(shí)擷取了四季佳景,(四時(shí)心情)詩人詩心,于四季變化中殊為明顯。
《錦瑟》是借瑟起興,五十弦,顯得弦聲密集,“雨打湘靈五十弦”(《聽雨夢(mèng)后作》)。
“歸來已不見,錦瑟長(zhǎng)于人”。有生命有感情的妻子已經(jīng)死去了,但她生前彈過的沒有生命沒有感情的瑟還留在這里。
一弦一柱,代表音樂,以部分代全體。以音樂帶到華年(過去)。都曾有過往的生命、感情和心靈。
《史記》說,五十弦是古制,不時(shí)尚,自己是不為世人所欣賞的,如同那個(gè)“不愛風(fēng)流高格調(diào),共憐時(shí)世儉梳妝”的女子。
“華年”是最美麗的青春。以弦斷比妻之亡逝。一說弦本來二十五弦(《莊子》、《淮南子》),因時(shí)間太久,已經(jīng)斷裂,故成五十弦。
自宋至清,大致有“令狐青衣”等十四種解讀。近代以來,主要有“自傷身世”、“悼亡”二說。
“思華年”,顯是追憶之作,這是總詩眼,下面分述少年、青年、壯年、暮年。寫一生。
莊生,最突出的是有才,李商隱有自信,常以司馬相如自比,虛負(fù)凌云萬丈才。自比莊生,莊子是河南的,隱令狐绹教育李商隱。
“曉夢(mèng)”,早晨的夢(mèng)。在河南初會(huì)令狐楚的時(shí)候,從古文改學(xué)今文,是一個(gè)惘然。“曉夢(mèng)”極言其短。“迷”,就是沉醉迷戀。“曉夢(mèng)”,夢(mèng)醒了,仕途無望。
盧弘止請(qǐng)他到幕府去做官,因?yàn)楸R弘止同情他在秋天寒冷的書齋之中只能空空地夢(mèng)蝶。“憐我秋齋夢(mèng)蝴蝶”(《偶成轉(zhuǎn)韻七十二句贈(zèng)四同舍》),“夢(mèng)蝶”在李商隱的詩中是代表對(duì)于仕途的一個(gè)夢(mèng)想。“夢(mèng)蝶”是秋天。
“春心”是春天。“望帝”,丟失故國(guó);詩人,丟失精神家園。丟失愛人。望帝春心,隱四川,巴山夜雨。
春心,追憶過去,理想不泯。望帝春心,在四川幕府,巴山夜雨的時(shí)候,也是一個(gè)惘然;“春心”在李商隱的詩里表示相思、愛情。“春心莫共花爭(zhēng)發(fā),一寸相思一寸灰”。
滄海,遠(yuǎn)。聯(lián)系李德裕和《淚》,遠(yuǎn)貶海南。古人用滄海遺珠來比喻人才埋沒。遺珠之嘆壯年時(shí)。
滄海里邊最美麗的珍珠,沒有被人選擇,所以哭泣,是失落的哭泣,被棄的哭泣。李德裕到海南,淚,青袍送玉珂,也是惘然;“滄海月明”是夏天。月明,冷。“滄海月明珠有淚”說的是李德裕死在崖州。崖州是浙江海邊一個(gè)地方。滄海月明,心系李德裕。賞識(shí)李商隱的李德裕,遠(yuǎn)在天涯海角。
日,常指君王。玉,又可能是君子。藍(lán)天日暖,短暫的京華美景美夢(mèng),已成往事。藍(lán)天日暖,隱朝中時(shí)刻。“藍(lán)天日暖”是冬天。初進(jìn)朝廷,后長(zhǎng)期為幕僚。在中國(guó)舊日的傳統(tǒng)中,在中央政府任職是好事,外放到別的地方就算落拓江湖,何況是在地方做幕僚。
藍(lán)田,在長(zhǎng)安南,自己是寶玉,無人采,只有玉之精氣上升。卞和懷玉,懷才不遇。暮年,一生懷才不遇。日暖,熱。
先作此解,仍不自信,姑存于此。
六
江山不幸詩人幸,或許也正是這種糾結(jié)成就了李商隱詩的獨(dú)特風(fēng)格。
按照中國(guó)舊日士大夫觀念,令狐楚算是李商隱的恩主,王茂元又是李商隱的岳父,都是最親近的人,都得不到他們的諒解,這種怨恨,這種感情很難直接地寫出來。
李商隱對(duì)于宦官,對(duì)于藩鎮(zhèn)的不滿,也不好直接說出來。對(duì)皇帝的不滿更是不敢言。所以李商隱的詩晦澀難懂。
李商隱早年就有“欲回天地”的遠(yuǎn)大政治抱負(fù),然而終其一生,都是為人幕僚。側(cè)身迎送,精神上極其痛苦。
李商隱的詩有一種“內(nèi)力”,有一種感動(dòng)、吸引人的力量,類似牛頓的萬有引力。
李商隱關(guān)心國(guó)家,關(guān)懷人民,可是平生沒有一個(gè)機(jī)會(huì)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抱負(fù)。他和杜甫一樣,是出自肺腑的,把別人的痛苦當(dāng)成自己的痛苦一樣寫出來。如果真正從打動(dòng)讀者的感發(fā)力量來說,李商隱才是真正繼承了杜甫。
李商隱是由盛唐中唐的向外,轉(zhuǎn)向晚唐的向內(nèi)關(guān)鍵人物的決定性階段。形式的完美說明藝術(shù)創(chuàng)作已經(jīng)達(dá)到一個(gè)狀態(tài),必須在形式上作出改變,于是“詞”的形式在民間出現(xiàn)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