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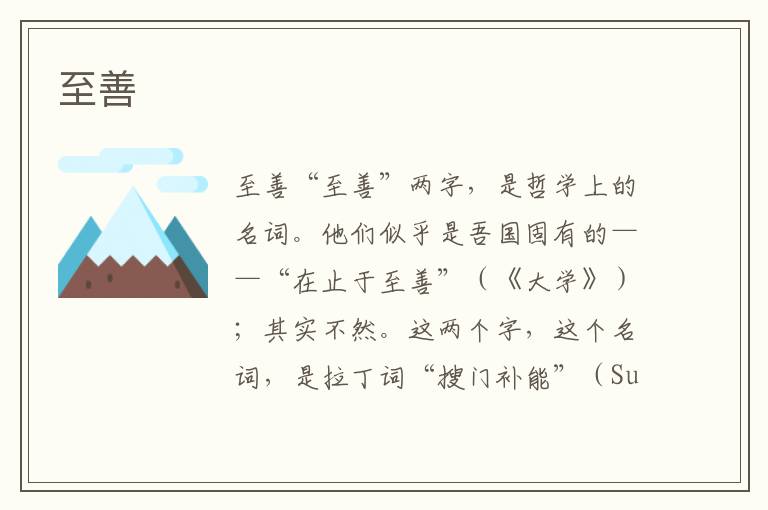
至善
“至善”兩字,是哲學上的名詞。他們似乎是吾國固有的——“在止于至善”(《大學》);其實不然。這兩個字,這個名詞,是拉丁詞“搜門補能”(Summum Bonum)的譯意;“搜門”作“極”或“至”解,“補能”作“佳”或“善”解,“至善”的確義如下:一切美德美物的總匯,即一切美德美物所自出的根源。
我今先借這個哲學名詞,來講我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
(一)衣。穿大布衫褲的鄉民,以為改服西裝之后,一定舒適,一定美觀,一定受人尊敬。他們以為西裝是衣服之至善。靠了它非獨可以表示摩登,并且可以得到地位。不知冬天西裝太冷,非有火爐不可;夏天西裝太熱,非有電扇不可。社會上的地位隨學問經驗而來,絕非西裝所能為助。我們雖然有“只重衣裳不重人”的那一句古話,但是實行此“主義”者,只有勢利小人。規規矩矩辦事的人們,斷不專重服裝而不問品學的。因此可知西裝不是至善。至善的服裝,是舒適的服裝。
(二)食。我們還是吃魚好,還是吃肉好?我們還是天天吃便飯的好,還是日夜吃筵席的好?一般人當然以為吃葷比吃素好,吃筵席比吃便飯好。其實,好的米飯,較劣的面包為佳,新鮮的素菜,較陳腐的魚肉為佳……筵席不一定為食的至善。
十二年以前,在某某兩個月中,我白天吃西菜,晚上吃筵席。并且我不論日夜,總是“鬧酒”,不吃飯。這樣的“應酬”了五十余天,我大病了——腰酸,背痛,腳軟,并且便血。醫師對我說道:“你要休息。不可天天這樣應酬。你每天吃的,葷多素少,酒多飯少,所以你要生病,你要便血。”照這樣講,我們中國人,每日三餐,非吃粥飯不可;否則即病。但是為什么求仙的道家要辟谷呢?辟谷,就是不食米類,不吃粥飯。道書云:“神仙以辟谷為下,然卻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入道。”我(舊時)以筵席至善,醫師以米食為至善,道家以卻粒為至善。究不知何者真為至善。我們中國人,究以何種食物為至善?究以何種食物最為適合,最多滋養?
(三)住。目下上海房屋大成問題;目下只有到上海來的人,沒有向外埠去的人。我們有了儲鈔,找不到房屋。就是找到了,一間統廂房的“頂”費,也要十萬八萬;至于單幢三層樓,加一個現成電話,恐怕非五、六十萬不可。大家都是馬馬虎虎地躲身而已。哪里還談得到——住?
然而住是應該研究的。我們還是住在城中的好,還是住在鄉間的好——還是留申的好,還是還鄉的好?我們還是住平房的好,還是住樓屋的好?我們還是住在樓上的好,還是住在樓下的好?我們還是住中式石庫門好呢?還是住西式大洋房,大公寓好?……這許多問題,倘然細詢一百個人,一定可以得到一百個不同的回答。為什么呢?因為每一個人的心,各有他的一個至善——住的至善。人心不同,所以至善也不相同。我的至善呢?我以空氣足,交通便,不喧鬧為至善。然而這不是他人的至善。
(五)行。除走路外,我們的行,包括騎馬乘車——電車,汽車,人力車,獨輪車。真的,我們還有飛機。
自己用腳走路的人,以為乘了車可以“隨心所欲”,要到哪里是哪里。坐汽車當然比較軋電車,比較叫人力車好得多,快得多。但是危險也比較大些。別人碰了我,我有性命之憂。我碰了別人,不是賠錢,定是訴訟。所以乘汽車,并非行的至善。飛機呢?飛機近處沒有用,遠處沒有空,買不到票——也不是行的至善。那末,什么是行的至善呢?我看我們還是自己走路的好,或者軋電車也好——危險較少,責任較輕。走路或軋電車,是我現在的至善。別人當然不是這樣想的。
上面所講的,無非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不是哲學,與哲學全無關系。提到哲學,哲理,事情大了。哲學家的派別極多;因此他們的至善(哲理)也狀大異。有的以道德為至善;有的以樂觀為至善;有的以自然為至善;有的以忠實為至善;更有以求智識,求自由為至善的。各派所說,各派所主張者,皆極有理。我們應該學哪一派呢?我們真是無所適從。我有一譬;譬之請客。我所邀請者,張,王,佘(從人從示)三人。他們嗜好不同。兩位要喝酒,一位反對。兩位喜魚,一位喜蝦。叫我怎樣辦呢?請閱下面不文不白,不詩不歌的七言韻語:
三個客人來我家,
姓王姓張又姓佘。
我留他們吃便飯;
大家都說“倒不差”。
張、王嗜肉嗜狂飲,
佘姓搖頭且悲嗟。
張、王兩君喜食魚,
惟有佘公要吃蝦。
彼此好尚全不同,
你南我北大喧嘩。
出錢破鈔東道主,
只得呆坐裝傻瓜。
請客吃飯,比較研求哲理容易。客人喜食的,我都要了;他們當然可以滿意。他們要魚要肉,要蝦要酒,我一一齊備。人人得到他所好的,當然人人愉快。但是研求哲理,研求至善,不能這樣的。所謂至善者,單而不變,一而不二。我們只能信仰一種哲理,我們只能尋求一個至善。我們還是吃蝦呢?還是吃肉?我們還是飲酒呢?還是禁酒?……我們還是求快樂呢?還是求自由?我們應該忠實呢?還是應該“滑頭”?我們應該受教育,力求智識呢?還是應該不讀書,一世愚笨?……到底什么是我們的至善?
哲學鼻祖蘇格拉底以順從國法為任何人民的至善。但是國法亦何嘗不變?今日視為至善者,明日已成禁令。例如:科舉盛行之時,八比(股)文與試帖詩,皆為世子的至善。后來變法自強(?),經義策論,成為至善。更后來廢科舉,興學校,非獨八比試帖無用,連經義策論也打倒了。國法改變之例甚多;我非歷史專家,不能多舉,亦不愿多舉。不過我知道順從國法,是很不容易的事。倘然這是至善,那末人民苦了——苦了!我出此言,意在“攻擊”蘇氏。請閱眾勿疑我為無政府主義者。我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公民。我批評蘇氏,意在說明選擇至善之難。我們的至善,我們處事之法,究以何者為最合宜呀!我們研以何者為至善呀!
我希望吾國學者,或外國學者,快快集合世界上的哲學家,編成一紙名單,開列他們所主張的處世法(至善),并且注明他們的信從者所得的結果。那末,我們一看,就可以明白,就可以擇善而從;不必東摸西索,也能求得至善。從前有一位比國學者,曾經試行此事。不過他沒有完全成功;他還偏心,且只做了一小部分的工作。
原載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文友》第三卷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