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不可諸葛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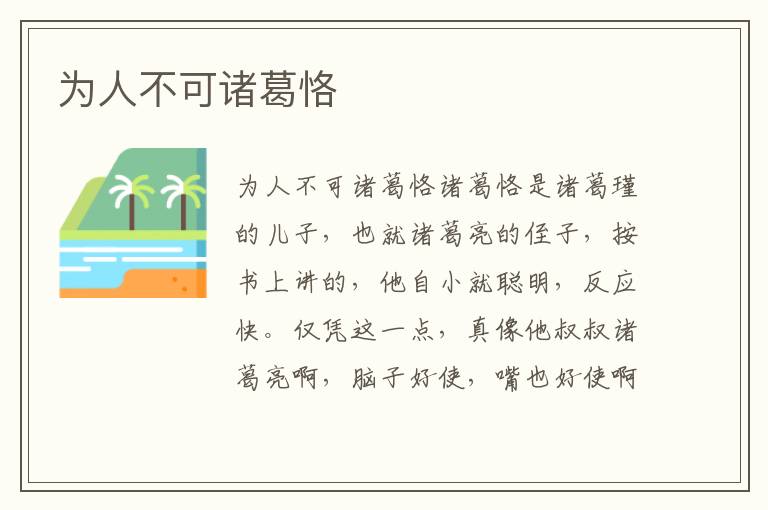
為人不可諸葛恪
諸葛恪是諸葛瑾的兒子,也就諸葛亮的侄子,按書上講的,他自小就聰明,反應快。僅憑這一點,真像他叔叔諸葛亮啊,腦子好使,嘴也好使啊。剛剛讀到這個人物時,真讓后來人羨慕啊,看看人家,嘖嘖!這遺傳基因!
現在民間還留有他許多聰明伶俐的傳說,比如,他六歲時,跟著父親諸葛瑾(字子瑜)上朝(不大明白,古代上班還可以帶小孩兒?),孫權愛開玩笑,一時來了興致,便拿諸葛瑾逗悶子,取笑諸葛瑾臉長,還即興讓人拉來一頭小毛驢,用粉筆在驢臉上邊寫了“諸葛子瑜”,眾人哄堂大笑。諸葛恪不慌不忙把粉筆拿過來,在下邊添了兩個字,就成了“諸葛子瑜之驢”,眾人皆驚訝,“這孩子真聰明啊,諸葛家有福氣啊,怎么生了這么個聰明兒子呢。”孫權也喜歡他了,“這孩子行啊,聰明啊。長大人準有出息。”就把這毛驢賞給了諸葛恪。類似這種表現諸葛恪智慧的傳說,還有許多。如果當代人有了這么一個寶貝孩子,那臉上還不得整天笑啊,還不得笑“爛”了啊。是啊,這種孩子根本不用上什么英語提髙班、奧林匹克班種種,人家是天生的啊。可是,諸葛瑾一點兒也不高興,他還擔心呢,這個當爹的,還總嘆息“這孩子啊,不行啊,將來不是保家的人啊。”這絕不是諸葛瑾謙虛,也絕不是諸葛瑾賣乖,他的話,果然讓后來的事實驗證了。諸葛恪果然連累全家都沒得好死。知子莫如父,還是諸葛瑾看得明白啊。
中國信奉神童,也推崇神童,中國人不是有句話嗎,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你長大什么樣兒,小時候就能看出來。其實,中國古人還有句話,“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翻譯過來就是,你小時候是個機靈鬼,長大了可能是一個大傻瓜。
什么叫聰明人,按照生活慣例,聰明人的第一個指標,往往在嘴上。也真應了老百姓那句話:好馬在腿,好漢在嘴。什么意思?出來混世界,你得能說啊。怎么叫能說?你先得腦子轉得快,人家轉一圈,你得轉三圈;你嘴皮子還得利落,人家說一句,你得說十句。你說你聰明,可是你的嘴皮子不行,笨得跟棉褲腰似的,人家說十句,你一句也說不出來,盡管你是博士后畢業,盡管你會八國外語,外國人都考不住你,可是能說你聰明嗎?
說一件舊事,談歌有一個同學,叫什么就不說了。順著諸葛恪這個例子,姑且叫他小諸葛吧。小諸葛從小聰明,“文革”前上小學的時候,老師提問,大多數的時候都是他搶答,而且總是都答對了。聰明啊!老師夸,同學夸,家長也髙興啊。他也就落了一個“神童”的稱號。一轉眼,就到了“文革”,這位神童剛剛上初中,別的同學還懵懂著呢,“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兒啊,可是他早就看準了方向,“我得積極參加啊!”有人勸他,“你先看看再說,你爸爸還是走資派呢。”他說什么?“我得跟我爸爸劃清界限。”得,他起來造反了,參加了批斗他爸爸的大會,還帶頭喊口號,堅決打倒他爸爸。《毛主席語錄》一百多頁,他能倒背,而且如流。一來二去,他在學校當了一個紅衛兵的頭頭兒。這一造反,他就更紅了,而且他的嘴能說會道,很快就出名了。結果,別人下鄉,他被當做造反派積極分子留城了,到了工廠,成了工人階級一員,又很快當了干部。在廠里,他整老干部,跟整小雞子似,整得老干部們沒法干工作了。這么說吧,“文革”當中,緊鑼密鼓,他步步都沒有踩錯了,可是他千算萬算,就是沒算準,“文化大革命”能夠結束,他成了“三種人”。檢查交待了幾個月,幸虧他沒有人命,總算過關了。只落了一個開除黨籍,留廠察看。又別別扭扭干了幾年,小諸葛就別別扭扭地提前退休了。前幾年,同學們在一起聚會,他也來參加,幾十年過去了,他還是那種“神童”的樣子,聰明勁兒不減當年。嘴皮子還是噼里啪啦,炒黃豆似的。可是大家都聽出來了,他的知識結構都已經老化了。或者說,他還生活在當年的時間表里,一張嘴還都是紅衛兵的詞兒呢。時代進步,小諸葛就一直沒有倒過時差來喲!有人感慨,小諸葛啊,就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所以說,聰明人,并不是天下的事情你都懂。老子講,“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辯者不善,善者不辯;博者不知,知者不博。”大凡聰明者,絕不是諸葛恪這樣子的,好家伙,又能說,又能狡辯,一張嘴,天底下沒有他不知道的事兒,沒有他講不出來的理兒。這不叫機靈,這叫“抖機靈”。這也不叫聰明,這叫“瞎聰明”。
咱們接著說諸葛亮這個“聰明”侄子。
孫權用“開心辭典”的方式問過他,“諸葛恪啊,你說說看,是你爹聰明優秀呢,還是你叔叔諸葛亮聰明優秀?”孫權這個題目出得有點兒損,什么意思嗎?非讓諸葛兄弟二人評選出一個傻瓜來?為什么讓人家諸葛兄弟二人對決呢?你怎么不說你孫權與孫策誰更聰明優秀呢?這是個難題,怎么回答都不對。可是諸葛恪馬上回答了,“這道題容易啊,孫領導啊,這還用問么,當然是我爹聰明了。您別急,不是因為我爹是我爹我就向著我爹,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我爹知道為誰服務,我叔叔不知道啊。換句話說,我爹知道您是好領導啊,我叔叔諸葛亮不知道啊,他還跟著那個破劉備整天瞎干呢。要我看啊,他那一肚子書真是白讀了。”孫權高興了,“嘿嘿,諸葛恪,你回答得好啊,給你加十分。”諸葛恪真是答對了?答對什么啊,就沖諸葛恪這個答案,就值一百個大耳光子!諸葛恪這就是拍馬屁嘛!為了取悅孫領導,不惜貶損他的親叔叔諸葛亮。再有一次,孫權的兒子(太子),大概也看不慣諸葛恪了,當面罵他:“諸葛恪啊,我看你小子就是吃馬糞的。”這話太難聽了,吃馬糞的人還是人嗎?這孫領導的兒子也真是仗勢欺人,你對諸葛恪有意見,你可以提嘛,正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都可以,你怎么能張嘴罵人呢?或許也是諸葛恪真把太子惹急了,否則,太子也不會罵這樣的臟話。這種臟話罵到誰頭上,也得生氣。你猜諸葛恪怎么樣,他一點兒也不生氣,他還笑嘻嘻地回答呢,“孫少爺,您說的沒錯啊,我就是吃馬糞的,那您就是吃雞蛋的。”孫權在一旁聽著奇怪了,“哎,我說諸葛恪啊,你怎么回事兒呢?你怎么聽不出好賴話呢?太子罵你吃馬糞長大的,你怎么說他吃雞蛋呢?”諸葛恪就等著問呢,他笑了,“孫領導啊,您想啊,這兩種東西都是從一個地方出來的嘛!”得,又把孫權給逗樂了。太子,肯定氣得肚子都疼轉筋了。行了!服了!諸葛恪這小子真能腦筋急轉彎啊。這種例子還有許多,足以證明諸葛恪是一個腦子活,心眼兒多,而且嘴上不吃虧的人。這樣的人真的不吃虧嗎?
古話講,“大智若愚”。意思是說,人聰明可以,但是不可以表面上也聰明,生活中聰明人適當裝得傻一些,好生存。老百姓講,聰明不可以使盡。也是這個道理。隨便打個生活上的比方,您如果上菜市場買大白菜,一棵白菜才幾個錢兒一斤呢?如果那錙銖必較的菜販子精得跟鬼似的,嘴皮子呱唧呱唧的倍兒能說,秤桿子上耍得不僅是斤斤計較,都跟你兩兩計較了,秤桿子剛剛高了一點兒,他就嚷嚷得驚天動地,“哎呀,我賠了!我都賠得掉底兒了!我們這生意還怎么做呢?”你如果還想讓他饒上你一頭蒜,一棵蔥,那你是做夢呢。他更得喊了,“哎呀,你還讓我活嗎?我這都賠死了。我們也得吃飯啊,你們這買菜的以為我們容易啊?”得,您買他一棵白菜,他能跟你矯情一火車廢話,你還想買他的菜嗎,或者說,你還樂意跟他打交道嗎?
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們,凡是這種仗著自己的小聰明,處處要占上風頭,話里話外,處處讓別人難堪,這樣的人,肯定招人忌恨啊,你想啊,周圍的同事,都恨你這張嘴,就你能說?就你反應快?行了,別著急,有你哭的時候。這種人啊,很難長久。談歌的朋友老李講過這么一位,說他們單位就有這么一位副科長,嘴皮子太溜了,您說什么,他都能接上下句,甭管接得對與不對,甭管驢頭還是馬嘴,比如,你說原子彈,他就插嘴說茶葉蛋;你說布什,他就說洗衣粉;你說你兒子昨天結婚了,他就敢插嘴說他家的哈巴狗昨天剛剛生了一窩兒;你說你家老爺子明天過生日,他就敢說薩達姆沒活到七十,就被絞死了……總之,他嘴里全是說辭兒,常常弄得你下不來臺。他能說會道啊,十八個郭德綱捆在一起,也杠不過他。久而久之,大家都煩他了,誰也不愿意跟他搭腔兒,是啊,話頭話尾,誰也別想占他的便宜。有一年年底考評,大家把他選下去了,副科長的位置也丟了。老李說,這個人就是嘴上太缺德了。招了眾怒嘍。唉!犯得上嗎?再舉一個外國的例子,說,有一位先生上飛機,之前去了一趟洗手間,有人閑說話兒,說,這洗手間里有監視器,藏在誰也找不到的地方,他不服,“什么?找不到?那是你們笨!看我的!”于是,東找西找,四下里搜尋,終于在某一個不起眼的地方,被他發現了,他得意極了,“哈哈!怎么樣?就沒有我找不到的。”結果,服務生告訴他,“先生,很遺憾,您乘坐的航班,已經起飛了。”這種人,跟上邊說的那位副科長一樣,已經超出了聰明的范疇,屬于逞強好勝之徒了。經常耽誤正事兒啊!比如,光顧夸獎他的水杯了,水喝了,藥片忘吃了!再比如,飯桌上,只顧上講他胃口好,從來不便秘,不拉稀,把別人的胃口都倒了。這種人,談歌真見過不少。
什么叫逞強好勝?就是不服氣啊!天底下什么事兒,他都不服。這還能有好嗎?諸葛瑾或許想到了這一點,才替寶貝兒子擔心的。
有人講過,凡是神童,大多沒有好下場。為什么?社會對這種孩子太嬌生慣養了,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生活的曲折與艱辛,只是一味地逞能較勁,還能不撞南墻嗎。如果只是撞撞南墻,也就罷了,頂多弄幾塊創可貼的事兒,可是如果撞厲害了,就得把小命搭進去了。與諸葛恪同時代的還有楊修、孔融二位,也是神童啊,聰明!后來也都讓曹老板給殺了。往后再數,明朝出過一個名叫解縉的,也是從小神童,就被破格提拔起來了,朱元璋很喜歡他,真把他當成了人才,當下沒用他,讓他回家歇著去,意思是給下一任皇上儲備人才。新皇帝上臺了,他可是受到重用了,可是他仗著自己的聰明,絕不能“埋沒”自己啊,到了皇宮里就給皇上亂出主意,還摻和皇上家里的爛事兒,天天在皇上的耳根子底下亂說,“皇上啊,我看誰可以接您的班,誰誰不行。您可千萬得聽我的,我說的不會錯。”結果呢,讓人家在雪地里活活給埋了。就因這一張破嘴,把小命兒都搭進去了。這值嗎?
接著說諸葛恪,他后來真是受到重用了,當了吳國太傅,帶著兵攻打魏國,他倒是建功立業心切,可是九分人算,還有一分天算呢,攻打了人家幾個月,他硬是打不下來。是啊,你嘴上能說,卻未必能打仗啊。還中了人家的計,丟人啊。諸葛恪肯定想,我這么聰明的人怎么能吃這種虧呢,我這面子也丟得太大了。不行!我得接著打!這仗打到這個時候,有點兒像賭博了。可是他運氣不好,把把不開和,不僅沒有取勝,他自己還中了一箭,這就更丟人了。按說,到了這般時候,他就應該撤兵了。士兵們水土不服,多數都鬧病,這還叫部隊嗎?簡直成疫區了。這應該是他下臺階的好時機啊。回去也有理由啊,“皇上,可不是我諸葛恪無能,主要是咱們的將士不適合哪兒的氣候條件,藥品也供應不上,我只好先撤兵了。您別著急,咱們接下來再說。我肯定得把魏國攻打下來。”他如果這么說,皇上能說什么呢?“行了,諸葛恪啊,我也知道,你也盡力了。這次戰爭失利,責任不在你。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你也外出這么多日子了,夠辛苦的了。”可是諸葛恪顧面子啊,他就是不肯下這個臺階,堅決不撤兵,接著打!士兵們可受不了了,“行了,咱們別再跟著諸葛恪在這里瞎泡著了。”于是開始紛紛地開小差兒了,各級干部也沒有斗志了,他看著實在不行了,這才灰溜溜地回來了。回來之后怎么辦呢?還有一個臺階,如果他能學習他叔叔諸葛亮,趕緊寫份檢討,主動要求上級處分,上級還能真處分他嗎?上級肯定會說,“好了,諸葛恪同志啊,勝敗乃兵家常事嘛。你不要太往心里去。你先休息幾天,咱們再分析研究我們輸掉這場戰爭的原因。”可是這位神童要面子啊,他大概覺得沒臉見人,回來之后就請了病假,什么檢討啊,承認錯誤啊,他一律不會,他還不上班了,躲在家里,還得讓領導和同事們一趟一趟到家里來看他。這還不算,他還讓人私下打聽呢,“你們去給我聽聽去,看誰講我壞話了?都給我記下來。”結果,還真聽到了不少議論,能有好議論嗎?你打個敗仗還不讓別人議論?諸葛恪的臉上就掛不住了,把議論他的人關的關,殺的殺,處分的處分。寫到這里,真是感慨,諸葛恪這種人搞政治,也太“八卦”了。
這一下,就招惹了公憤。那些暫時沒有被他處理的干部,也擔心害怕啊,行了,咱們先下手為強喲。大家一商量,就去找第一把手了,這時候喜歡諸葛恪的孫權已經死了,第一把手現在是孫亮了。孫亮說了,“哎呀,你們怎么才說啊,我早就恨上他了。他眼里還有我這個第一把手嗎?行了,我批準了,殺了他吧。記著,早點動手,別超過今天晚上!”結果,就把諸葛恪給殺了,還被滅了門。唉,真讓諸葛瑾給說中了啊。
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們,凡是把別人看成蠢豬的人,他自己距離豬圈就不遠了。而且他一定先把自己趕進去。而且這些人,多數都是聰明人,是根本看不起別人的。
諸葛亮啊,家門不幸,出了這么一個蠢豬式的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