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啟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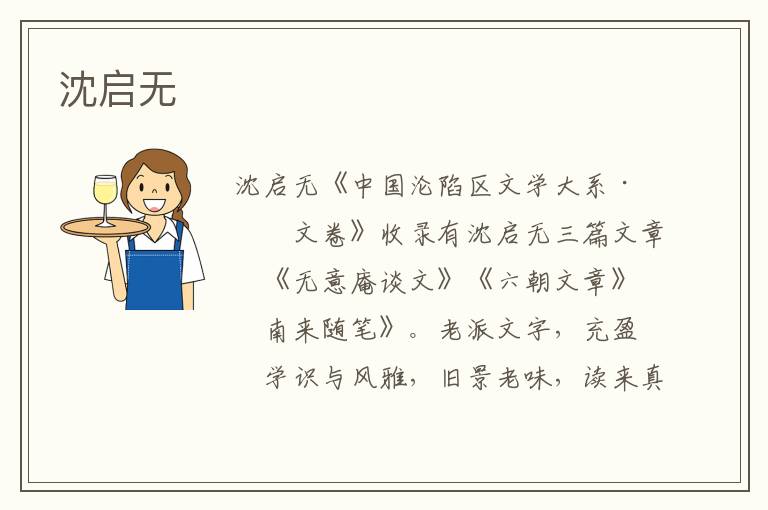
沈啟無
《中國淪陷區(qū)文學大系·散文卷》收錄有沈啟無三篇文章,《無意庵談文》《六朝文章》《南來隨筆》。老派文字,充盈著學識與風雅,舊景老味,讀來真叫人恍惚。
前些年,買了一本《近代散文鈔》,編者是沈啟無,讀后,頗有得隴望蜀之不甘。再讀北京魯迅博物館編的《苦雨齋文叢·沈啟無卷》,開篇卻是《〈中國小說史略〉校注》。手頭剛好有魯迅原書,一一對照讀來,頗有云開見月之疏朗。沈氏的校注,用力頗深,常有深意,文字勘誤之精當,書目提要之簡約,注解補正之齊備,可視為學者的功力與作家的眼光。
散文寫作上,身為周作人的弟子,沈啟無否定載道、崇尚言志,下筆成文,頗有六朝舊氣,像《關(guān)于蝙蝠》《閑步偶記》《談古文》《記王謔庵》《閑步庵書簡》等文章,表現(xiàn)出風雅文人的情思與趣味。
沈啟無除了做點學問,寫寫散文,也作點詩。他的詩和廢名一樣,頗有禪宗的意境,字句有藕斷絲連之美:
秋夜雨
灑在深更
我輕輕滅了燈獨自靜聽
我看不見天上的雨絲
也看不見葉上的雨點
萬花如笑
一九〇二年,沈啟無生于江蘇淮陰。后來在燕京大學讀書,恰好周作人在此任教,一時成為知堂的崇仰者。
沈啟無師從周作人,很多人說他亦步亦趨知堂的思想與文筆,甚至提筆寫字也是周的路子。有人說沈啟無的字“清秀、恬淡,一眼即可認出是學習周作人的字體”。沈啟無的墨跡我也見過,流暢秀美,結(jié)體從二王里來的。
汪曾祺對沈啟無不以為然,在文章中公開貶損,大意是說吃老師的剩飯,沒有出息,文章是無生命力的,把他當作反面例子。孫郁也說:“沈啟無的學術(shù)基本從周氏那里來,也學到一點魯迅的小說史觀,別無創(chuàng)建。他的小品文在韻律上暗襲周作人,連句式都是一樣的。”這些我并不贊同,沈啟無的落墨比周作人平白,并沒有他的澀,敘事寫物,取的是柔而不膩、淡卻有味的路子。他的很多小品文,讓人讀后感覺余音繚繞里猶存一絲清香,如水墨小品的留白,可謂技法,也算境界,更是趣味。
沈啟無文學成就主要在散文上,他的散文有超越時代的語感,今天展讀,依然是一片晴空萬里,厚味綿長,不妨引用一段:
黃昏時分,土城投射一片黑影,于是趕集的人們紛紛回家。你會看見問杏村酒店里掛著的空瓶子,一個個都裝滿了酒香,付了錢,又隨著它們的主人悠悠蕩蕩地歸去……我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再走上這個土城,重溫一次李饅頭的菜味與問杏村的酒香,在這里,我咀嚼著我的漂泊。(《卻說一個鄉(xiāng)間市集》)
這樣清麗溫情的話周作人不會說,尤其不會抒情地讓文章升華。但綿延不盡、欲言又止的文風的確得了幾分知堂翁的真?zhèn)鳌?/p>
一九三九年元旦上午,大約九點鐘,一人進得北平八道灣十一號周家,只說一聲:“你是周先生嗎?”迎面就是一槍。周作人覺得左腹有點疼痛,卻并未跌倒。那時沈啟無站了起來,說道:“我是客。”這人不理睬,也是一槍,沈啟無應(yīng)聲仆地。
周作人命大,子彈擊中毛衣,僅擦破腹部皮面。沈啟無中彈于左肩,在同仁醫(yī)院療養(yǎng)了一個半月,子彈終未取出。那句“我是客”,成了沈啟無平生最大的笑柄與罪證,成為周作人將他逐出師門的導火索,后人說起他,常提此節(jié)。
《知堂回想錄》憶遇刺那一段,暗藏怨懟。“我是客”輕輕一言,不啻道德的雷霆,道盡了沈啟無的怯懦與涼薄。可設(shè)身處地,直面殺氣騰騰的手槍,第一反應(yīng)會是什么?誰能撲在周作人身前擋住子彈?誰能保證,他會沖上去與刺客殊死搏斗?看照片,沈啟無只是一介清瘦書生。或許大多數(shù)人的反應(yīng),不是呆若木雞,就是奪門而逃,不堪者,則匍匐討?zhàn)埌伞?/p>
一九四四年四月間,知堂翁與沈啟無徹底翻臉,周作人這回火氣大得莫名其妙,印“破門聲明”給人,不再認這個弟子。
沈啟無后來自述:“周作人公開發(fā)出破門聲明,并在各報上登載這個聲明,一連寫了好幾篇文章在報上攻擊我。我并未還手,只想把事實擺清楚,寫了‘另一封信’送到北京、上海各報。他們都不刊登,當時只有南京胡蘭成等人,還支持我,‘另一封信’才在南京報刊上發(fā)表出來。周作人不經(jīng)過北大評議會,挾其權(quán)力,就勒令文學院對我立即停職停薪,舊同事誰也不敢和我接近。由于周作人的封鎖,使我一切生路斷絕,《文學集刊》新民印書館也宣布停刊……靠變賣書物來維持生活。武田熙、柳龍光要拉我到《武德報》去工作,我拒絕沒有接受。北京現(xiàn)待不下去,我就到南京去謀生,胡蘭成約我?guī)退帯犊嘀瘛冯s志。”
一九四五年初,沈啟無隨胡蘭成到漢口接辦《大楚報》。胡蘭成做社長,他任副社長。胡蘭成寫文章說:“周作人和沈啟無決裂,沒有法子,也只好讓他們決裂吧,我個人,是同情沈啟無的。”胡蘭成的同情主要是因為周作人太過強勢,擠迫得沈啟無沒法在京城待下去,忍不住出來打抱不平。
胡蘭成對沈啟無的評價并不高,在他的筆下,沈啟無是一個貪婪、妒忌、不顧他人的小人。《今生今世》“漢皋解佩”一章中,胡蘭成說:“沈啟無風度凝莊,可是眼睛常從眼鏡邊框外瞟人。”嫌惡之情,顯而易見。不過,他們有經(jīng)濟上的糾葛,胡蘭成又對沈在他情人面前說過是非耿耿于懷,這些話明顯雜了私念。
因為胡蘭成,沈啟無結(jié)識了張愛玲,寫過評論文章:
張愛玲的文章,我讀過的沒有幾篇,北京的書壇上還沒有《傳奇》賣,這次到南京同蘭成去建國書店買了一本再版的《傳奇》,里面小說一時還沒有工夫讀,僅僅把再版的話讀了,接著我讀她在《苦竹》月刊上的《談音樂》,使我又聯(lián)想起她談畫的文章幾乎每一篇都有她的異彩,仿佛天生的一樹繁花異果,而這些花果,又都是從人間的溫厚情感里洗練出來的。她不是六朝的空氣,卻有六朝人的華瞻。六朝也是一個大而破的時代,六朝的人生是悲哀的,然而對六朝人的描寫,落于平面,把人生和文章分開,沒打成一片,生活的姿態(tài),即使描成種種形形色色的圖案,生命還是得不到解放。因為沒有升華的作用,虛空的美,不透過感情,終歸要疲倦的,所以只能沉入枯寂。枯寂的人生,世界是窄小的,他只能造成自己的格律,用自己的理性筑成藩籬,自己不愿意沖破,也不愿意被人家沖破,沒有智慧的靈光,只有嚴肅的知識是可怕的,人生到此,是要僵化了的,要僵化了的,不是平靜而是死滅。
這此說法是獨特的,文字也好,讀來享受。關(guān)鍵這些話里有沈啟無對自己過去的反思,張愛玲活生生的例子讓他找到了如何看待一貫推崇的六朝文章的另一個思路。
沈啟無妻子說他是一個做學問的人,涉世經(jīng)驗不豐,甚至有些幼稚。子女的記憶里,沈啟無中等個頭,瘦瘦的,戴眼鏡,有精神,脾氣平和,總是笑瞇瞇的,能吃肉,一頓能吃一小碗豬肉,煙癮大,不怎么喝酒,喜歡綠茶。女兒沈蘭印象最深的是父親看書、寫字的背影,不是嚴父的形象。同事回憶,沈啟無謙虛謹慎,溫文爾雅,頗有學者風度。
沈啟無口才不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大學教書,主講宋元明清文學,只是諱談晚明小品。授課深入淺出,感情充沛,學生們很喜歡。有一次講《長生殿》,說起唐明皇和楊貴妃生離死別、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幾個女生感動哭了。他因此挨了批,說思想感情不健康。
沈啟無晚年,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不提陳年往事。他喜歡京戲,偶爾出去也多是到舊書店看看,或者逛逛琉璃廠。
晚年沈啟無對周作人還是有感情的,“文革”中,聽說周很潦倒,住在黑屋子里,無人照顧,感慨系之,還寫過一首詩。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同處一城的周作人也表示過對這個昔日弟子的關(guān)心。師徒偕老,一笑泯恩仇,天涯淪落人抱團取暖以抗凄涼與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