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心亭看雪》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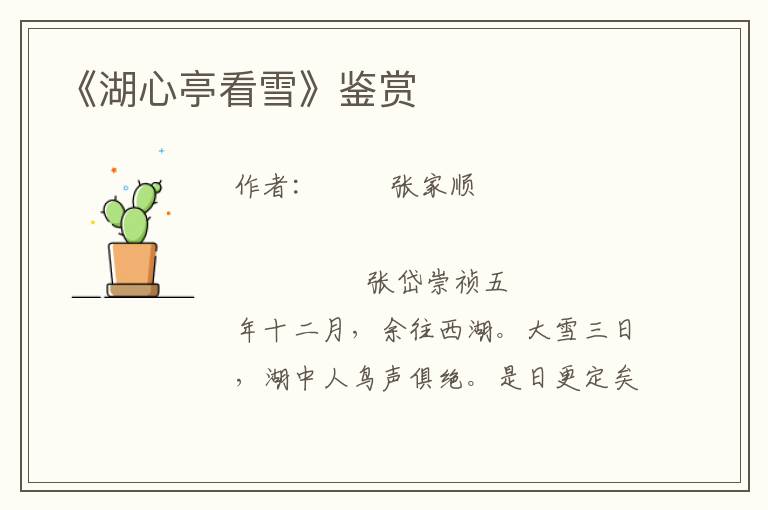
作者: 張家順
張岱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往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1),擁毳衣爐火(2),獨(dú)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沆碭(3),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diǎn),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qiáng)飲三大白而別(4)。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本篇選自晚明小品文著名作手張岱的《陶庵夢憶》,是明代小品中的一篇杰作。
小品文猶如詩中絕句,最講究自然天成而又韻味無限;最忌造作、古板、膚淺之病。文景要寫得如風(fēng)行水上自然成文,作者的詩人般的情致要自然流出,不著痕跡。《湖心亭看雪》在這方面堪為典范。文章起得甚平,純以敘事開篇,在敘事之中漸露作者襟懷:“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dú)往湖心亭看雪。”行文平中見奇,不僅寫出了“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雪后的清寂,而且寫出了作者不同凡俗的性格,他偏偏要選擇在人們都不敢出門的奇寒雪天,又是在“更定”之后,“獨(dú)”往湖心亭看雪。這不由得令人想起晉朝的王子猷雪夜訪戴的故事,不由令人感嘆大凡非常之士必有非常之節(jié),必有常人難以生出的突發(fā)奇想,必有很獨(dú)特的一種心靈。
接下去作者用寥寥數(shù)筆寫西湖雪景。他所寫的西湖雪景,并不似一般人從某一固定視點(diǎn)所看到的景象,而是用心靈的眼,籠罩全景,是作者經(jīng)過藝術(shù)心靈處理過的全景圖。它突出地表現(xiàn)了作者對西湖雪景的獨(dú)特的感受,所表現(xiàn)的是虛靈化,情致化了的一種藝術(shù)境界。這正是中國山水畫的一種獨(dú)特的空間意識與作者個性的結(jié)合。他運(yùn)用強(qiáng)烈對比的手法寫出了雪后天地的混莽、宇宙的無限空闊與自身的落寞與孤寂。“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連用三個“與”字與一個“一”字相應(yīng),寫出了大雪之后萬象歸一的渾然景象,使畫面有無盡之勢。然后作者連用四個近景加以點(diǎn)染,更反襯了雪后天地之空闊,你看那湖上長堤在蒼莽天地中已變得隱隱約約,唯見“一痕”,那湖心亭也影影綽綽地僅余“一點(diǎn)”,湖上小舟更是渺小得如同滄海“一芥”,至于舟中人物只是“兩三粒”而已。這顯然不是置身于舟中、亭上時的視覺。但只有這樣寫才是寫意的山水,有情致、有理趣的山水,才可見出大手筆的胸中丘壑。作者用筆亦是大家風(fēng)度,好似用一支信手拈來之禿筆,在畫面上隨意抹上“一痕”、“一點(diǎn)”“一芥”、“兩三粒”,咫尺畫面立即顯出萬里之勢了。
寫了雪景之后,作者又承接開頭轉(zhuǎn)入敘事。寫到湖心亭遇到了同好:“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真是別開生面,奇中生奇!然而細(xì)細(xì)尋思下來,作為《陶庵夢憶》中的一篇,真正值得作者憶起的大概還是這湖心亭的奇遇,前邊寫景不過是鋪墊而已。作者在孤寂之中突遇同好,其驚喜當(dāng)何如哉!兩位客人“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其實(shí),這都是借敘事以抒情,借別人之口說出自己的“癡”絕,自己的孤特。自己的特點(diǎn)在別人那里得到了印證,這樣的機(jī)會對作者來說也許并不多,而在完全無意的情況下遇到了,當(dāng)然會極為珍視,深藏在自己的記憶之中。這段敘事與上段寫景看似聯(lián)系不密,其實(shí)是暗中呼應(yīng)、相得益彰。寫景主要寫作者在浩漫雪夜孑然一身的孤特,敘事則更進(jìn)一步申足此意并表示了一種自我肯定的心態(tài)。前邊的寫景也同此而顯現(xiàn)了超凡脫俗的情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