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古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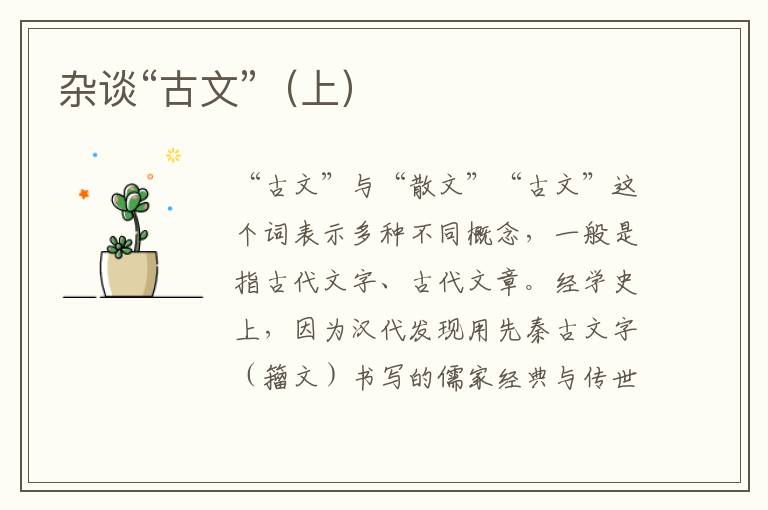
“古文”與“散文”
“古文”這個詞表示多種不同概念,一般是指古代文字、古代文章。經學史上,因為漢代發現用先秦古文字(籀文)書寫的儒家經典與傳世經典文字(隸書)不同,是為“古文經”,引起經學長時期的今、古文之爭。文學史上,唐人以韓愈、柳宗元為代表,反對“駢四儷六”、雕繡藻繪的駢文,提倡復興先秦盛漢單行散體的文體,稱為“古文”,一時造成聲勢,用個近代概念,稱為“古文運動”。唐宋以來,這種“古文”成為文章寫作和散文創作的主導文體,是本文將要討論的。
至于“散文”,定義很難下。在文學理論(實際是西方的文學理論)里,“散文”作為文學樣式,是與詩歌、小說、戲劇并列的文學“樣式”,指一種自由松散地進行敘事、描寫、抒情、議論的“文學”作品。細分起來,又有隨筆、小品、雜文、報告文學等不同體裁。但由于它體制“自由松散”,什么樣的作品算“散文”,具體包容范圍如何,也就相當模糊。總的說來,散文是一種短篇文章,不同于各類政治、思想、學術論著,能夠體現點作者的“主觀創作”意識,在行文上有點感情和文采、講究點“藝術性”。至于上面這幾“點”如何把握,如何用來衡量具體作品,就得見仁見智了。
具體到中國古代文章,情形更為復雜。這和魯迅所說的“文學的自覺”觀念在中國明晰較晚有很大關系。如本刊前面刊載的《說“四六”》(《古典文學知識》2016年第2、3期)一文所指出的,唐、宋以前,文章主要是“實用”的。講先秦、兩漢文學史,講“諸子散文”“史傳散文”“政論散文”等,嚴格說來,那都是學術著作、歷史著作、政治論文,都不能算是純正的“散文”。魯迅講小說史,提出“唐人始有意為小說”,是說到唐代,才有基于作者的“幻設”“作意”寫出來的、作為自覺的文學創作的“小說”(《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那就意味著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例如《搜神記》)、志人小說(例如《世說新語》)還不能算是真正意義的小說。實則文學散文的情況類似。下面拿兩個例子來說明。
南朝梁武帝時,臨川王蕭宏率兵討伐北魏,曾在齊、梁擔任過江州(今湖南九江市)刺史、已經投降北魏的陳伯之率兵相拒,蕭宏請幕僚、也是陳伯之的朋友丘遲(464—508)寫了一封勸降信。這就是收在《文選》里的名作《與陳伯之書》。信的前半大部分文字分析形勢,曉以利害,指出其依魏之非計,亡命之悖謬,勸對方“迷途知返”。這是訴之于理;最后用一小節描寫江南風光,這是陳伯之故鄉風景,動之以情。文曰: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于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這里用了兩個戰國人典故:“廉公之思趙將”,是說廉頗本為趙國上卿,因為不被趙悼襄王重用而投奔魏國,卻又不為魏王信重,后來趙國困于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于趙;“吳子之泣西河”,是說吳起仕魏,治西河之外,即今陜西合陽一帶,魏武侯聽信讒言召吳起,吳起臨行,望西河而泣。兩個典故都是講懷抱忠心的臣下遭受讒害,用在這里,有對陳伯之的叛變行為加以緩頰的用意。在這段文字前面,是短短十六個字,生動地描摹一幅江南三月暮春風光,意在啟發對方的“故國”之思,確是神來之筆。宋湘(1757—1862)《論詩八首》之七說:“文章絕妙有丘遲,一紙書中百首詩。正在將軍旗鼓處,忽然花雜草長時。”據說當初“伯之得書,乃于壽陽(今山西壽陽縣)擁兵八千歸降”。在文學史上,這篇文章被贊許,特別著眼在自然景物的描寫。這封信與大體同時期的陶弘景(456—536)的《答謝中書書》和吳均(469—520)的《與朱元思書》,同被看做是唐、宋繁榮的山水散文的濫觴。
再看另一篇文章,柳宗元“永州八記”里的一篇《至小丘西山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倏爾遠游,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和他的“永州八記”人們耳熟能詳,不煩另作解說。如果僅從兩篇文章對自然景物的描寫看,都鮮明生動,字字珠玉,是絕佳文字。但就總體相比較,兩者有很大的不同:
一,丘遲文章的文體是書信,是“應用文”,描寫自然風景只是附帶部分;柳宗元的文章是一篇“記”,專門“記”小石潭,小石潭風光是這篇文字的主體。
二,前者的寫作以勸降為目的,書寫目的是現實的、理性的;后者則是借自然景物抒寫作者個人的游興,是主觀構想的產物。
三,兩者描摹自然風光的美都具有供人欣賞的美學意義,但在前者,這種贊賞是說理的補充,是附帶的,而在后者,抒發、欣賞小石潭的美則是寫作的主要目的。
文學史上講柳宗元在文學寫作上的貢獻之一,是他寫出了成熟的山水游記,確立了“山水記”這一散文體裁的歷史地位。從前面的對比中可以明確,柳宗元的山水游記與丘遲書信的景物描寫確有根本不同,就是后者乃是出于作者主觀構想的藝術創作。對于這種藝術創作的“主觀”性質,到過永州的人,拿柳宗元的描寫和當地景物加以對比就可以領會。經過一千幾百年,草樹等景觀會發生改變,但陵谷不會有大的變遷。如今永州的實際景象是,柳宗元描繪的丘壑縱橫、奇峰峻嶺的西山不過是低矮的山丘,婉轉曲折、奔流激越的小溪也只是平常的溝渠而已。在柳宗元給朋友寫的信里曾描寫與上述《小石潭記》等作品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永州于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仆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與李翰林建書》)柳宗元在永州還寫過一篇《囚山賦》。他把永州寫成群山圍困的牢獄。那是他心里的另一樣永州山水。唐時的永州本是南荒僻遠小州,基本還沒有開發。這后一類描寫顯然更接近真實。由此可知《小石潭記》等《永州八記》里描寫的永州山水顯然是帶著作者強烈主觀感情的藝術創作的產物。林紓評論柳宗元說他“文有詩情”(《柳文研究法》),他的山水游記正突出地體現了主觀的“詩情”。清人劉開(1784—1824)在《與阮蕓臺宮保(阮元)論文書》一文里又說“柳州始創為山水雜記之體”。所謂“始創”,也是肯定柳宗元寫作“山水雜記”有所創新,推動這一體創作走向成熟。當然在柳宗元之前,如王維(《山中與裴秀才迪書》)、元結(《右溪記》)等人已經寫出一些描摹自然風光的優美篇章。應當說這些也給柳宗元創作成熟的山水散文做了準備。
這樣,柳宗元利用“古文”寫的山水游記,乃是出自他的主觀構想、具有獨立的美學欣賞意義的創作。這已經是不同于一般應用文字的文學散文。
唐代“古文”家的創作,仍多采用漢魏以來的“實用”文章體裁,如書啟、記序、碑志、傳狀等,但從總體說,它們已體現出前所未有的藝術創新價值,乃是作家主觀創作的成果,是真正意義的“文學散文”。例如碑志,一般評價韓文中以碑志為第一。韓愈那些優秀的碑志作品已經完全打破漢魏以來作為紀念、頌揚死者的“應用”文字的傳統格局,寫成具有一定思想內容、藝術技巧純熟的記述人物的散文。下面還將舉例介紹。
不過應當指出,上面用了“純正的‘散文’”“真正意義的文學散文”之類說法,是因為衡量古代作品是否算是散文,時代越是靠前,標準越是寬松。特別是考慮到中國散文發展的具體狀況,一般還是要承認先秦兩漢的“諸子散文”“史傳散文”“政論散文”為“散文”的。不過越是靠后的作品,判斷就越加嚴格了。沒有人把《清史稿》當做“史傳散文”的,盡管有些段落也是文采盎然;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則往往在兩可之間。
總之,正如前面引述魯迅講的“唐人始有意為小說”,是說唐傳奇作為文學樣式才具有“小說”充分成熟的形態;唐代散文的發展與小說處在同一個文學創新的潮流之中。唐代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面轉折時期。思想觀念在發生重大轉變,文學觀念、文學創作隨之發生演變。文學散文的成熟是這重大演變的一端。
“古文”與“傳奇”
上面說到唐代散文與小說的發展處在同一文學演變的潮流之中。二者的發展相互關聯、相互影響。
關于這一點,宋人陳師道(1053—1101)《詩話》里記載的一個掌故可給人以啟發:
范文正公(仲淹)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铏所著小說也。
尹師魯(名洙,1001—1047)這個評論,陳振孫(?—1261?)在《直齋書錄解題》里說“蓋一時戲笑之談耳”。尹師魯博聞強記,知通今古,和范仲淹(989—1052)是朋友。仁宗朝,范與宰相呂夷簡相忤,貶饒州(今江西鄱陽縣),其時尹師魯為太子中允,上疏辯護,牽連被貶監郢州(今湖北鐘祥市)酒稅。他對友人寫的《岳陽樓記》的評論雖出戲謔,確也指出了這篇文章表現上的特點。
《傳奇》是晚唐裴的一部志怪小說集。裴在僖宗(874—888)年間做過靜海節度使(靜海軍,轄地占今越南北部)高駢的幕僚。高駢好神仙道術,他應有同好,所作《傳奇》所述“皆神仙恢譎事”(《郡齋讀書志》)。傳奇創作發展到晚唐,已是其爛熟期。這部作品總體水平不能和以前的《李娃傳》《鶯鶯傳》《霍小玉傳》等優秀作品相比,但其中《鄭德麟》《聶隱娘》《裴航》《陶尹二君》等篇設想奇詭,描摹生動,也算是晚唐傳奇里較優秀、有特色的作品。尹師魯說《岳陽樓記》是“《傳奇》體”,也是著眼于二者表達技巧有相似處。范仲淹“用對語說時景”一段如下: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拿裴的《傳奇》文字與之相比照,兩者明顯類似點有二:一是二者行文基本都用駢體;再是二者都使用描摹手法。文學創作講究形象性,重描摹,這后一點在考察散文發展形態上是個重要標準。
錢鐘書在《管錐篇》里討論梁江淹的《四時賦》《麗色賦》,同樣聯系到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指出其中“春和景明”云云描寫洞庭風景一段文字,“艷縟損格,不足比歐、蘇之簡淡”,又批評“尹洙抗志希古,糠秕六代,唐文舍韓、柳外,即視同鄶下,故讀范《記》而不識本源。”(《管錐篇》第1408—1410頁)他批評尹洙不知道《岳陽樓記》這一段因襲了江淹的寫法。如果從“用對語說時景”角度看,江淹與范仲淹兩人的文章確有繼承關系。下面是江淹《四時賦》里的一段:
若乃旭日始暖,蕙草可織,園桃紅點,流水碧色。思舊都兮心斷,憐故人兮無極。至若炎云峰起,芳樹未移,澤蘭生坂,朱荷出池。憶上國之綺樹,想金陵之蕙枝。若夫秋風一至,白露團團,明月生波,螢火迎寒。眷庭中之梧桐,念機上之羅紈。至于冬陰北邊,永夜不曉,平蕪際海,千里飛鳥。何嘗不夢帝城之阡陌,憶故都之臺沼。
兩相比照,主要類似點在都是用排比手法寫四時風景,又都用駢體。但認真分析,兩者寫法有根本不同:江淹不是寫實景,基本是組織事典,加以藻繪形容,這是六朝賦的典型寫法;而范仲淹則是對真實情境的生動描繪:面對浩淼的洞庭湖,聯想到宇宙浩瀚,人生起伏,抒寫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志愿。至于這種文字是否“艷縟損格”,則各人所見不同了。
錢鐘書還舉出歐、蘇同樣是登臨寫景、按時間變化加以描寫的文章,說他們的寫法更為“簡淡”。他沒有舉出具體作品。這里姑且看看寫法類似的例子:歐陽修的《醉翁亭記》: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云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又蘇軾的《放鶴亭記》:
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于斯亭而樂之。
這兩篇的寫法,就描寫真情實境一點,確實與《岳陽樓記》有類似處。兩者寫得確實也更為靈活淡雅。黃宗羲論文有一個看法:“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為小說家伎倆。”(《論文管見》)這樣從總體看,《岳陽樓記》和這兩篇作品的行文又確實與裴《傳奇》有一致之處。
關于唐代“古文”與傳奇小說的關系,陳寅恪又曾說:
中國文學史中別有一可注意之點焉,即今日所謂唐代小說者,亦起于貞元元和之世,與古文運動實同一時,而其時最佳小說之作者,實亦即古文運動中之中堅人物是也……是故唐代貞元元和間之小說,乃一種新文體,不獨流行當世,復更輾轉為后來所則效,本與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體制也。(《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長恨歌》)
后來他寫關于韓愈的專論,又論述韓愈的“古文”與傳奇小說的關系:
……退之之古文乃用先秦、兩漢之文體,改作唐代當時民間流行之小說,欲借以一掃腐化僵化不適用于人生之駢體文,作此嘗試而能成功者,故名雖復古,實則通今,在當時為最便宣傳,甚合實際之文體也。(《論韓愈》)
這就精辟地揭示“古文運動”和傳奇小說在文體上的一致處,并把這種一致歸結到同一的社會背景和社會需求。實則類似的意見魯迅也說過,他在《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別》一文中指出:
晉人尚清談,講標格,常以寥寥數言,立致通顯,所以那時的小說,多是記載畸行雋語的《世說》一類,其實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門書。唐以詩文取士,但也看社會的名聲,所以士子入京應試,也須豫先干謁名公,呈獻詩文,冀其稱譽,這詩文叫做“行卷”。詩文既濫,人不欲觀,有的就用傳奇文,來希圖一新耳目,獲得特效了,于是那些的傳奇文,也就和“敲門磚”很有關系。
這樣,說《岳陽樓記》乃是“《傳奇》體”,實則表明唐、宋“古文”與傳奇創作寫法上相類、發展上相促進。這也是文學發展中各種樣式相互作用的具有規律性的現象。
前面提到韓愈的有些碑志乃是優秀的文學散文。另如韓、柳寫的“傳”,其中包括寓言性質的所謂“寓傳”,如韓愈的《張中丞傳后敘》《圬者王承福傳》《毛穎傳》,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童區寄傳》等,無論是構思還是寫法,也都和當時流行的傳奇類似。
這樣,“古文”作為文學散文的發展,得力于與唐傳奇寫作的相互交流與借鑒。正是在這樣的交流與借鑒中,兩者作為自覺的文學創作的性格形成、確立下來。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