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適與武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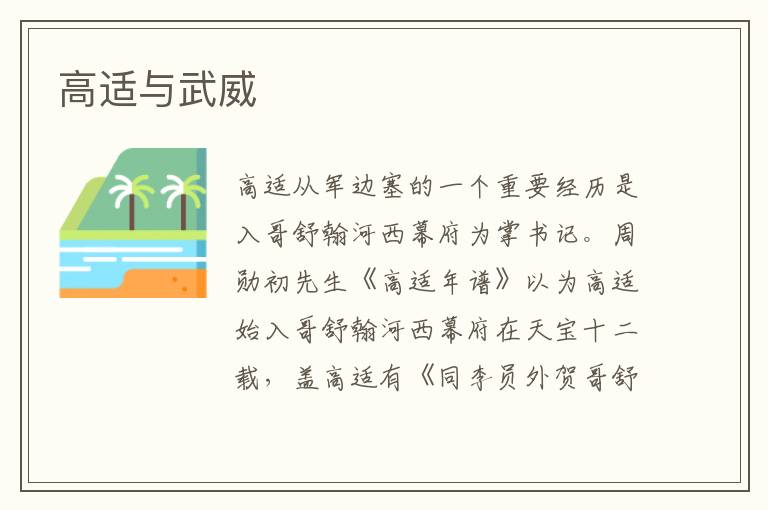
高適從軍邊塞的一個(gè)重要經(jīng)歷是入哥舒翰河西幕府為掌書記。周勛初先生《高適年譜》以為高適始入哥舒翰河西幕府在天寶十二載,蓋高適有《同李員外賀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李員外”即李希言,希言天寶十四載已在河西行軍司馬任,蓋十二年已入哥舒幕府。而高適《自武威赴臨洮謁大夫不及因書即事寄河西隴右幕下諸公》即作于天寶十二載入哥舒幕府赴河西臨洮謁哥舒翰不遇之作。“高適在長(zhǎng)安應(yīng)薦,先至武威,后轉(zhuǎn)臨洮,仍未及與哥舒翰謀面。其后高適赴隴右節(jié)度駐地鄯州西平郡,始與哥舒翰相見。西平郡在今青海樂(lè)都縣。此詩(shī)作于天寶十二載秋”(周勛初《高適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獨(dú)孤及又有獨(dú)孤及《送陳兼應(yīng)辟兼寄高適賈至》詩(shī),有“高侯秉戎翰,策馬觀西夷。方從幕中事,參謀王者師”,其時(shí)高適在河西幕府。參獨(dú)孤及《送陳贊府兼應(yīng)辟赴京序》“天寶十二載冬十月,果以公才征”語(yǔ),高適天寶十二載已在河西幕府。孫欽善《高適年譜》(《高適集校注》附錄)以為高適天寶十一載即入河西哥舒翰幕,時(shí)在秋冬之際。而十二月又隨哥舒翰入朝,天寶十二載夏季又返回河西隴右。其說(shuō)較周勛初先生考證更為圓融。王維亦有《送高判官?gòu)能姼昂游餍颉芬酁楸灸晁透哌m赴河西之作,但高適為掌書記,這里稱“高判官”,則還需要進(jìn)一步研究。高適在武威作詩(shī)共十六題二十首,主要是歌頌戰(zhàn)功、登覽名勝、送別友人、抒寫情懷四個(gè)方面。
一、 歌頌戰(zhàn)功高適從軍武威是擔(dān)任哥舒翰的河西節(jié)度掌書記,哥舒翰是盛唐時(shí)期威震西域的著名將領(lǐng),故而高適在赴河西而未見到哥舒翰時(shí)就作對(duì)歌頌哥舒翰。其《自武威赴臨洮謁大夫不及因書即事寄河西隴右幕下諸公》云:
浩蕩去鄉(xiāng)縣,飄飖瞻節(jié)旄。揚(yáng)鞭發(fā)武威,落日至臨洮。主人未相識(shí),客子心忉忉。顧見征戰(zhàn)歸,始知士馬豪。耀崖谷,聲氣如風(fēng)濤。隱軫戎旅間,功業(yè)競(jìng)相褒。獻(xiàn)狀陳首級(jí),饗軍烹太牢。俘囚面縛,長(zhǎng)幼隨巔毛。氈裘何蒙茸,血食本膻臊。漢將乃兒戲,秦人空自勞。立馬眺洪河,驚風(fēng)吹但白蒿。云屯寒色苦,雪合群山高。遠(yuǎn)戍際天末,邊烽連賊壕。我本江海游,逝將心利逃。一朝感推薦,萬(wàn)里從英旄(髦)。飛鳴蓋殊倫,俯仰忝諸曹。燕鴿(頷)知有待,龍泉惟所操。相士慚入幕,懷賢愿戰(zhàn)友。清掄揮塵尾,乘酣持蟹螯。此行豈易酬,深意方郁陶。微效儻不遂,終然辭佩刀。
這首詩(shī)高適詩(shī)集未收,從敦煌文獻(xiàn)中發(fā)現(xiàn)。詩(shī)應(yīng)作于天寶十二載冬,詩(shī)題中“大夫”為哥舒翰。哥舒翰天寶六載代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jié)度副大使知節(jié)度事,八載破九曲后拜鴻臚員外卿,加攝御史大夫。十一載加河西節(jié)度使。其時(shí)高適自武威赴臨洮拜謁哥舒翰,而哥舒翰不在,故作是詩(shī)以寄幕下諸公。詩(shī)的開頭“浩蕩去鄉(xiāng)縣”至“客子心忉忉”,敘寫離開家鄉(xiāng)奔赴武威,又離開武威到達(dá)臨洮謁見主將,但不見主將,心中憂勞。“顧見征戰(zhàn)歸”至“秦人空自勞”,敘寫哥舒翰破九曲凱旋后的盛況,重點(diǎn)贊揚(yáng)了哥舒翰的功業(yè)。“立馬眺洪河”至“邊烽連賊壕”,描寫邊塞冬日的肅殺景象。“我本江海游”至“終然辭佩刀”是作者書寫懷抱、表明心志之語(yǔ),以向河西諸公呈現(xiàn)自己建功立業(yè)的追求,而這種述說(shuō)又以謙語(yǔ)出之,謂不能立功即辭職隱退。高適又有《入昌松東界山行》詩(shī):
鳥道幾登頓,馬蹄無(wú)暫閑。崎嶇出長(zhǎng)坂,合沓猶前山。石激水流處,天寒松色間。王程應(yīng)未盡,且莫顧刀環(huán)。
這首詩(shī)也是高適在河西哥舒翰幕中所作。“昌松”是武威屬縣,《舊唐書·地理志三》:“涼州中都督府,隋武威郡。……昌松,漢蒼松縣,屬武威郡。后涼呂光必為呂松。”詩(shī)言“王程應(yīng)未盡,且莫顧刀環(huán)”,蓋是初赴涼州謁見哥舒翰途中所作,應(yīng)為天寶十二載冬。
高適在哥舒翰幕府判官,隨從哥舒舒與吐蕃作戰(zhàn),因哥舒翰屢獲戰(zhàn)功,高適寫了好幾首詩(shī)加以頌揚(yáng)。其《同呂判官?gòu)母缡娲蠓蚱坪闈?jì)城回登積石軍多福七級(jí)浮圖》詩(shī)云:
塞口連濁河,轅門對(duì)山寺。寧知鞍馬上,獨(dú)有登臨事。七級(jí)凌太清,千崖列蒼翠。飄飄方寓目,想像見深意。高興殊未平,涼風(fēng)颯然至。拔城陣云合,轉(zhuǎn)旆胡星墜。大將何英靈,官軍動(dòng)天地。君懷生羽翼,本欲附騏驥。款段苦不前,青冥信難致。一歌陽(yáng)春后,三嘆終自愧。
這首詩(shī)作于天寶十二載五月,《資治通鑒》卷二一六天寶十二載稱:“夏五月……隴右節(jié)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jì)、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呂判官”即呂,據(jù)《舊唐書·呂傳》記載,呂,河?xùn)|人。“翰益親之,累遷虞部員外郎、侍御史”。《冊(cè)府元龜》卷七一六云:“呂為隴右河西節(jié)度哥舒翰度支判官,性謹(jǐn)守,勤于吏職,雖同寮追賞,而塊然視事,不離案簿。翰益親之。”《舊唐書·呂傳》又言呂“志行修整,勤于學(xué)業(yè)”,《全唐詩(shī)》中雖未見其詩(shī),但根據(jù)高適詩(shī)中所寫“一歌陽(yáng)春后,三嘆終自愧”,可知其頗有詩(shī)才。這首詩(shī)是從哥舒翰破吐蕃后回軍登塔之作,前半寫征途登塔眺望之景,體現(xiàn)出鞍馬登臨的豪放情懷;后半著重歌頌哥舒翰的戰(zhàn)功,同時(shí)贊頌呂跟隨哥舒翰的業(yè)績(jī),并述說(shuō)呂與自己的交厚。這首詩(shī)亦見敦煌寫本殘卷,詩(shī)題與內(nèi)容與集本稍有異同。
表現(xiàn)哥舒翰軍功的另一戰(zhàn)役是破九曲,高適于這次戰(zhàn)爭(zhēng)作詩(shī)多首。其《同李員外賀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云:
遙傳副丞相,昨日破西蕃。作氣群山動(dòng),揚(yáng)軍大旆翻。奇兵邀轉(zhuǎn)戰(zhàn),連孥絕歸奔。泉噴諸戎血,風(fēng)驅(qū)死虜魂。頭飛攢萬(wàn)戟,面縛聚轅門。鬼哭黃埃暮,天愁白日昏。石城與巖險(xiǎn),鐵騎皆云屯。長(zhǎng)策一言決,高蹤百代存。威棱懾沙漠,忠義感乾坤。老將黯無(wú)色,儒生安敢論。解圍憑廟算,止殺報(bào)君恩。唯有關(guān)河渺,蒼茫空樹墩。
這首詩(shī)敦煌寫本殘卷與集本有所不同,題為《同呂員外范司直賀大夫再破黃河九曲之作》,是。哥舒翰收河西九曲在天寶十二載八月,《資治通鑒》卷二一六天寶十二載記述:“隴右節(jié)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jì)、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為河西行軍司馬。是時(shí)中國(guó)盛強(qiáng),自安遠(yuǎn)門西盡唐境凡萬(wàn)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wú)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詩(shī)即其時(shí)所作。有關(guān)九曲,《資治通鑒》卷二一〇睿宗景云元年記述:“安西都護(hù)張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絕和親,乃賄鄯州都督楊矩,請(qǐng)河西九曲之地為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胡三省注:“九曲者,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草良,蓋即漢大、小俞谷之地,吐蕃置洪濟(jì)、大漠門等城以守之。”呂員外即呂,見前詩(shī)所考。這首詩(shī)是哥舒翰破九曲勝利之后,高適奉和之作。前半敘述攻破九曲的戰(zhàn)況,表現(xiàn)了唐軍排山倒海、勢(shì)如破竹,而吐蕃軍天昏地暗、鬼哭黃埃的慘象。后半重在稱頌哥舒翰之武威和策略,憑廟算以解重圍,止殺戮以報(bào)君恩。高適又有《九曲詞三首》:
許國(guó)從來(lái)徹廟堂,連年不為在疆場(chǎng)。將軍天上封侯印,御史臺(tái)上異姓王。
萬(wàn)騎爭(zhēng)歌楊柳春,千場(chǎng)對(duì)舞繡騏。到處盡逢歡洽事,相看總是太平人。
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逤取封侯。青海只今將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
這組詩(shī)是天寶十二載破九曲后于秋日封西平郡王時(shí)所作。郭茂倩《樂(lè)府雜錄》卷九一:“哥舒翰破吐蕃,收九曲黃河,置洮陽(yáng)郡,適為作《九曲詞》。”末句“御史臺(tái)中異姓王”即指哥舒翰封西平郡王事。這組詩(shī)集中贊頌哥舒翰破九曲之戰(zhàn)功,表現(xiàn)出主將與部下以身許國(guó)、立功沙場(chǎng)的壯志。
高適還有一首《無(wú)題》詩(shī):
一隊(duì)風(fēng)來(lái)一隊(duì)砂,有人行處沒(méi)人家。陰山入夏仍殘雪,溪樹經(jīng)春不見花。
這首詩(shī)高適詩(shī)集傳世各本不傳,見于敦煌詩(shī)集殘卷伯3619號(hào)。次于《九曲詞三首》之后。詩(shī)中“陰山”在新疆境內(nèi),據(jù)《新唐書·地理志》,唐北庭都護(hù)府轄有陰山州都督府,唐高宗顯慶三年以西突厥葛邏謀落部置。唐代岑參詩(shī)中也經(jīng)常見到“天山”的描寫,故此詩(shī)亦當(dāng)為高適從哥舒翰幕府在河西隴右之作。詩(shī)寫人煙稀少、春風(fēng)不度的邊關(guān)景象。而詩(shī)的首句“一隊(duì)風(fēng)來(lái)一隊(duì)砂”則是描寫行軍之句,又是入夏之間,應(yīng)該也是描寫九曲之戰(zhàn)的詩(shī)作。
高適還有一首《同呂員外酬田著作幕門軍西宿盤山秋夜作》詩(shī),雖非描寫戰(zhàn)功,但是也與戰(zhàn)事相關(guān):
磧路天早秋,邊城夜應(yīng)永。遙傳戎旅作,已報(bào)關(guān)山冷。上將頓盤阪,諸軍遍泉井。綢繆閫外書,慷慨幕中請(qǐng)。能使勛業(yè)高,動(dòng)令氛霧屏。遠(yuǎn)途能自致,短步終難騁。羽翮時(shí)一看,窮愁始三省。人生感然諾,何啻若形影。白發(fā)知苦心,陽(yáng)春見佳境。星河連塞絡(luò),刁斗兼山靜。憶君霜露時(shí),使我空引領(lǐng)。
詩(shī)中田著作應(yīng)為田良丘,“上將”即哥舒翰。據(jù)《舊唐書·哥舒翰傳》,良丘為京兆人,為哥舒翰判官。杜甫有《贈(zèng)田九判官梁丘》詩(shī),亦當(dāng)詩(shī)中田著作。田梁丘曾引薦高適入哥舒翰幕府。詩(shī)題中的“幕門軍”,即莫門軍,或作“漠門軍”。《通典》卷一七二:“莫門軍,臨洮郡城內(nèi),儀鳳二年置,管兵五千五百人,馬二百匹。”盤山即在臨洮,《讀史方輿紀(jì)要》卷六十:“臨洮府有十八盤山。”注:“在府東南百里,山高險(xiǎn),有石級(jí)一十八里。”這首詩(shī)是高適在河西幕中與呂和田良丘酬和之作。地點(diǎn)在臨洮,哥舒翰為河南隴右節(jié)度使,治所雖在武威,而臨洮是唐軍與吐蕃對(duì)陣之地,故發(fā)生戰(zhàn)事,往往在臨洮。詩(shī)作于秋日,又在臨洮關(guān)山之地,高適隨上將哥舒翰屯軍盤阪,邀請(qǐng)?zhí)锪记疖娔蝗温氁园l(fā)揮其勛業(yè)。最后寫出秋日盤山星河連塞,遼闊曠遠(yuǎn)的蒼茫景象,使得整首詩(shī)充滿了雄渾蒼涼的格調(diào)。
二、 登覽名勝高適在武威,常常與幕府同僚登覽名勝古跡,并且飲宴賦詩(shī)。其《陪竇侍御靈云南亭宴詩(shī)》云:
人幽宜眺聽,目極喜亭臺(tái)。風(fēng)景知愁在,關(guān)山憶夢(mèng)回。只言殊語(yǔ)默,何意忝游陪。連唱波瀾動(dòng),冥搜物象開。新秋歸遠(yuǎn)樹,殘雨擁輕雷。檐外長(zhǎng)天盡,尊前獨(dú)鳥來(lái)。常吟塞下曲,多謝幕中才。河漢徒相望,嘉期安在哉。
這首詩(shī)前有序交代了原委:“涼州近胡,高下其池亭。蓋以耀蕃落也。幕府董帥雄勇,經(jīng)踐賊庭,自陽(yáng)關(guān)而西,猶枕席矣。軍中無(wú)事,君子飲食宴樂(lè),宜哉。白簡(jiǎn)在邊,清秋多興,況水具舟楫,山兼亭臺(tái),始臨泛而寫煩,俄登步以寄傲,絲桐徐奏,林木更爽,觴蒲萄以遞歡,指蘭芷而可掇。胡天一望,云物蒼然,雨瀟瀟而牧馬聲斷,風(fēng)裊裊而邊歌幾處,又足悲矣。員外李公曰:七日者何?牛女之夕也。夫賢者何得謹(jǐn)其時(shí),請(qǐng)賦南亭詩(shī),列之于后。”高適和竇侍御詩(shī)作于天寶十二載。因高適有《李云南征蠻詩(shī)并序》云:“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十二載四月,至于長(zhǎng)安。……適忝斯人之舊,因賦是詩(shī)。”四月在長(zhǎng)安,而七月七日已經(jīng)在涼州。高適又有《送竇侍御知河西和糴還京序》一文,均是在涼州與竇侍御交往之作。詩(shī)序中的“董帥”,孫欽善《高適集校注》以為是董延光,原為河西隴右節(jié)度使王忠嗣部將,曾主動(dòng)獻(xiàn)策請(qǐng)攻石堡城。見于《舊唐書·王忠嗣傳》及《資治通鑒》。蓋王忠嗣以后,董延光仍留在武威成為哥舒翰幕府屬官。同樣是秋日,高適還和竇侍御泛靈云池,其《陪竇侍御泛靈云池》詩(shī)云:
白露時(shí)先降,清川思不窮。江湖仍塞上,舟楫在軍中。舞換臨津樹,歌饒向迥風(fēng)。夕陽(yáng)連積水,邊色滿秋空。乘興宜投轄,邀歡莫避驄。誰(shuí)憐持弱羽,猶欲伴鹓鴻。
這首詩(shī)亦應(yīng)作于天寶十二載。詩(shī)寫泛舟靈云池之時(shí),白露已降,時(shí)屬深秋,清川無(wú)際,引發(fā)出無(wú)窮的邊思。塞上軍中,歌舞相伴,泛舟之樂(lè)與空曠的清川之境融為一體。更兼主人殷勤留客,故自己則以弱羽短翮而陪鹓鴻之游。末尾實(shí)是高適自謙之詞。
高適與竇侍御交誼甚深,同樣在這一年的冬日,他們登上了涼州的七級(jí)浮圖,并有詩(shī)歌唱和。高適《和竇侍御登涼州七級(jí)浮圖之作》云:
化塔屹中起,孤高宜上躋。鐵冠雄賞眺,金界寵招攜。空色在軒戶,邊聲連鼓鼙。天寒萬(wàn)里北,地豁九州西。清興揖才彥,峻風(fēng)和端倪。始知陽(yáng)春后,具物皆筌蹄。
這首詩(shī)應(yīng)作于天寶十二載冬日,故有“天寒萬(wàn)里北”之語(yǔ)。詩(shī)是與同幕竇侍御唱和之作。這里的“七級(jí)浮圖”應(yīng)為涼州的蓮花山開元寺。據(jù)《法苑珠林》所載,佛祖舍利有十九所在中國(guó),其一即在涼州姑臧故塔,又名鎮(zhèn)魔塔。其間文昌宮之鐵鐘,索巴讓摩之鐵像,金頂之鐵冠,稱之三鐵。鐵鐘穿山,書聲朗而學(xué)子立;鐵像靜穆,佛音稀而行者冥;鐵冠搖鈴,蓮瓣開而楊柳飛。高適詩(shī)稱“鐵冠雄賞眺”,正是金頂鐵冠的生動(dòng)描摹。詩(shī)的前四句狀域之高峻雄偉,中四句寫登塔之所見所聞,后四句寫登塔后所悟之理。塔之高峻、塔周之景、登塔之情都躍然紙上。
三、 送別友人武威地處中原與西域交通的節(jié)點(diǎn),故而高適在武威幕府,送往迎來(lái)就成了軍幕生活和個(gè)人生活都不可或缺之事。值得我們注意者,一首是送友人長(zhǎng)安赴舉詩(shī),《河西送李十七》詩(shī):
邊城多遠(yuǎn)別,此去莫徒然。問(wèn)禮知才子,登科及少年。出門看落日,驅(qū)馬向秋天。高價(jià)人爭(zhēng)重,行當(dāng)早著鞭。
這首詩(shī)是高適在河西哥舒翰幕府送李十七赴京應(yīng)試之作。詩(shī)中有“登科及少年”“行當(dāng)早著鞭”語(yǔ),李十七赴京應(yīng)試可以確定。由這首詩(shī),我們也可以認(rèn)識(shí)到,唐代的科舉考試,已覆蓋到邊城。故李十七赴舉,高適與之遠(yuǎn)別,勉勵(lì)其少年登科。就“高價(jià)人爭(zhēng)重”語(yǔ),我們可以推測(cè)李十七赴京當(dāng)為應(yīng)進(jìn)士舉。蓋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三稱:“故當(dāng)代以進(jìn)士登科為登龍門。”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下《喜信》條稱:“新進(jìn)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于家書中,至鄉(xiāng)曲,親戚例以聲樂(lè)相慶,謂之喜信也。”另一首是送友人入長(zhǎng)安詩(shī),《送蕭判官賦得黃花戍》云:
君不見黃花曲里黃,戍日蕭蕭帶寒樹。樓上偏臨北斗星,門前直至西州路。每到瓜時(shí)更卒來(lái),只對(duì)黃花□□□。樓中幾度哭明月,笛里何人吹《落梅》?多君莫不推才杰,欲奏平戎赴天闕。轅門杯酒別交親,去去云霄羽翼新。知君馬上貂裘暖,須念黃花久戍人。
這首詩(shī)原本缺佚,據(jù)敦煌詩(shī)集殘卷補(bǔ)入。因詩(shī)中有“門前直至西州路”語(yǔ),故知此詩(shī)亦為高適從哥舒翰幕府在武威時(shí)作。蕭判官即為哥舒翰河西節(jié)度判官,名字未詳。黃花戍,唐王烈《塞上曲》:“紅顏歲歲老金微,砂磧年年臥鐵衣。白草城中春不入,黃花戍上雁長(zhǎng)飛。”唐張說(shuō)有《送李侍郎詩(shī)》:“藉藉黃花塞,搜兵白狼水。”唐人胡皓有《夜行黃花川》詩(shī),知唐詩(shī)尤其是邊塞詩(shī)當(dāng)中運(yùn)用黃花戍、黃花塞、黃花川者頗多,屬于常見的邊塞地名。這首詩(shī)在邊地武威送友人入長(zhǎng)安,別意當(dāng)中,既見邊城蒼涼之景,又有勉勵(lì)之意,更寓相知之情。
與送別友人相關(guān)的作品是高適在武威與友人集會(huì)之作,表現(xiàn)了軍幕文士豪放情懷。高適《武威同諸公過(guò)楊七山人得藤字》云:
幕府日多暇,田家歲復(fù)登。相知恨不早,乘興乃無(wú)恒。窮巷在喬木,深齋垂古藤。邊城唯有醉,此外更何能。
這里的“楊七山人”,陶敏《全唐詩(shī)人名匯考》以為楊炎。《舊唐書·楊炎傳》:“炎美須眉,風(fēng)骨峻峙,文藻雄麗,汧隴之間,號(hào)為‘小楊山人’。釋褐辟河西節(jié)度掌書記。”《全唐文》卷四二一楊炎有《河西節(jié)度使廳壁記》末署:“天寶十二年夏六月記。”陶敏云“十二年”為“十五年”之誤,是。又《全唐文》卷四二二楊炎有《云麾將軍郭公(千里)神道碑》稱:“以天寶十一載二月,薨于武威之地。……以十三載某月,葬我公于武威北原。”是知楊炎天寶末與高適同在河西,故有這一次詩(shī)歌集會(huì)。高適在武威的這一次詩(shī)歌集會(huì),對(duì)于我們研究唐詩(shī)的群體創(chuàng)作具有重要意義。因?yàn)檫@樣的群體創(chuàng)作在京城長(zhǎng)安以及江南等地是屢見不鮮的,而在西部邊塞卻非常罕見。詩(shī)題“同諸公”是說(shuō)一群幕僚去拜訪楊炎,而又一起分韻賦詩(shī),故高適“得藤字”。這首詩(shī)作于天寶末年,是時(shí)唐朝強(qiáng)盛,邊境無(wú)事,農(nóng)業(yè)豐收,故而武威幕府亦多暇日,也就有這一次赴楊炎山莊的集會(huì)。這就是首聯(lián)描寫的景象。頷聯(lián)則轉(zhuǎn)入抒情,言其過(guò)楊七山人是因?yàn)橄嘀嘤鲋墶ni聯(lián)又轉(zhuǎn)入寫景,突出了楊炎山莊深掩于喬木古藤之中的幽靜環(huán)境。尾聯(lián)描寫邊城友朋聚會(huì),酣醉豪放的場(chǎng)面。
四、 抒寫情懷高適為哥舒翰河西節(jié)度府掌書記,從軍出塞,鎮(zhèn)守邊關(guān),故而常常以詩(shī)抒寫情懷。他常用樂(lè)府舊題來(lái)寫邊塞生活。如《塞下曲》云:
結(jié)束浮云駿,翩翩出從戎。且憑天子怒,復(fù)倚將軍雄。萬(wàn)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風(fēng)。日輪駐霜戈,月魄懸雕弓。青海陣云匝,黑山兵氣沖。戰(zhàn)酣太白高,戰(zhàn)罷旄頭空。萬(wàn)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jīng)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塞下曲》屬于樂(lè)府舊題,高適即借樂(lè)府舊題吟詠出塞之情。詩(shī)有“青海陣云匝”句,青海即青海湖,是吐蕃東北邊塞與唐交接的地方,哥舒翰指揮的九曲之役就發(fā)生在這里。故這首詩(shī)應(yīng)是哥舒翰頗九曲勝利后,高適歌頌之作。詩(shī)中“萬(wàn)里不惜死”六句,表現(xiàn)了高適從軍出塞志在建功立業(yè)的雄大抱負(fù)。再如《部落曲》云:
蕃軍傍塞游,代馬噴風(fēng)秋。老將垂金甲,閼支著錦裘。 雕戈蒙豹尾,紅旆插狼頭。日暮天山下,鳴笳漢使愁。
《部落曲》也屬于樂(lè)府詩(shī)題,部落沒(méi)有開化的民族分部屯居,這里指游牧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區(qū)。按,這首詩(shī)《全唐詩(shī)》馬逢詩(shī)卷亦收入。紀(jì)昀《瀛奎律髓刊誤》卷三十云:“此詩(shī)鈍置,非常侍之佳作。”
樂(lè)府舊題之外,他還有《武威作二首》詩(shī):
朝登百尺烽,遙望燕支道。漢壘青冥間,胡天白如掃。憶昔霍將軍,連年此征討。匈奴終不滅,塞下徒草草。唯見鴻雁飛,令人傷懷抱!
晉武輕后事,惠皇終已昏。豺狼塞瀍洛,胡羯爭(zhēng)乾坤。四海如鼎沸,五涼徒自尊。而今白庭路,猶對(duì)青陽(yáng)門。朝市不足問(wèn),君臣隨草根。
這二首詩(shī)的題目,傳世高適集各本都作“題百丈峰二首”,敦煌寫本高適詩(shī)集作“武威作二首”,今從敦煌本。首句“百尺烽”,傳世集本多作“百丈峰”,或作“百尺峰”,今亦從敦煌本。又“五涼徒自尊”,傳世各集本作“五原徒自尊”。劉開揚(yáng)云“‘五原徒自尊’,《高適詩(shī)集》殘卷作‘五涼徒自尊’,考前涼、后涼、北涼均在武威,南涼在樂(lè)都,四涼在敦煌,后徙酒泉,仍以《武威作》為是。”(劉開揚(yáng)《高適詩(shī)集編年箋注》,第251頁(yè))這首詩(shī)應(yīng)為天寶十二載秋作,表現(xiàn)了高適從軍邊塞之感從而生發(fā)出的懷古傷時(shí)之慨。明人唐汝詢《唐詩(shī)解》卷九評(píng)該詩(shī)第一首曰:“此嘆苦戰(zhàn)之無(wú)益也,言登高而望邊境,見漢壘而想去病之北征,其時(shí)以為必滅匈奴而后已,然終果滅乎?狼居胥之封徒草草耳。毀無(wú)足稱,然睹鴻雁之飛而獨(dú)傷懷抱者,竊有感于傳之事也。夫去病依次偽功而取封,子卿守節(jié)而薄賞,適蓋有慨于當(dāng)時(shí)矣。”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xué)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