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朱偉《重讀八十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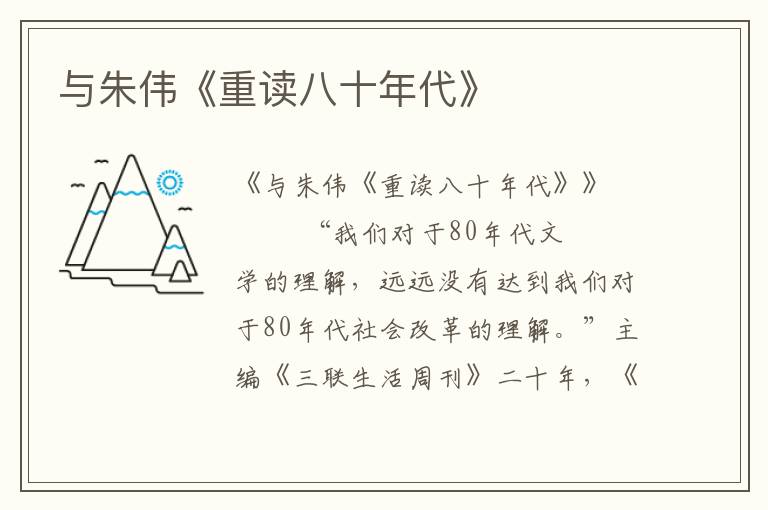
《與朱偉《重讀八十年代》》
“我們對(duì)于80年代文學(xué)的理解,遠(yuǎn)遠(yuǎn)沒(méi)有達(dá)到我們對(duì)于80年代社會(huì)改革的理解。”
主編《三聯(lián)生活周刊》二十年,《重讀八十年代》讓退休后的朱偉又回到了文學(xué)(蔡小川 攝)
2013年,朱偉曾在博客中以《我與八十年代》為題,想依自己的生活軌跡回憶80年代的各個(gè)節(jié)點(diǎn),記錄他與一位位作家的交往過(guò)程。可惜的是,文章剛剛寫(xiě)到1980年,就沒(méi)再更新了。是因工作繁忙。那時(shí)候,作為《三聯(lián)生活周刊》的主編,編輯工作占用了他幾乎全部的時(shí)間。
2015年,退休后,朱偉開(kāi)始應(yīng)邀給周刊寫(xiě)專(zhuān)欄“80年代”,寫(xiě)作對(duì)象是他在80年代熟悉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從第一篇解讀王蒙開(kāi)始,少則五六期,多則用十余期欄目的體量,通過(guò)作家的創(chuàng)作背景、寫(xiě)作意圖和特點(diǎn),完成對(duì)一個(gè)作家的梳理,兼有與他們交往的回憶。三年時(shí)間,已寫(xiě)到的作家有李陀、韓少功、陳村、史鐵生、王安憶、莫言、馬原、余華、蘇童、格非等人,最近在寫(xiě)賈平凹。如今,大部分文章被集結(jié)成書(shū),命名為《重讀八十年代》。
朱偉說(shuō),這個(gè)專(zhuān)欄的寫(xiě)作建立在他與作家熟識(shí)的基礎(chǔ)上。他口中的“熟識(shí)”,大概與我們現(xiàn)在的定義不同,至少程度不同。在80年代,趣味相投的人是可以用大把大把的時(shí)間,從早到晚,整日整夜混在一起的。那時(shí)候,他是《人民文學(xué)》的編輯,與作家們既是編輯與寫(xiě)作者的關(guān)系,也是朋友知己。他的文學(xué)履跡,除了每周一遍遍巡查全城的書(shū)店搜尋新書(shū),就是騎著自行車(chē)從一個(gè)作家家里出發(fā),去見(jiàn)另一個(gè)作家。
朱偉那時(shí)住在白家莊,張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東大橋,鄭萬(wàn)隆住東四四條,史鐵生住雍和宮大街,阿城住廠橋,都是抬腿就到的距離。80年代的親密無(wú)間,是彼此都不用打招呼,隨時(shí)敲門(mén)就進(jìn)。“我還清楚記得,早晨我騎車(chē)去阿城家里,他總在被子里甕聲甕氣說(shuō):‘催命鬼又來(lái)了?’傍晚去,他則總不在,桌上有留言:‘面條在盆里。’”“最難忘的是1990年夏天,余華、格非一起在我家看世界杯。那個(gè)決賽之夜,我們準(zhǔn)備了啤酒與各種吃食,余華堅(jiān)挺馬拉多納,我則賭德國(guó)隊(duì),格非態(tài)度游移。”多讓人羨慕的回憶!
文學(xué)之繁盛,80年代《人民文學(xué)》的發(fā)行量能達(dá)到100多萬(wàn)。作家只要在這個(gè)被稱(chēng)為“皇家刊物”的文學(xué)雜志上發(fā)表一篇小說(shuō),就可以成為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的會(huì)員。當(dāng)時(shí),很多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是經(jīng)朱偉之手發(fā)表的。一個(gè)好編輯之于一個(gè)好作家,不僅僅意味著發(fā)掘,還存在培養(yǎng),就像之于成長(zhǎng)的一方肥沃的土壤。因此,作為編輯,不僅僅是與作家同為文學(xué)潮流的經(jīng)歷者,也同樣是參與締造者。
可以說(shuō),解讀80年代的文學(xué),恐怕很難有比朱偉更合適的人了,且他依然可以讀得那么認(rèn)真!文章的寫(xiě)作程序大致是這樣的:作家把全部作品和作品發(fā)表的順序給他,他從他們的創(chuàng)作論中確定一個(gè)標(biāo)題,然后一本書(shū)一本書(shū)地閱讀,在閱讀中尋找破解結(jié)構(gòu)的途徑。這些小說(shuō),很多他過(guò)去都讀過(guò),有些就是經(jīng)他之手發(fā)表的,現(xiàn)在也都一一仔細(xì)重讀。讀的過(guò)程中,有疑問(wèn)再去問(wèn)作家。如此,一周內(nèi)通讀一部長(zhǎng)篇或兩部中篇,動(dòng)輒幾十萬(wàn)字,再寫(xiě)出分析的文字,保證每周的專(zhuān)欄,工作量不可說(shuō)不繁重。每一篇文章發(fā)表前,朱偉還會(huì)發(fā)給作家看。他說(shuō),對(duì)他而言,就像是交考試答卷,答完要請(qǐng)作家審閱。“他們一般都滿意,說(shuō)幾句好話,‘寶刀不老、理解我者還是朱偉’等等,我付出的辛苦亦就得到滿足。”
重讀之后,朱偉的結(jié)論是:“就我已梳理完的這些作家而言,如將他們看成一個(gè)整體,就已經(jīng)是很驕傲的一個(gè)時(shí)代了。這個(gè)作家群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與自身的思考,其實(shí)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超越了20世紀(jì)的前輩作家。”一本書(shū)下來(lái),雖然還有很多重要的作家沒(méi)來(lái)得及收錄或還沒(méi)有寫(xiě)到,比如,汪曾祺、陳忠實(shí)、路遙、阿城、王朔、劉震云、王小波……但可以看到,一部個(gè)人經(jīng)歷的80年代文學(xué)史正在完成。
朱偉說(shuō),也許再花幾年時(shí)間,涉及的作家更廣泛些,才可說(shuō)形成系統(tǒng)和規(guī)模,且一部文學(xué)史,還必須對(duì)80年代各個(gè)階段社會(huì)背景的烙印做出反映。就眼下的這本書(shū),他始終只是強(qiáng)調(diào)導(dǎo)讀的意義,更在意的是自己對(duì)作品,對(duì)作家創(chuàng)作軌跡的解讀,希望有助于讀者更好地了解那些作品。用他的話說(shuō),這正是一個(gè)編輯該做的工作。而我們看到的,是一堂堂興味盎然的文學(xué)課。“80年代文學(xué)對(duì)于中國(guó)文學(xué)史,對(duì)于文學(xué)的發(fā)展到底構(gòu)成了多大的承啟作用?這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到底構(gòu)成了什么? 這是一個(gè)特別重要的事情。”朱偉說(shuō)。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你說(shuō)自己對(duì)作家作品的解讀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導(dǎo)讀,為什么倡導(dǎo)文學(xué)作品需要導(dǎo)讀?
朱偉:我們過(guò)去講一個(gè)作品需要接受美學(xué),作家的創(chuàng)作在讀者中間需要有一個(gè)接受,實(shí)際上就是你對(duì)他作品的閱讀,你的解讀方法。這就跟破案一樣,案子就是作品,怎么能把案子中間真正的案情破清楚,是考驗(yàn)一個(gè)閱讀者和作家的智商能不能對(duì)接的問(wèn)題。
很多讀者閱讀作品可能會(huì)被故事?tīng)恐疲瑢?shí)際并沒(méi)有讀懂。小說(shuō)的表面是故事,作家在寫(xiě)故事的背后有一個(gè)目的,要通過(guò)故事去了解目的,就需要有導(dǎo)讀。導(dǎo)讀是從作家到他具體的作品,首先讓你了解他們各自的寫(xiě)作方法是如何,然后了解每一部作品的創(chuàng)作意義,也就是寫(xiě)這個(gè)故事的目的是什么。這就是我的工作。
我覺(jué)得實(shí)際上存在一個(gè)“文學(xué)課”的問(wèn)題。小說(shuō)閱讀可以說(shuō)是在藝術(shù)修養(yǎng)中最最普遍的一種修養(yǎng),人們讀小說(shuō),有的人就是為了讀故事、讀消遣,有的人就是為了讀經(jīng)典。現(xiàn)在大家都覺(jué)得文學(xué)修養(yǎng)特別重要,我覺(jué)得它是需要老師來(lái)帶的,從某種角度上講,就是文學(xué)課。
納博科夫有本書(shū)叫《文學(xué)講稿》,我還是在80年代看的,那時(shí)還有一本福斯特寫(xiě)的《小說(shuō)面面觀》和一本《現(xiàn)當(dāng)代小說(shuō)99篇》,推薦99本書(shū),了解現(xiàn)當(dāng)代最重要的作品,每個(gè)作品有一個(gè)簡(jiǎn)單的介紹。我覺(jué)得我做的工作就是這樣的。
離開(kāi)《人民文學(xué)》,做《三聯(lián)生活周刊》20年,我現(xiàn)在回過(guò)頭來(lái)看,重新跟這些作家做交流,把我寫(xiě)的東西給他們看,實(shí)際上是給作家交一份答卷,讓他們來(lái)看我對(duì)他們的分析是否能有會(huì)心一笑,然后他們覺(jué)得我仍然是寶刀未老吧,我的閱讀還是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三聯(lián)生活周刊: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作家自己都能看到嗎?
朱偉:有的東西作家能意識(shí),有的東西他也不一定能意識(shí)到。因?yàn)樗趯?xiě)作中間,也會(huì)被寫(xiě)作牽制著走。比如莫言,他很特殊,他寫(xiě)長(zhǎng)篇小說(shuō)一天可以寫(xiě)一萬(wàn)八千字,就像流水一樣,一氣呵成。這中間他未必思考那些問(wèn)題。你去對(duì)他做總結(jié),他覺(jué)得你講得非常對(duì),那正好。而有的作家構(gòu)思是很清晰的,比如余華,每天寫(xiě)得很慢,基本上每一段句子都是經(jīng)過(guò)深思熟慮的,他就是在有意識(shí)地寫(xiě)作。作家和作家之間很不同,這就需要你去辨別。
我以前總是舉一個(gè)例子,就是斯皮爾伯格,他說(shuō)他拍電影是把一顆石子扔到樹(shù)林里面,去尋找石子的過(guò)程就是一部電影。一個(gè)作家的寫(xiě)作也是這樣,他先有一個(gè)想法,然后這個(gè)想法慢慢膨脹,變成一部作品,方法不同。作為一個(gè)編輯,去閱讀,在閱讀中間去想這個(gè)故事背后可能有什么,讀完之后,去想這個(gè)故事背后的邏輯是什么。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你閱讀一個(gè)小說(shuō),會(huì)關(guān)注哪些方面?
朱偉:我們當(dāng)初閱讀小說(shuō),覺(jué)得小說(shuō)當(dāng)中有三個(gè)層面,第一是它的故事,第二是它的氛圍,第三是它的內(nèi)核,小說(shuō)中間有可能通過(guò)結(jié)構(gòu)表達(dá)的東西。我的說(shuō)法是,這就是一個(gè)專(zhuān)業(yè)的對(duì)小說(shuō)的解讀方法。我對(duì)這些作家的梳理基本上就是這樣,首先把他的特征梳理出來(lái),然后把每一個(gè)作品的寫(xiě)作意圖告訴讀者,讀者可以作為一個(gè)啟發(fā),再去閱讀這些作品的時(shí)候,會(huì)發(fā)現(xiàn)原來(lái)可以找到這樣一個(gè)路標(biāo)去理解作品。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你通過(guò)什么來(lái)判斷一部作品?在做《人民文學(xué)》編輯時(shí),主要憑感覺(jué)還是用方法?
朱偉:無(wú)論是好作家的誕生、好編輯的誕生,還是好讀者的誕生,一個(gè)人的認(rèn)識(shí),都是因?yàn)樗拈啔v。我始終強(qiáng)調(diào)一個(gè)人的閱讀量,如果沒(méi)有一定閱讀量的累計(jì),就不會(huì)有閱歷。閱讀量使量變達(dá)到質(zhì)變,通過(guò)閱讀很多作品才能知道作品中間有一個(gè)結(jié)構(gòu)的問(wèn)題,作家和作家之間是有區(qū)別的。這還不夠,不能僅僅讀小說(shuō),還需要有其他的積累,比如哲學(xué)、認(rèn)識(shí)論的積累。哲學(xué)的方法很重要,它會(huì)告訴你一個(gè)邏輯編碼,就像數(shù)學(xué)公式,有了哲學(xué)的基礎(chǔ)你就可以從作品的更深處去了解。
我原來(lái)講過(guò)一個(gè)讀書(shū)的話題,一個(gè)人需要不斷地顛覆自己,當(dāng)你熟悉了一種閱讀以后,就要跳出來(lái),去閱讀你不熟悉的東西,然后通過(guò)閱讀不熟悉的東西擴(kuò)大閱讀面,因?yàn)榕龅讲皇煜さ臇|西,你就會(huì)拼命去鉆,熟悉的東西只會(huì)順理成章地讀,不會(huì)進(jìn)入另一個(gè)領(lǐng)域,進(jìn)入另一個(gè)領(lǐng)域再來(lái)看這個(gè)領(lǐng)域,它可能就不一樣了。這就是我們講的看一個(gè)東西要同時(shí)打開(kāi)好幾個(gè)窗口。有的人只是順著自己的一個(gè)方向,那就會(huì)變成一個(gè)匠人。
我在做《人民文學(xué)》編輯的時(shí)候也經(jīng)歷了幾個(gè)階段,剛開(kāi)始的時(shí)候是用感性,我的感覺(jué)相當(dāng)不錯(cuò)。80年代初期我和王蒙認(rèn)識(shí),他就覺(jué)得我的感覺(jué)非常好,他寫(xiě)一篇小說(shuō)讓我看哪兒好哪兒不好,我說(shuō)得非常對(duì)。這個(gè)判斷就建立在閱讀量上,我讀了很多外國(guó)小說(shuō),它們變成了我的框架。到了80年代中后期,我發(fā)覺(jué)我的理論性不夠,就開(kāi)始讀哲學(xué)。當(dāng)讀了一定的哲學(xué)之后,我就覺(jué)得自己對(duì)作品的認(rèn)識(shí),對(duì)作家的認(rèn)識(shí)上升了一個(gè)層面。
后來(lái)我離開(kāi)《人民文學(xué)》做《三聯(lián)生活周刊》,特別雜,需要對(duì)各種各樣的選題迅速做出判斷,不僅僅是文學(xué),還有經(jīng)濟(jì)的、社會(huì)的。尤其是做封面故事,要判斷往哪個(gè)方向走,我對(duì)作品的結(jié)構(gòu)有了更高的理解。這種方法和你的閱歷有關(guān)系,你的閱歷越廣,你使用的方法就越便利。這是我所說(shuō)的文學(xué)課里面更深層次的一個(gè)問(wèn)題。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作為一個(gè)編輯,你如何判斷一個(gè)作家是否能成為大家?
朱偉:這也是一個(gè)認(rèn)識(shí)論的問(wèn)題。一個(gè)人要形成別人走不了的道路,這個(gè)人才能成為大家。我看一個(gè)作家有沒(méi)有可能脫穎而出,前提是他的寫(xiě)作方法能不能區(qū)別于別人。好的作家一定形成一種獨(dú)特的寫(xiě)作方法,這種方法使人眼前一亮。如果一個(gè)作家總是在模仿,或者總是在重復(fù)自己,就不能成為大作家。格非如果順著《敵人》寫(xiě)下去,就不能成為大作家,但他在寫(xiě)《人面桃花》的時(shí)候變了,寫(xiě)了“江南三部曲”,那他就成了大作家。如果賈平凹只寫(xiě)了《浮躁》《廢都》也不是大作家,但是他寫(xiě)了《古爐》,沒(méi)有一部作品寫(xiě)“文革”寫(xiě)得那么深刻的。
三聯(lián)生活周刊:在作家成為大作家的過(guò)程中,編輯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朱偉:一個(gè)好的作家生長(zhǎng)是需要土壤的,沒(méi)有一個(gè)好的編輯就沒(méi)有一個(gè)好的作家生長(zhǎng)的土壤。不論是發(fā)表還是出版,一個(gè)編輯要看準(zhǔn)作家的作品是重要的,推他的作品。一個(gè)好的編輯,會(huì)不斷地按照適合的方法引導(dǎo)作家,讓他去走,越走越大。我和作家之間良好的關(guān)系就是這樣一點(diǎn)點(diǎn)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比如莫言,剛開(kāi)始寫(xiě)作的時(shí)候,第一篇小說(shuō)不是我發(fā)的,從第二篇就是我發(fā)的了,那么從《爆炸》到《紅高粱》再到《歡樂(lè)》,完成了他的三級(jí)跳。這個(gè)過(guò)程中我和他有交流,一個(gè)編輯就參與了一個(gè)作家的成長(zhǎng),或者說(shuō)一個(gè)編輯要通過(guò)與一個(gè)作家的交流使得作家能夠越做越大。當(dāng)然他后來(lái)的作品都不是我經(jīng)手的,我后來(lái)已經(jīng)離開(kāi)文學(xué)了。
三聯(lián)生活周刊:現(xiàn)在回看80年代的作家和作品,和你過(guò)去看他們有什么不一樣的視角嗎?
朱偉:很不一樣。重新看80年代的文學(xué)和這些作家,我覺(jué)得我真正看到了他們對(duì)中國(guó)文學(xué)構(gòu)成的特別重要的意義,就像我們?cè)趺磥?lái)認(rèn)識(shí)80年代中國(guó)的改革開(kāi)放的重要性一樣。80年代中國(guó)改革開(kāi)放是如何重要,80年代中國(guó)文學(xué)的重要性也就如何重要。只不過(guò)我們對(duì)于80年代文學(xué)的理解,遠(yuǎn)遠(yuǎn)沒(méi)有達(dá)到我們對(duì)于80年代社會(huì)改革的理解。
真的沒(méi)有多少人懂文學(xué)到底構(gòu)成了多大的意義。過(guò)去80年代構(gòu)成了一批批評(píng)家,但那時(shí)候的批評(píng)家不是真正地從整體上對(duì)這些作家、對(duì)文學(xué)的重要性做判斷的。這些作家的創(chuàng)作,現(xiàn)在慢慢印量沒(méi)有那么大了,年輕人讀他們的東西越來(lái)越少,從整體的文學(xué)意義上來(lái)講,我覺(jué)得沒(méi)有得到特別好的強(qiáng)調(diào)。
80年代文學(xué)對(duì)于中國(guó)文學(xué)史,對(duì)于文學(xué)的發(fā)展到底構(gòu)成了多大的承啟作用?這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到底構(gòu)成了什么?這是一個(gè)特別重要的事情。這本書(shū)里有些作家我還沒(méi)談到,比如汪曾祺、陳忠實(shí)、王小波……賈平凹我快寫(xiě)完了,還有更多。過(guò)去我們講中國(guó)文學(xué)的重要性可能是講中國(guó)有魯迅、錢(qián)鍾書(shū)、張愛(ài)玲等等,一種普遍的看法是,80年代這些作家還是建立在西方文學(xué)的上面。但當(dāng)我一個(gè)個(gè)去讀了那么多作品之后,把他們作為一個(gè)整體看待,才感覺(jué)到80年代的整體的重要性。他們基本上沖決了束縛,越來(lái)越多的作家無(wú)所顧忌地寫(xiě)人性的惡,不寫(xiě)人性的惡,怎么能夠襯托出人性的善呢?寫(xiě)作越來(lái)越自由,才有可能出現(xiàn)各種各樣的類(lèi)型。這是80年代特別了不起的地方。
三聯(lián)生活周刊:具體來(lái)說(shuō),80年代這批作家構(gòu)成的重要意義表現(xiàn)在哪兒?
朱偉:首先是差異性,這些作家各自構(gòu)成了非常不同的寫(xiě)作方法。同時(shí),雖然很多作家借用了西方的一些敘述或結(jié)構(gòu)方式,但是他們都在各自的形式里寄托自己對(duì)社會(huì)生活的理解,做出了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的思考,對(duì)國(guó)民性的思考,對(duì)自己的思考,并且達(dá)到了相當(dāng)?shù)纳疃取N覀€(gè)人的觀點(diǎn)是,他們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了20世紀(jì)的前輩作家。
比如說(shuō)莫言、賈平凹、陳忠實(shí)對(duì)中國(guó)農(nóng)村的了解。中國(guó)是一個(gè)農(nóng)業(yè)社會(huì),中國(guó)作家的問(wèn)題就是如何思考農(nóng)村,如何思考自己。我覺(jué)得一個(gè)作品的深度,與一個(gè)作家對(duì)自己、對(duì)土地的理解有關(guān)。作家創(chuàng)作不能僅限于意識(shí)形態(tài),我是反對(duì)意識(shí)形態(tài)解讀的,那樣很容易變成,這個(gè)作品在控訴什么、在歌頌什么,有一個(gè)政治性在里頭。如果從一個(gè)大的社會(huì)形態(tài)理解的話,就要對(duì)中國(guó)的社會(huì)、國(guó)民性、對(duì)自己做出一個(gè)解答。
當(dāng)然,這些作家的思考也有深淺不同,比如有的就很回避自己,你很難在他的作品中間找到他自己。有的就容易。但總的來(lái)講還是很了不起的,如果真把80年代這些創(chuàng)作做一個(gè)梳理,這30年里,能有30部重要作品,從百年史的角度來(lái)講,已經(jīng)很不錯(cu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