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棄李斯的“鼠目寸光”——小人得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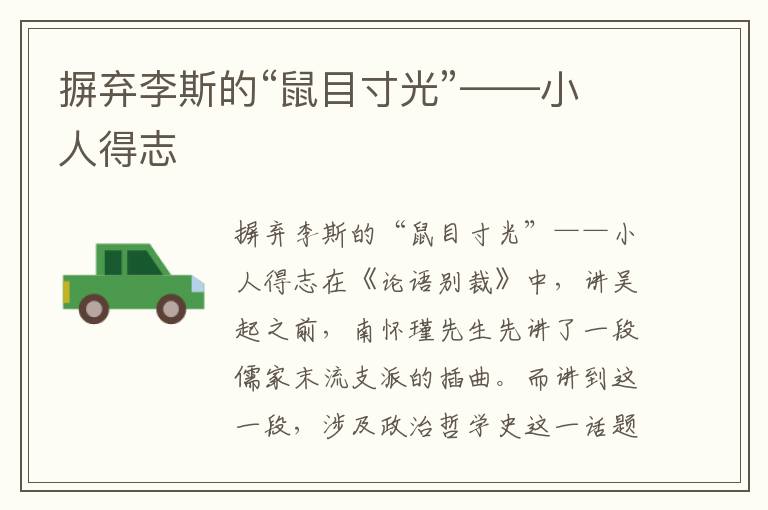
摒棄李斯的“鼠目寸光”——小人得志
在《論語別裁》中,講吳起之前,南懷瑾先生先講了一段儒家末流支派的插曲。而講到這一段,涉及政治哲學史這一話題的時候,南先生重點講了李斯。南先生說,我們可以把李斯的哲學叫做老鼠哲學。
事實上,南先生無比痛斥李斯的老鼠哲學,甚至直言不諱地罵道:“結果李斯碰到秦始皇這樣一個混蛋,兩個搞在一起,于是把一個國家搞得民不聊生。”為何南先生會嚴厲批判李斯的老鼠哲學?那么我們先來弄清楚,究竟什么是老鼠哲學。
眾所周知,少年時的李斯家境貧寒,當時他師從荀子。據《史記》記載,在李斯當小吏期間,有一天,李斯去上廁所,看到糞坑里的老鼠,長得又小又瘦,見到人就倉皇地逃跑,樣子十分可憐,也很卑賤。后來又有一次,他經過米倉的時候,發現在米倉中偷米吃的老鼠又肥又大,見到人也不怕,不但不逃跑,反而顯得很神氣。
李斯琢磨了半天,反而給他悟出了一個現實的道理來:恥辱莫大于卑賤,悲哀莫大于貧困。廁鼠饑之食糞便,而人狗見之,則奮力追打,總是生活在一種驚恐和偷食之中;倉鼠食囤積之糧,棲息在寬大的廊檐下,而人狗不擾。可見人之賢與不賢,與他所處的環境有非常大的關系。用李斯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在所自處耳”。
對此,南先生將李斯的“在所自處”解釋為“有所憑借”。李斯認為,廁鼠之所以見人就跑,是因為它們無所憑借;而倉鼠見人反而表現得很神氣,是因為它們有所憑借。進而,南先生將“憑借”理解為有本事,有靠山,有本錢之類。
李斯因老鼠而領悟到現實的道理之后,便辭別荀子,說:“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故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而這也正是李斯的老鼠哲學。荀子一聽,說,你這個學生的這種思想真是很糟糕,你快去吧!于是就放棄了李斯。
結果,如南先生所說:“李斯和秦始皇兩個混蛋,‘鼠目寸光’,只搞老鼠哲學注重現實,不知仁義道德為何物的結果,自秦始皇身死沙丘之后,李斯也自家難保。所以在他父子臨刑的時候,他對兒子說:‘此時要想和你牽黃犬出東門也不可能了。’”
由此可見,李斯的老鼠哲學,縱然一時讓他能夠成功,但是,也不過是暫時的,當他失去了他的憑借的時候,他便難以保全自己。更主要的是,李斯的成功,也不過是小人得志;他越得志,對國家和百姓,越是種禍害。況且,李斯靠著他“鼠目寸光”的老鼠哲學取得成功,也有很大的歷史偶然在其中。
回到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我們必須想到一句話:“斯人已去,后人鑒之。”特別是在我們的職場生活中,李斯的老鼠哲學更是我們應當摒棄和規避的。但事實上,很多人都在潛意識里踐行著李斯的“老鼠哲學”,并且對此獲得的成功引以為傲。殊不知,這是把自己的成就建立在損害別人的利益之上。用南先生的話來說,就是“不知仁義道德為何物”。
大家都知道,李斯搞老鼠哲學,一切以自己眼前的利益為重,不念舊情,殘害自己的同窗韓非;史上愚昧的“焚書坑儒”也是李斯提出的建議……而在我們的職場上,類似的人甚而有之。比如,為了與同事爭得某個頭銜、職位,獲取某種獎勵,甚至不惜損害同事之間的情誼,明槍暗箭,甚至鉤心斗角。縱然最后贏得了自己一直渴望的東西,可是仁義道德又何存?為了取勝,而傷害別人,甚至喪盡天良,沒有一點道德心,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甚至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心里是否還會有一些愧疚感和恥辱感?
這也正是南先生痛斥李斯老鼠哲學現實依據。在職場中,我們應當摒棄李斯的老鼠哲學,以免自己淪為一個得志的小人。這不僅是破壞職場和諧的大害,從長遠角度來看,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表現。
仔細想想,縱然一時風光,有所憑借,但是,終究還是倚賴著別人,別人可以提拔你,必然也可以給你穿“小鞋”,甚至攆你走。人要靠自己,才是王道。自己要站住腳,不僅要有真本事,還要心存仁義道德之心,凡事要對得起天地良心,要得人心。特別是在利益沖突明顯的職場中,我們更應該做一個正直、有長遠眼光、有本事的君子,而非如李斯一樣,小人得志。事實證明,小人得志,并不久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