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干《山亭與老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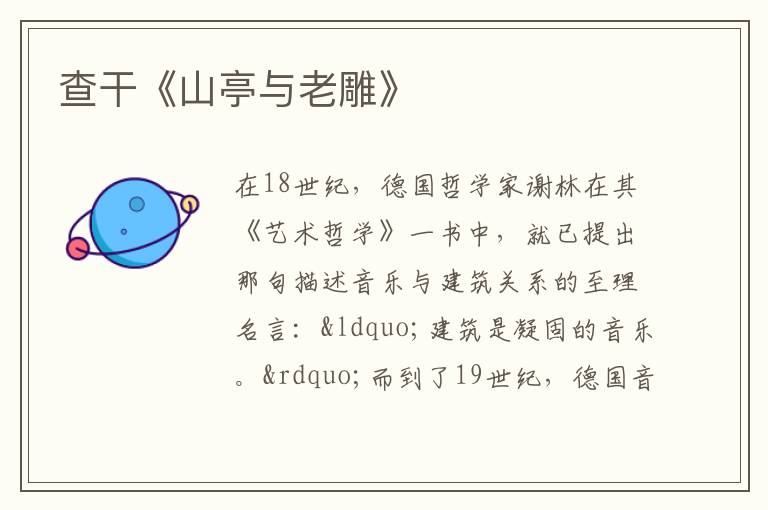
在18世紀(jì),德國哲學(xué)家謝林在其《藝術(shù)哲學(xué)》一書中,就已提出那句描述音樂與建筑關(guān)系的至理名言:“建筑是凝固的音樂。”而到了19世紀(jì),德國音樂理論家和作曲家霍普德曼又補充說:“音樂是流動的建筑。”以此推理,中國園林藝術(shù)中的亭、臺、樓、閣,可不可以說是一架架錚錚琮琮、余音裊裊的祖?zhèn)鞴徘伲瑥棑苤两瘢?/p>
比如亭。亭,起源于周朝。起先,多建于路旁,供行人休息,乘涼或觀景用。亭,一般為開敞性結(jié)構(gòu),沒有圍墻,頂部可分六角、八角、圓形等多種形狀。古籍解釋:亭,從高從丁,停也。道路所舍,人停集也,亭是供人停宿用的。
亭有多種,如:路亭、半山亭等。在園林藝術(shù)中,它是亮點,也是魂,假若不設(shè),就少了內(nèi)涵。古時建亭,可分木亭、石亭等。到了現(xiàn)代,又有了鋼筋混凝土亭、鋼結(jié)構(gòu)亭等多種。
關(guān)于亭,一言兩語是說不盡的。亭與人近,內(nèi)含溫馨。古人送友,往往在亭子里話別。中國的亭臺,不計其數(shù),我登過的,恐怕也不下幾百座了。歷來,亭乃景之窗口。有亭,必有景,這是傳統(tǒng),也是規(guī)矩。
在我記憶中,我喜愛的是一座茅亭。我們稱它為山亭,是建在半山腰之緣故。茅亭,乃亭之鼻祖,資格比其它亭類都要老。這座茅亭,結(jié)構(gòu)極為簡單,把六根原木稍事加工,埋入地里,上覆茅草便了事。
我說的這座茅亭,是建在一處野性的國有林場里,地處故鄉(xiāng)的罕山山脈南麓。從此東望,便是小興安嶺莽莽蒼蒼的一碧林海。有一年的深秋季節(jié),我在那個林場小住月余。林場黨委書記特木爾原是一位騎兵戰(zhàn)士,因形勢需要,脫下軍裝,回鄉(xiāng)任職。
這座茅亭,他親自動手,選址、擇木,拉鋸、斧削等活兒,無一不參與。亭,在半山腰。離場部有一華里之距。用途有三:一,護林觀察;二,職工工間休息,喝茶用食;三,觀景、辦公。一年四季,他的大部分辦公時間都在這里。他說,坐在這里,一抬頭,整個林場,一覽無余,瞅著暢快,心也安穩(wěn)。
亭,由六根樺木樁子組成。柱子與柱子之間,足有三米之距。下方橫木搭在柱子三面,供人坐用。上頂是由金黃色的茅草編織而成的大草帽,戴在亭頭,很是威嚴(yán),也顯得粗獷。
上亭的小路,由片石鋪設(shè)而成。亭上方橫梁上,用火剪燙成三個大字:松鷹亭。亭下是一片林海,松濤萬頃,引得金雕三五成群的來,盤旋,觀賞。金雕是獨立行動的飛禽,是獨行俠。由于林場美,又有獵物,雕獨來而成群,也互不排斥。金鷹的蒙古語叫阿拉坦布日古德。我當(dāng)兵在連隊時,我們的文藝宣傳隊還演出過一個獨幕話劇,就叫“阿拉坦布日古德”,我是主演,也因此與鷹結(jié)緣,幾天不見鷹,心里就發(fā)慌。鷹,是通人情的,這座茅亭,不僅屬于我,也屬于鷹。
這日清晨,天空格外晴朗,秋風(fēng)一陣陣蕩來,松聲遍野,草露亮晶晶的,路旁的野花剛剛蘇醒,以露梳妝。離亭大概有五六十米處,我停步,抬頭,果然有一只老雕,落在亭中圓桌旁,安詳?shù)卦诖蝽铩<?xì)看,是一只栗褐色的金雕,比一般的雕類大了很多。我止步,靜靜地看,只怕吵醒了它。心里則描摹著一幅幅剪影:鷹與亭,草露與野花。
這時,起床的黎明號聲響起來了,孩子們要乘車去五里外的學(xué)校上課了。聽到號聲,金雕也醒了,見我這張陌生的臉,也不緊張。昂起頭,睜大眼睛,拍拍巨翅,起飛了。它在空中盤旋了幾圈,就消失于云天迷蒙處了。據(jù)特木爾說,這只金雕,幾乎以亭為家,戀情感人,它本核棲息在高巖巨樹上的。是啊,這里既然叫作松鷹亭,鷹怎會缺席,不來堅守它的陣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