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釣竿》浩子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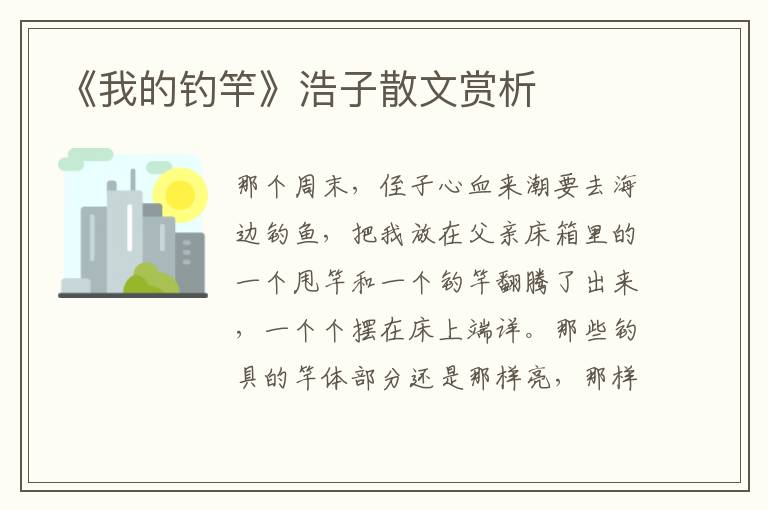
那個(gè)周末,侄子心血來(lái)潮要去海邊釣魚(yú),把我放在父親床箱里的一個(gè)甩竿和一個(gè)釣竿翻騰了出來(lái),一個(gè)個(gè)擺在床上端詳。那些釣具的竿體部分還是那樣亮,那樣新。只是魚(yú)線已經(jīng)泛黃,有些老化和變形。幾個(gè)銹跡斑斑的魚(yú)鉤依然掛在上面。魚(yú)竿的穿線金屬環(huán)也長(zhǎng)了綠銹,透著歲月厚厚的釉質(zhì)感。
我有很長(zhǎng)時(shí)間沒(méi)摸這些東西了,幾乎將它們忘了。想起來(lái)挺可笑,有時(shí)我們的記憶也很勢(shì)力和現(xiàn)實(shí)。它只會(huì)牢牢綁架我們的需要和關(guān)注,而將那些不甚攸關(guān)的,都慢慢過(guò)濾掉、丟棄掉,讓它變成繁雜生活中的沉積層,與那些無(wú)關(guān)的泥土慢慢地凝結(jié)在一起,被匆忙的腳步所踩踏,被日趨僵硬的地表漸漸覆蓋……
其實(shí),我很愛(ài)釣魚(yú)。但花很多錢買魚(yú)竿去釣魚(yú),卻不是我的本意。那些漁具是我在廠辦室當(dāng)秘書(shū)時(shí)買的,全是日本貨,竿體是碳纖維的,分量輕,柔韌性強(qiáng),不易折斷。釣竿的滑輪非常靈敏,甩出去時(shí)聲音極小,收線時(shí)又快又穩(wěn),還伴著歡快的滴答聲,很少有魚(yú)兒脫鉤。那時(shí),漁具店有幾種魚(yú)竿,有竹子做的,有塑料做的,也有碳素材料做的。碳素材料的魚(yú)竿也分國(guó)產(chǎn)的和進(jìn)口的。雖然都是魚(yú)竿,也都可以釣魚(yú),但魚(yú)竿的“顏值”有所不同,價(jià)格也差距很大,少則兩三倍,多則十幾倍。我們常常讓老板把各式各樣的滑輪都拿出來(lái),把耳朵貼在不同滑輪的邊緣,聽(tīng)搖柄轉(zhuǎn)動(dòng)時(shí)的聲響,其中的質(zhì)量?jī)?yōu)劣耳朵自然會(huì)告訴我。但我知道,我不能買便宜的,只能圍著貴的打轉(zhuǎn)轉(zhuǎn)。
不就是釣魚(yú)嗎,什么魚(yú)竿不能釣魚(yú)?記得,我小的時(shí)候,要去海邊釣魚(yú)時(shí),就喊鄰居柳細(xì)哥哥,和他要些舊魚(yú)線,胡亂地綁在一根細(xì)竹竿上。竹竿不是很直,歪歪扭扭的,上面還滿是咯手的竹節(jié)。柳細(xì)哥哥綁好了魚(yú)鉤,再找一個(gè)大一點(diǎn)的舊螺母,拴在魚(yú)線的最下面當(dāng)魚(yú)墜。然后將線一圈又一圈纏在竹竿上,肩上一扛就出發(fā)了。
我們釣魚(yú)都去那個(gè)河與海交匯的“河汊子”,那里有一個(gè)廢棄的石頭壩。向著海口的那段壩體已經(jīng)被海浪沖毀了,很多石塊散落在大壩周圍,表面上長(zhǎng)滿了像苔蘚一樣的海草。海水蕩漾,綠絨似的海草隨波搖曳,間或有小魚(yú)穿梭其間。柳細(xì)哥哥說(shuō),千萬(wàn)不要踩那上面,很滑,會(huì)摔到水里。
柳細(xì)哥哥會(huì)看潮汐,每次釣魚(yú),我們都能見(jiàn)到海水退去后留下的大片灘涂。但壩的四周卻有著一道很寬很長(zhǎng)的深溝,我總有一種感覺(jué),那里面一定有各種各樣正在游動(dòng)或是覓食的魚(yú)。
“河汊子”往東是一個(gè)漁碼頭。那里的漁船早晨很早起航,臨近中午靠岸卸魚(yú);下午,日在正中又起航了,傍晚再回來(lái)“錨船”。漁民在那里搭了窩棚,煮飯、喝酒、睡覺(jué)都在那里。晚上,他們圍在一起抽著嗆人的旱煙,講著兒童不宜的葷笑話。白天,有的在樹(shù)蔭下拿著梭子織補(bǔ)著漁網(wǎng),有的亮著古銅色的脊背,手握著鑿子、斧子或是錛子,在烈日的沙灘上修著船。他們嘴里叼著用煙葉擰成的“錐子把”。那紙煙不像是火柴點(diǎn)著的,倒像是被太陽(yáng)點(diǎn)燃的。因?yàn)轭^頂?shù)奶?yáng)很毒,腳底的沙子很燙。蜷曲的煙灰中,不時(shí)飄出一股股淺藍(lán)色的細(xì)煙,海風(fēng)一吹,一下就沒(méi)了蹤影……
朦朧中,聞到了一股濃烈的魚(yú)腥味和修船的桐油味。我們知道“河汊子”到了。
微曦中的灘涂很夢(mèng)幻,就像一條擱淺的大魚(yú)。那些水洼,就像它身上金色的魚(yú)鱗。我們的魚(yú)食就在那個(gè)夢(mèng)幻的灘涂里。灘涂是黑色的,只是邊緣有黃色的沙灘,看上去很實(shí)很硬,但踩上去就會(huì)陷進(jìn)去很深。艱難地拔出腳,小腿以下已染成黑色。
我們脫掉褲衩和背心,裸著身子用手挖淤泥里的蟲(chóng)子。那是一種淡紅色的多足的腔體動(dòng)物,頭的前端有一對(duì)黑色的螯牙,很像蜈蚣,所不同的是,它藏在泥里,是魚(yú)兒很愛(ài)吃的食物。后來(lái),我知道它的學(xué)名叫“沙蠶”。
那時(shí)海里的魚(yú)很多,柳細(xì)哥哥總是能釣很多魚(yú),但我們卻收獲很少。我總覺(jué)得是柳細(xì)哥哥的甩竿幫助了他。因?yàn)椋乃Ω蜕嫌幸粋€(gè)他自己做的滑輪,“唰啦啦”一聲呼嘯,就把魚(yú)鉤拋得很遠(yuǎn)。所以,他釣的魚(yú)又大又多。我很羨慕他,也有些恨他,按現(xiàn)在的話說(shuō),就是羨慕嫉妒恨。柳細(xì)哥哥是鉗工,手很巧。他的滑輪是用自行車的后軸加上一圈輻條做成的,輻條連著軸在纏線的地方折成了漂亮的圓弧,形成一個(gè)大圓盤(pán),上面纏著魚(yú)線,邊緣像長(zhǎng)了小翅膀。所以,魚(yú)墜也像長(zhǎng)了翅膀,飛得很遠(yuǎn),魚(yú)也釣得很大。只是,他不想給我做,即使我說(shuō)可以找到車軸和輻條,他還是說(shuō):“你太小,甩不好,魚(yú)鉤把你當(dāng)魚(yú)釣了,鉤了你的嘴可不是鬧著玩的。”
后來(lái),我長(zhǎng)大了,挖魚(yú)食時(shí)不再脫去褲衩,也不再用手挖,而是用鐵鍬了,柳細(xì)哥哥依然沒(méi)給我做甩竿。而他的魚(yú)竿上,卻多了一個(gè)報(bào)信的鈴鐺,有魚(yú)咬鉤時(shí)會(huì)發(fā)出急促的鈴聲,叫人特別亢奮。
到了我買了如此高檔的釣竿以后,我們連魚(yú)食也不用挖了。每到周末,我和司機(jī)就開(kāi)著車去大橋的橋頭去買。那里賣魚(yú)食的人很多,他們坐在大柳樹(shù)的陰涼下,身旁支著一輛摩托車,擺著一堆大小不等的木盒。木盒不是很精致,但拾掇得很利索,想得也很周到。沙蠶都經(jīng)過(guò)了篩選,大小一致,沒(méi)有挖斷的,也沒(méi)有化水的。盒里的紅土搓得很細(xì),撒得很勻,沒(méi)有大的礫石,確保那些沙蠶一天一宿也不會(huì)化水、變質(zhì)。大盒的30元,小盒的20元。那些魚(yú)食販子很會(huì)做買賣,買多了會(huì)慷慨地贈(zèng)送一盒。而贈(zèng)送的那一盒,就是我和司機(jī)釣魚(yú)所用。其他的都是廠級(jí)領(lǐng)導(dǎo)的,我們不能染指。那時(shí)釣魚(yú)也談不上興趣,多數(shù)時(shí)間都是服務(wù),誰(shuí)的魚(yú)墜被石頭卡住了,我就要趕緊找魚(yú)墜、魚(yú)鉤;誰(shuí)的魚(yú)食告罄,我就要在自己的盒子里抓上一把送過(guò)去。自己的釣竿上了魚(yú)也來(lái)不及摘。只有把那些呼叫聲都平息了,才能返回來(lái)看自己的魚(yú)竿。我的那個(gè)醬紅色的魚(yú)竿常常孤獨(dú)地躺在沙灘上,在白色沙灘上反射著漂亮的陽(yáng)光。我覺(jué)得,那個(gè)色彩亮麗的高檔魚(yú)竿,還不及我小時(shí)候那個(gè)彎彎曲曲周身都是“骨節(jié)”的竹竿,它只是一個(gè)漂亮的道具、一個(gè)擺設(shè),卻不能給我?guī)?lái)一絲垂釣的快感。
買高檔釣具既有虛榮,也有攀附的成分。那時(shí),用低檔漁具會(huì)給領(lǐng)導(dǎo)跌份。因此,自己感覺(jué),只有拿著碳素魚(yú)竿,才能挺直腰桿,哼著小曲或吹著口哨,在那些斑斕的魚(yú)竿叢中悠閑地釣魚(yú)。
再后來(lái),我的高檔漁具也束之高閣了,一放就是十來(lái)年。我跟父親說(shuō),魚(yú)竿給你吧,沒(méi)事兒釣釣魚(yú),修心養(yǎng)性,陶冶情操,長(zhǎng)壽,健康。父親也沒(méi)去釣。他很長(zhǎng)壽了,但釣不動(dòng)了。雖然魚(yú)竿不沉、魚(yú)也不沉,他卻去不了了。沒(méi)多久,他坐上了輪椅。
再再后來(lái),我連海邊也很少去了。鄰居中倒是有垂釣愛(ài)好者,也常常開(kāi)著車,后備廂里裝著全套的釣魚(yú)用具。碳纖維釣竿進(jìn)口滑輪的甩竿,三四把用帆布袋子裝著,還有竿架、抄魚(yú)用的網(wǎng)抄、不銹鋼做的魚(yú)筐,以及魚(yú)墜、浮漂、魚(yú)線、魚(yú)鉤、魚(yú)餌、精致的折疊垂釣椅,應(yīng)有盡有,一個(gè)不落。只是回來(lái)時(shí),卻罵罵咧咧,埋怨現(xiàn)在海里太窮,去了一整天,也是收獲寥寥。他瞅著我問(wèn),就納悶了,魚(yú)都哪兒去了?就像那次落大潮時(shí),一個(gè)外地朋友問(wèn)我,海水都哪兒去了一樣,當(dāng)時(shí)就把我這個(gè)生在海邊、長(zhǎng)在海邊的人問(wèn)蒙了,是呀,海水哪兒去了?而如今,我同樣蒙了。是呀,魚(yú)都哪兒去了?想想也很可笑,現(xiàn)在釣魚(yú)的魚(yú)竿漁具越來(lái)越好了,魚(yú)卻釣不著了。
“我的背包,讓我走起來(lái)很緩慢,終有一天陪著我腐爛。你的背包,對(duì)我沉重的審判,借了東西為什么不還?”陳奕迅的《你的背包》,像是對(duì)我們唱的。仿佛我們欠了什么東西,卻至今沒(méi)有還似的。我不由自主地哼唱道:“我的釣竿,讓我覺(jué)得很沉重……”記憶總是有既得功能的。釣魚(yú)釣不到時(shí),我們才想起了,小時(shí)候撿到的“海兔子”、被海浪嗆上岸的“大白眼”,它們似乎告訴我們海里很富饒,海洋生物很豐富。我們吃過(guò)很多貝類,花蛤、毛蚶、牡蠣、海蟶子,也有過(guò)去我們從來(lái)不吃的海星、海膽。現(xiàn)在的人們變得太勤勞,鐵筢子已將海底摟了遍,摟得海底的腐殖質(zhì)把黃色沙灘都染黑了。細(xì)密的漁網(wǎng)也把很小的魚(yú)捕撈上來(lái)。人們勤勞久了,把海洋生物鏈也從根上挖斷了,大海焉有不窮之理?人們?cè)谙硎苤笞匀坏酿佡?zèng)時(shí),卻總在重復(fù)著選擇性失憶。只記得索求,卻忘記了賦予。
我真的不愿意再拿那些魚(yú)竿,我似乎總覺(jué)得海里只有化石般的記憶。望著遼闊湛藍(lán)的海水,我總覺(jué)得,是到我們歸還的時(shí)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