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叔河《蝙蝠的不幸》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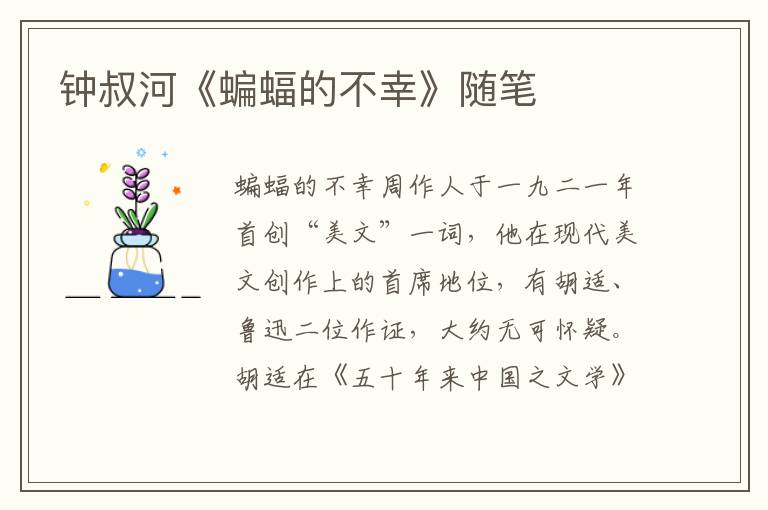
蝙蝠的不幸
周作人于一九二一年首創(chuàng)“美文”一詞,他在現(xiàn)代美文創(chuàng)作上的首席地位,有胡適、魯迅二位作證,大約無可懷疑。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xué)》文中說,“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fā)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把他作為成功的代表。魯迅在答復(fù)斯諾問中國最優(yōu)秀的散文作家是誰時,也把周作人排在第一,排在林語堂和他自己之前。
周作人活了八十多歲,寫了近七十年文章。在這個世界上,他確實留下了許多可以稱為美文的作品,但這不是他工作的全部,也不是他工作的大部。他在《兩個鬼的文章》中寫道:
我的確寫了些閑適文章,但同時也寫正經(jīng)文章,而這正經(jīng)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見,在自己更覺得有意義。
《苦口甘口》自序中更詳細地說到了他的思想和所謂“閑適小品”:
如英吉利法蘭西的隨筆,日本的俳文,以及中國的題跋筆記,平素也稍涉獵,很是愛好,不但愛讀,也想學(xué)了做,可是自己知道性情才力都不及,寫不出這種文字,只有偶然撰作一二篇,使得思路筆調(diào)變換一下,有如飯后喝一杯濃普洱茶之類而已。這種文章材料難找,調(diào)理不易。其實材料原是遍地皆是,牛溲馬勃只要使用得好,無不是極妙文料,這里便有作者的才情問題,實在做起來沒有空說這樣容易了。我的學(xué)問根柢是儒家的,后來又加上些佛教的影響,平常的理想是中庸,布施度忍辱度的意思也頗喜歡,但是自己所信畢竟是神滅論與民為貴論,這就與詩趣相遠,與先哲疾虛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對于古來道德學(xué)問的傳統(tǒng)發(fā)生懷疑,這樣雖然對于名物很有興趣,也總是賞鑒里混有批判,幾篇《草木蟲魚》有的便是這種毛病,有的心想避免而生了別的毛病,即是平板單調(diào)。那種平淡而有情味的小品文我是向來仰慕,至今愛讀,也是極想仿做的,可是如上文所述實力不夠,一直未能寫出一篇滿意的東西來。以此與正經(jīng)文章相比,那些文章也是同樣寫不好,但是原來不以文章為重,多少總已說得出我的思想來,在我自己可以聊自滿足的了。
如其中所說,他所信的神滅論與民為貴論,通常的說法便是賽先生與德先生,實在是理解周作人思想與文章的津梁。就是只想欣賞美文(所謂的“閑適小品”),亦當率由此道,才不致得魚忘筌,舍本逐末。
《兩個鬼的文章》寫成以后,直到一九五九年才編入《過去的工作》在澳門出版,《苦口甘口》印行于淪陷中的北平,解放后更成了禁書,像我這樣在長沙城里拉板車的右派分子,當時都無法看到。但是,我于一九六三年寫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中也是這樣說的:
先生的文章之美,固然對我具有無上的吸力,但還不是使我最愛讀它們的原因。我一直以為,先生的文章的真價值首先在于,它們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態(tài)度,乃是上下數(shù)千年中國讀書人最難得的態(tài)度,那就是誠實的態(tài)度……無論是早期慷慨激昂的《碰傷》《死法》諸文,后來可深長思的《家訓(xùn)》《試帖》各論,甚至就是眾口紛紜或譽為平淡沖和或詈為“自甘涼血”的《茶食》《野菜》那些小品,在我看來全都一樣,都是藹然仁者之言。先生對于我們這五千年古國,幾十兆人民,蕓蕓眾生,婦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憂憤是強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藥方也是開得對的。
時年不滿三十的苦力,當然不敢在五四文壇老宿面前妄托知己,不過在讀到周作人隨后寫了寄來給我的古人詩句“萬卷縱觀當具眼”之后,我還是不禁暗喜。因為于冥冥長夜中知道自己還有一雙看得出好壞的眼睛,在漫漫長路上也就不會像原來那樣不知所從了。
因為我喜歡周作人的文章(不僅僅是他的美文),又因為周作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里給我的一點知己之感,又因為能得到周豐一先生的信任和委托,遂以十年之力搜集、整理了周氏近三千篇文章。事實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在這近三千篇文章中,正經(jīng)的文章確實比閑適的小品多得多。當然,周作人的正經(jīng)文章,也有他所特有的文章之美,即如《兩個鬼……》這一篇,信手拈來,“道士與狐所修煉得來的內(nèi)丹”,“飯后喝一杯濃普洱茶”,又何嘗不是巧妙地使用了“文料”,使一篇說理文達到了平淡而有情味的境界。在本文中,他一再聲言自己實力不夠,性情才力不及,寫不好純文學(xué)的美文,但正如他過去說過的,這里的自謙也就是自夸。《兩個鬼……》在最后重申他作文的原則是言必由衷,道:
其實這樣的做也只是人之常道,有如人不學(xué)狗叫或去咬干矢橛,算不得什么奇事,然而在現(xiàn)今卻不得不當作奇事說,這樣算來我的自夸也就很是可憐的了。……俗語云,無鳥村里蝙蝠稱王。蝙蝠本何足道,可哀的是無鳥村耳,而蝙蝠乃幸或不幸而生于如是村,悲哉悲哉!蝙蝠如竟代燕雀而處于村之堂屋,則誠為蝙蝠與村的最大不幸矣。
這恐怕想要不稱其為美文亦不可得了。
但除了大量的正經(jīng)文章外,周作人畢竟還寫了不少為消遣或調(diào)劑之用的“閑適文章”。香港潘耀明先生約我在這一部分文章中選若干篇,編一部《周作人美文選》。香港的村里當然是有鳥的,而且會唱歌的鳥恐怕還會越來越多,但是感受一點過去無鳥村中蝙蝠的悲哀,我覺得還是有些意思的。
我選的七十八篇文章,只占三千篇的百分之三不到,但寫作跨度同樣從光緒戊戌到“文化大革命”長達六十八年,與周作人的寫作生涯相始終。每篇都在題下注明了寫作年份,可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作者思想與風格的逐漸形成也能看得比較清楚。《山中雜信》以前的七篇屬于“少作”,用的是文言,但仍是大作家形成期的面影。其馀有的是歷來傳誦的名篇,有的則是普通讀者也許比較生疏,卻為我所深愛,覺得可以作為美文向大家推薦的。
因為是“美文選”,當然沒有包括周作人自己更加看重的正經(jīng)文章,但也有意識地加入了兩篇有點“搭界”的文字。一篇是一九二一年寫的《碰傷》,是他見到北洋政府殘殺學(xué)生的感想;一篇是一九五七年寫的《談毒草》,是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私下所作的一點補充。我想以此說明,周作人并不是只在寒齋喝苦茶的人。對于能讀他全部文章的人,當然用不著如此費辭;但對于只看看選本,尤其是又聽過些“文學(xué)批評”的讀者,恐怕也還有此必要。當然,這兩篇文章也還是美文,廣義的,正如周作人所有的文章一樣。
(一九九七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