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養(yǎng)心》劉梅花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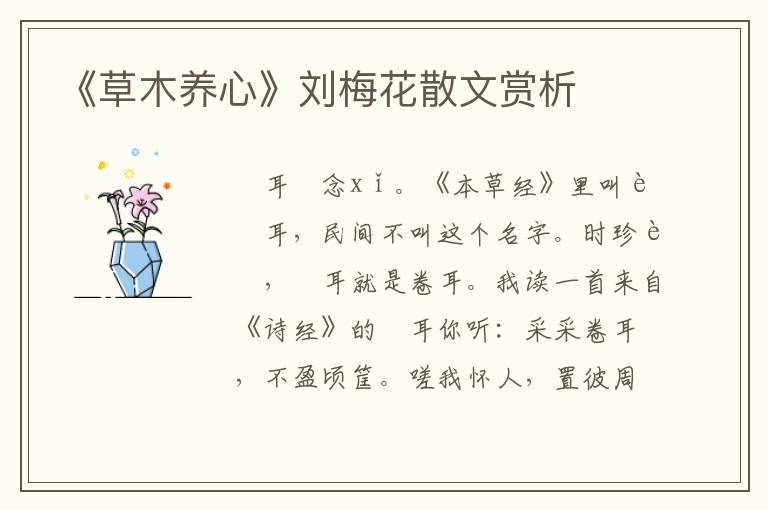
葈耳
葈念xǐ。《本草經(jīng)》里叫葈耳,民間不叫這個名字。時珍說,葈耳就是卷耳。我讀一首來自《詩經(jīng)》的葈耳你聽: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周南·卷耳》
這么風(fēng)雅的卷耳,來自天籟。讀一遍,心香。讀兩遍,空氣都清香撲面啊。不過,我還要告訴你的是,葈耳的俗名叫蒼耳,菊科。葈耳到了秋天,結(jié)了果實(shí),像棗核,全身伸著鉤刺,就是大名鼎鼎的草藥蒼耳子。
我喜歡得發(fā)瘋的草藥,古人可不一定喜歡。你看,王逸就說了,椒瑛兮湼污,葈耳兮充房。說葈耳是惡草。為什么呢?因?yàn)槿}耳有小毒,人吃了中毒后天旋地轉(zhuǎn)的,很不好。王逸是《楚辭》里的貴族,追求唯美,容不下一點(diǎn)不美的東西。不像我,布衣平民,看什么草都好得很呢。
其實(shí),葈耳是真的好,有點(diǎn)小毒算什么,哪一味草藥還不帶點(diǎn)兒脾氣呢。時珍說,卷耳,苓耳也。《集傳》曰,葈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你想想,多么優(yōu)雅的好草藥啊。
卷耳的叫法來自于周定王的《救荒本草》。古籍說,卷耳的嫩苗可食用,淘洗,炸熟,水浸泡,涼拌食,可救饑荒。這個炸熟,不是拿清油炸熟,而是用開水燙熟,我們河西也是這樣叫的,說把野菜炸一炸。你想,嫩葈耳葉是救饑荒的,饑荒年間哪兒有清油呢。不過,你要知道,葈耳是有小毒的,是在饑饉年成來充饑養(yǎng)命的,平日里沒事最好不要吃,沒那么好吃。人在饑寒的時候,求生的欲望驅(qū)使,體內(nèi)迸發(fā)出來奇異的免疫能力,可以過濾抵抗野草野菜的毒性,達(dá)到活命的目的。特殊情況下,人體吞噬細(xì)胞的攻擊力會加強(qiáng)。至于平日里,那些強(qiáng)烈的免疫力是不會有的,吃了要中毒。
古人講究養(yǎng)生,說道法自然,凡事都不要走偏岔極端,不能吃太離奇的東西。熊掌、猴腦、穿山甲之類的。吃進(jìn)去這些東西的時候,就把它們身體里的毒素也吃進(jìn)去,把它們心里的怨氣也吃進(jìn)去。沒有哪個生靈喜歡被人吃掉。不是在饑饉年代,人體的抵御力很弱,沒有辦法消化這些怨氣毒素,時間一長就會積聚致病。
所以,我以為,吃素是最好的。就算食肉的話,就吃被我們供養(yǎng)的動物,豬雞、牛羊、魚蝦。至于野生的生靈,都不要吃了,它們又不欠你的,祖輩就生長在山野里,招惹誰了。瀕危植物也口下留情,人來世上,不是為了吃光喝盡。
葈耳的葉子青白,瘦一點(diǎn)的像鼠耳朵,肥一點(diǎn)的淺心形,慢慢都長成闊楔形,邊緣有鋸齒,不甚鋒利,鈍鈍的。也開花,很細(xì)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小小的花朵上,棲息著一只長腿的蚊子,收攏了薄薄的羽翅,歪著脖子呆呆想心事。結(jié)果實(shí),蒼耳子全身的勾刺像無數(shù)的小爪子,跟著風(fēng)四處溜達(dá)。你走過去,就粘附在你的衣裳褲腳,連長發(fā)上都是。牛羊走過去也一樣,野兔躥過去也一樣。死纏爛打,就跟著大家走,散布他處。落在哪里,哪里扎根長葉,隨風(fēng)搖曳,快活得很,一點(diǎn)也不知道憂愁。
蒼耳子治療慢性鼻炎很好,可用蒼耳子三錢,辛夷花二錢,蔥白五錢。先將蒼耳子與辛夷加水,煎取濃汁,候冷。再將蔥白用冷開水洗清后搗汁沖入,用藥棉蘸藥汁塞入鼻中。治風(fēng)濕痹痛、治外感風(fēng)邪所致的頭痛都有療效,得遵醫(yī)囑,不可過量中毒。服用蒼耳子的時候,忌口,豬肉是絕對不能一起吃。
卑相
深濃的荒漠,落了霜,月光打不透,是卑相黑枯枯的影子,是沙丘灰淡的影子。一匹沙狐貍,拖著妖嬈的尾巴,爪子輕輕的,一點(diǎn)兒聲音也沒有,一滴墨水一樣,倏然滲進(jìn)卑相叢的黑影里,啥也看不見了。一會兒,探出腦袋來,在月光里張望,一縱身,倏然消失。卑相叢里,留下一架沙雞的骨架。
卑相可不管這些。沙狐貍也罷,沙雞也罷,都是世塵的過客。唯有它自己,才是千年的老妖,淡定恬靜,不狐媚也不妖冶。大漠的地脈氣從沙灘里鉆出來,朝著天彌漫而去,潮潮的。卑相在潮濕的地氣里悠閑梳頭發(fā),一根,兩根,無數(shù)根。也不挽個發(fā)髻,就那么披散著,拂掠著沙地。當(dāng)然,花還是要戴的,小小的黃花朵兒,攢成一簇,枝梢晃蕩。
光陰深處,雅士陶弘景低低說一句,卑相草,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卻青。
哦,多么不可思議的卑相草。
一只笨拙的大鳥落下來,咕咕叫了幾聲。它伸長脖子,啄了一口卑相的草莖。這清淡的草葉,氣微香,味澀,微微苦,微微麻。是的,一點(diǎn)兒也不好吃。算了罷。草莖上蜷縮的那條蟲子,很不高興,對大鳥吹胡子瞪眼。當(dāng)然,它可能沒有胡子。
卑相,并不認(rèn)識李時珍。它比時珍老多了,始載于《本經(jīng)》,列為中品。可是,時珍卻熟識它,說,卑相長者近尺,名殊不可解。俗名叫麻黃,大概是其根皮顏色黃赤、味道有點(diǎn)麻的緣故吧。自從漢代《傷寒論》中收載麻黃湯一方后,后世醫(yī)家都認(rèn)為麻黃是一味發(fā)汗解表、止咳平喘的要藥。
卑相,既然連醫(yī)圣都不知道意思,我就不要費(fèi)心思猜測了,一定是神仙取的名字,玄機(jī)重重。就我這點(diǎn)兒心思,比麻雀也多不了多少。
我只知道,卑相,發(fā)汗散寒,宣肺平喘,利水消腫。用于外感風(fēng)寒,惡寒發(fā)熱。能宣肺氣,開腠理,散風(fēng)寒。
對于卑相,這就夠了。知道的多了,反而不美。
木賊
好好的一味草,卻背了個賊名聲,這可怎生是好?又不曾偷過,也不曾得罪誰,一心一意,只想著過日子,可是好人卻擔(dān)了個賴名聲。這世上的事情,總是難以如意。好吧,就木賊吧,不然又能怎么樣呢,總不能四處尋找著和取名字的人打上一架吧。
木賊性子不急,就慢慢生長。腰身在風(fēng)里怯怯地抖動,不敢張揚(yáng),不敢恣意。就那么一寸一節(jié)地生長,也算是一步一個腳印兒,不敢太快。能省的都省省,日子刪繁就簡,節(jié)約得連葉子也沒有了,只剩下莖稈,扶搖直上。長一寸,遲疑一下,思慮著該不該再長,先打個結(jié)。木賊總是有點(diǎn)畏縮,不敢放開手腳生長。不像蘆葦們,長得恣意妄為,快要發(fā)瘋了。
時珍倒也不嫌棄它,說,此草有節(jié),面糙澀。治木骨者,用之磋擦則光凈,猶云木之賊也。陳藏器說,木賊苗如節(jié)節(jié)草,節(jié)節(jié)相接,一名接續(xù)草。魯班呢,說,木賊為銼草。
他們到底說什么意思呢?你也許不知道,我就知道。古人把吞食苗節(jié)的害蟲稱之為賊,說,食根曰蟊,食節(jié)曰賊。木賊又不吃苗,也不是蟲子,怎么還是賊?事情還是有緣由的。時珍說了,木賊長得很粗糙,可以打磨木頭的骨節(jié)。云木是最堅硬的木頭,木質(zhì)細(xì)密,堅韌,多疤節(jié),用木賊打磨過的木結(jié),光凈閃亮,好得很。除了木賊,堅硬的云木沒有辦法打磨光滑。一物降一物,木賊降服云木,天生的克星,就叫它木賊哩。魯班說的銼草,銼就是打磨的意思。
悄悄生長的木賊,喜歡叢生,苗長尺許。每一根只有一稈,無花亦無葉,它是參禪的草,把所有多余的身外之物都拋卻了,只留下自己。寸寸有節(jié),是凝思,也是總結(jié)。色青,很柔和,不凌亂。中空,留有竅,就是虛心唄。低調(diào)而謙順。草莖粗糙,披著絨狀的銳利之物,是密密的微細(xì)刺毛。打磨木頭,就是這些刺毛。老木工采收了木賊,把木賊草編成辮子,浸泡在水里。初做成的物件,表變都是毛糙滯澀之極。用木賊草辮,細(xì)細(xì)打磨。古人喜歡在物件上雕刻花紋,椅子上雕一朵纏枝蓮,卷幾上雕一對云頭紋。淺雕的花紋,取一兩莖木賊打磨。遇見木結(jié),則要用木賊辮使勁兒打磨才行。
一件書案,細(xì)細(xì)用木賊打磨過后,光潤如玉,柔順平滑,閃著綢子一樣柔和的光澤。也不上漆,就那樣原汁原味的,散發(fā)著自然的氣息。水的味道,森林的味道,陽光的味道,草木的味道,彌漫在屋子里,溫馨干凈。
入藥的木賊,棕色,輕薄。氣微細(xì),味甘淡,微澀,嚼之有沙粒感。古時的采藥人,在秋季收割了木賊,曬干,剪成段扎把留用。木賊能疏風(fēng)散熱,解肌,退翳。治目生云翳,迎風(fēng)流淚,腸風(fēng)下血,血痢,喉痛,癰腫等病癥。手上生了疣子,木賊煎水洗,也有很好的療效。你想,木頭的骨節(jié)子它能降服,手上的節(jié)子它照樣能收拾了。誰叫它是木賊呢。
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木賊草老了,辭了光陰,辭了青綠,只留著一身枯黃。可是,枯黃就是智慧。歲月濾去了輕浮,沉淀下精華。
老天讓每一味草下凡,都有安排,誰該干啥就干啥,不要相互扯皮推諉。木賊當(dāng)然也記著自己的使命。
芐
芐草長在白云深處,獨(dú)自參禪。殿開白晝風(fēng)來掃,門到黃昏云自封。芐不在世俗里,不要儒家入世哲學(xué)。它是從《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里飄繞而來的,只有出世哲學(xué)。芐,念糊。芐活得很明白,一點(diǎn)兒也不糊涂。《爾雅·釋草》里說,芐,地黃也。是的,芐草還有個俗名叫地黃。不要驚訝,古代的草都是很風(fēng)雅的。叫俗名,它理都不理。雅士羅愿說,芐,以下沉者為貴,故字從下。
是這樣的,這味藥,草叫芐,根叫地黃。知道了吧?
芐一輩子都很低調(diào),絕無張揚(yáng)。嫩苗出土,塌著地皮生長,葉子很像山白菜而毛澀,葉面深青色,葉脈稍微有點(diǎn)紫氣兒。再長大一點(diǎn),葉子變厚,有點(diǎn)兒近似小芥葉,不叉丫。再長呢,葉子中間攛起來莖,莖上細(xì)細(xì)的白絨毛。五六月,莖梢開小筒子花,紅的,黃的,色濃深。長累了,就結(jié)子實(shí),如小麥粒一樣的。藥用呢,用得是根。因其地下塊根為黃白色,就叫地黃。根長四五寸,瘦的纖細(xì)如美人的手指,肥的像紡錘。皮赤黃色。
剛剛挖出來的根,叫鮮地黃。還有干地黃、熟地黃呢。
《本草經(jīng)》里說,取鮮地黃一百斤,挑揀肥碩的六十斤,抖掉沙土,暴曬,曬到根皮微皺。挑出來的瘦地黃呢,投到清水里淘洗干凈。放在木臼中,搗碎,絞汁,摻入白酒。取汁,拌入曬蔫的肥地黃里,日中曬干。天陰,用炭火焙干。不管是曬干、陰干、火干的,都叫干地黃。
干地黃性甘,寒,無毒。主治男子五勞七傷,女子傷中胞漏下血,通血脈,益氣力。
至于熟地黃呢,炮制的方法也是很繁瑣的。大木盆里盛滿清水,投入鮮地黃,木棍攪和,沉水肥大者揀取出來,瘦的不要。一壇子好酒,加了砂仁末,攪拌均勻,灌入放了肥大地黃的柳木甄里,擱在瓦鍋里蒸透,晾干。再拌入砂仁酒,蒸晾。如此,九蒸九曬,乃止。所以,熟地也叫九地。
唉唉,我這么好的手藝,也沒有藥廠請我去炮制中藥,真是不能想,一想就憂傷得不行啊。英雄沒有個用武之地么。
九地,填骨髓,長肌肉,生精血,補(bǔ)五臟內(nèi)傷不足,通血脈,補(bǔ)血?dú)猓棠I水。
時珍說,男子多陰虛,用九地。女子多血熱,用生地黃。
蓫薚
蓫薚,念逐湯。
山野里做草時,無緣見。做了藥材,才得一見真顏。藥肆的柜臺上,一張枯草做成的紙,一撮蓫薚,在陽光里淡淡地散發(fā)著一脈草藥香氣兒。灰棕色,隱約滲了絲絲老綠,仿佛使勁兒挼揉了似的,皺縮著,枯萎著,也淡定著。問,這草,可是商陸?答曰,是的,就是章柳。低聲感嘆,這蓫薚,枯了都這樣清美。
做草的時候,女兒一般,豆蔻好年華,叫蓫薚。你看,《詩經(jīng)》里說: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fù)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婚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fù)。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祗以異。——《小雅·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這蓫,就是蓫薚了,俗名叫羊蹄子菜,古人也是吃它的。只是啊,讀來,心里愁緒彌漫。獨(dú)自行走郊野,樗樹枝葉婆娑。因?yàn)榛橐鲫P(guān)系,才來同你生活。你不好好待我,只好我回鄉(xiāng)國。獨(dú)自行走郊野,采摘羊蹄野菜。因?yàn)榛橐鲫P(guān)系,日夜與你同在。你不好好待我,回鄉(xiāng)我不再來。獨(dú)自行走郊野,采摘葍草細(xì)莖。不念結(jié)發(fā)妻子,卻把新歡找尋。誠非因?yàn)樗唬∈悄阋炎冃摹?/p>
空曠岑寂的原野上,被遺棄的女子獨(dú)自行走,碎碎念。布衣羅裙,滿面淚痕。路邊的樗樹,蓫草,還有茂密的葍草,都不能愈合心里的傷痛。如此孤獨(dú)凄涼意境,真的不能多想,一想,眼淚就下來了。你這蓫薚草,醫(yī)天醫(yī)地,卻不能醫(yī)心啊。
蓫薚老了,掘出根,入藥,叫商陸。草為蓫薚,也叫章柳。根為商陸,也叫當(dāng)陸。時珍說,此草能逐蕩水氣,枝葉柔美,所以叫蓫薚。路邊多生,掘根叫商陸。至于叫當(dāng)陸,因?yàn)椴萑~枝枝相值、葉葉相當(dāng),故也叫當(dāng)陸。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蓫薚老熟,也就枯萎了,但根依然活著,來年,萌發(fā)一枚新芽,輕輕說,我是去年的蓫薚呀。一味草,懂得收斂自己的脾氣,沉默,卻也悄悄地繁榮。
商陸入藥,味辛,平,有毒呢。《本經(jīng)》說,主水腫疝瘕痹,熨除癰腫,殺鬼精物。《別錄》記載,能療胸中邪氣,水腫痿痹,疏五臟,散水氣。古代名醫(yī)甄權(quán)說,能瀉十種水病。喉痹不通,薄切醋炒,涂抹喉外,良。
弘景先生說,方家不甚用,唯有療水腫挺好。道家用得多,據(jù)說能見鬼神。道家用蓫薚的花朵和籽實(shí),叫神藥。至于醫(yī)家,只用根。
總覺得,每一味草藥,都有自己的活人之道。順其自然,守著本分,淡泊名利。一味草,絕對不去浮躁狂妄,不去給自己的同類使個絆子挖個坑。草們,淡淡的,在大自然里和諧相處,真是有一種天人合一大境界。如果參禪,就在一味草藥里參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