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松《簡寫寒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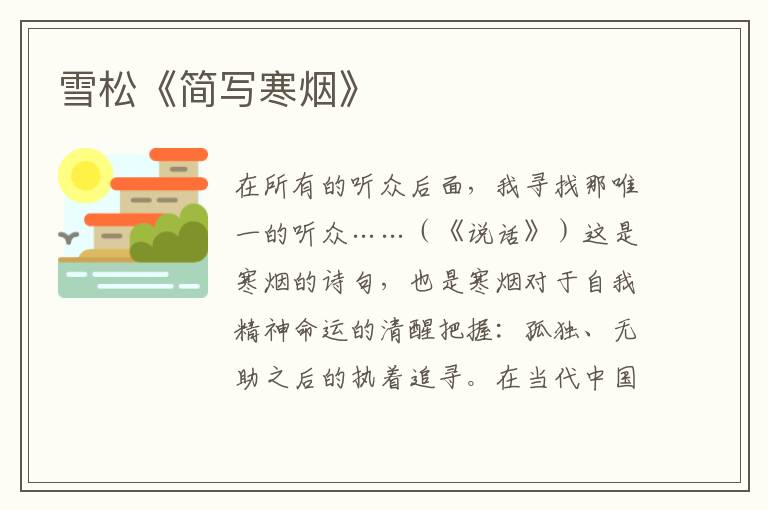
在所有的聽眾后面,我尋找
那唯一的聽眾
……
(《說話》)
這是寒煙的詩句,也是寒煙對于自我精神命運的清醒把握:孤獨、無助之后的執著追尋。在當代中國的詩歌語境中,寒煙的寫作是一個異數,她所發出的聲音,像攜帶著鉆頭的鐘聲——帶著審問和自我反省向人的靈魂深處鉆探。她認為寫詩是一場從自我開始的靈魂清算,一種自我救贖的方式。因此,她詩歌中極致的部分,不是靠修辭的推動,而是靠生命原有的氣息,靠命運獨特的際遇,靠那唯一的、不可取代也無人能取代的“命定性”來艱難養育,從這個意義上說,寒煙是一位這個時代少有的“元詩人”。她整個的詩歌寫作,是以行動的意志,而非以優雅的文化意義上的“作品”來與當下時代構成背離與批判的緊張關系。
一個時刻感受到靈魂困厄和疼痛的人,一個肉體與精神相互砥礪的人——寒煙在一個普遍缺血的時代保持對血性的頌揚,因為她要“以血的名義/在世間辨認高貴……”(《阿赫瑪托娃》)。在以解構與修辭支撐的中國當代詩歌寫作里,寒煙奇跡般地保持了與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學精神的“骨頭的相認”(《帕斯捷爾納克》),這也注定了寒煙要以生命來喂養詩歌,要以苦難作為詩歌的肥料,要以生命的純潔來觸摸、探尋和保持靈魂的高貴——于是,我們看見寒煙生存的身影:“從拒絕開始,生活這樣難以下咽……”(《茨維塔耶娃》)。在城市的邊緣,在人群的底層,在物質的貧困里,在人生情感的困頓中,她不向世俗低頭,不為物質出賣靈魂,不以修辭緩和內心的痛苦——她始終以批判的姿態指向時代、以自我的追問與反省去修補人性,她和著血淚咽下難以下咽的命運。
寒煙所葆有的詩歌觀念,再一次顯示出她不為環境所左右的執拗。她認為,不管詩歌的潮流如何變化,詩歌的基本價值尺度是不會變動的。詩歌必須忠于靈魂、審視靈魂,真正的詩寫要對時代和自我人性做無情的追究,詩人是“為世界喊疼的人”。而寒煙依靠自己對痛苦的承擔,在詩中緩和著時代的疼痛。她這種對自己的堅守,使她的寫作與整個詩壇處在一種緊張的對峙之中。
寒煙絕對的詩歌觀念和立場,我曾切身領教過。記得當年在一次頒獎后詩友聚會的交談中,我那個時期的部分作品的寫作方式,遭到了她毫不留情的批評——她認為我的那一部分作品跟風、與靈魂無關、把心交給了修辭,她不能容忍這樣的寫作發生在自己的朋友身上。她爽快耿直、無遮無攔、直來直去的發言態度,讓我看見這個時代少有的真誠、透明,和因真誠、透明而生的可愛。
自那次頒獎會以后,我與寒煙再未謀面。2010年春天,她以電子郵件的方式給我發來她的多篇詩文近作——我看到的寒煙仍在堅守著她的精神高地,仍以受苦的方式試圖為中國當代詩歌獲取一個可靠的標準。只不過她懷疑、追問、批判的方向,更加自覺、深入地指向了自身的人性、內心和靈魂,更加強調獨立承擔的悲劇精神。在讀完她的近作后,我寫下了如下的筆記,至今還存在電腦里:“……在當下的詩歌環境和精神環境里讀寒煙的作品,我感到了其特殊的分量和意義。她是當代不多見的用自己的生命實踐寫作的詩人,而且,她已經擁有了自己自足的精神背景,這是了不起的事情,這也是一個詩人開始成熟的標志……”
以香茶、紅酒的狀態和方式進入寒煙的詩歌,在我來說是不適合的。在人性殘破、靈魂無著、智力與修辭充斥的時代精神氛圍中,當你變得優美、雅致、幸福閃耀,或者身心輕飄飄、油腔滑調的時候,讀寒煙的詩不啻為一種矯正,一種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