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紹俊《《淮水謠》,鄉土文學的新開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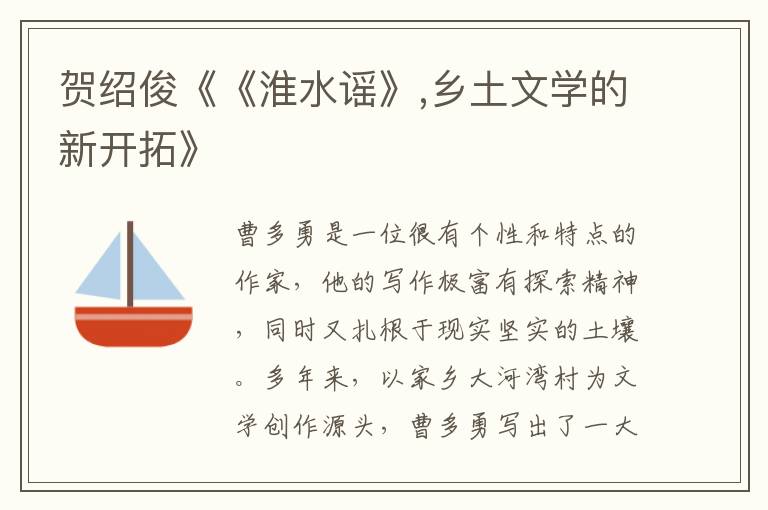
曹多勇是一位很有個性和特點的作家,他的寫作極富有探索精神,同時又扎根于現實堅實的土壤。多年來,以家鄉大河灣村為文學創作源頭,曹多勇寫出了一大批覆蓋長中短篇體制的優秀小說作品。可以說曹多勇是新時期涌現出來的鄉土文學的優秀代表。他生長在淮河流過的地方,他說過,淮河是他的母親河。曹多勇熱愛家鄉、熱愛土地、熱愛淮河,這種愛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得很突出。他在訪談中說,自己的作品有兩類:一類寫“歷史”,一類寫“當下”。寫歷史基本就是童年記憶,而寫“當下”的作品同樣也能看出記憶對他的影響。他的這些記憶其實都是關于淮河的記憶。他是在夯實鄉土記憶的基礎上,來寫當下的鄉土和生活,有厚厚的記憶底色。《淮水謠》就突出體現了曹多勇的這個特點。正如他在小說的后記里寫的那樣,這也是一本關于記憶的書。讓人感到驚喜的是,作為鄉土文學的《淮水謠》,既有著他小說固有的精神與特色,同時,又有著新的可貴的創新與探索,可以說是鄉土文學在新時期的富有開拓意義和價值的優秀文本。
首先,《淮水謠》的結構極具藝術創新意味。剛接觸《淮水謠》的讀者,一開始可能會以為其結構比較老套,因為它是以小說中的十個人物為章節來結構小說的。猛一看,一個個人物像素描、特寫、拼盤一樣拼成了鄉村圖景。其實細心讀進去,就發現不是這樣的,這是一種凝結了作者深刻想法的結構。當然,這個結構并不是現代結構,從形態上說《淮水謠》仍是傳統現實主義的小說,然而,盡管傳統,卻新意十足。曹多勇的《淮水謠》結構表面上看是一個形式問題,往深里追究,它與內容密切相關。如果只是為結構而結構,那它可能是純粹的形式問題。但假如小說結構是作家在觀察和剖析寫作對象的過程中生發出的,這就不僅僅是個形式問題了。《淮水謠》的結構就是在觀察和剖析寫作對象中生發出的結構,是作家對小說總體精神與思想,經過深入思考和高度把握的結果,它反映著作家對小說中人物、命運、環境,甚至血脈與精神文化傳統的精深考察與透徹領會。《淮水謠》寫的是淮河邊上的一個鄉村家庭,先從第一輩的父母寫起,再寫大兒子、二兒子、三兒子、小女兒,然后輻射到兒媳、女婿等。我把它叫作從倫理上進行結構的小說。什么意思呢?就是這個結構是根系形態的,主人公韓立海、吳水月夫婦是根,從他們那兒發散開來。表面看來,是十個人物各自登場,各奔前程。而在更深層次,卻是由近而遠,由表及里,是一脈相承的,是血氣相通的。這樣的結構形式,形散而神不散,它使得小說中的人物在變化無窮的人生舞臺上,在各自命運的展開里,始終連接著韓立海、吳水月這根精神主脈,他們的命運遭際與生存軌跡,若隱若現地發散著來自鄉土深處的人文氣場、精神氤氳與風俗神韻。在曹多勇的《淮水謠》里,小說的結構就是這樣與小說的內在肌理有著骨肉相連的關系,這樣的獨特結構就像是小說的骨架與筋脈,將小說的肉與血支撐起來,生動起來,豐滿起來。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淮水謠》的主題內涵就包含了很多新的東西,是有著新的開拓的。但是他的這種“新”又藏得很深,有時候粗讀可能沒有發現。這里,只著重說一點,《淮水謠》其實寫了一個普遍的觀點——在鄉村的人都想離開鄉村。小說主要情節是寫韓立海四個兒女包括韓立海自己其實都想離開鄉村。小說每一章都寫他們是怎么離開鄉村的。小說最開始韓立海也是想離開鄉村的,他到煤礦去,他差點離開了,因為有了吳水月以及其他原因,他留下來了。其實,但凡對農村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農村人都想到城鎮去,有些農村的孩子在企業工作很辛苦,雖然很辛苦,但是他們也不愿意回到鄉村。可以說《淮水謠》真實地寫了鄉村人的這種普遍的愿望:向往更好的生活,有著強烈的離鄉愿望。《淮水謠》的深刻與新穎在于,他在寫從鄉村出走,也就是在寫一個逃離的主題的同時,還有一個始終表現的主題:戀鄉。這就使得《淮水謠》籠罩著一股濃濃的鄉愁。這種將逃離鄉村和鄉愁、鄉戀放在一起的寫法,就構成了一種獨特的饒有意味的互文關系。也就是說,在《淮水謠》里,離鄉情結與戀鄉情結是鄉愁的一體兩面。而當這二者會合到一起時,鄉愁主題不僅出奇地完美,更具有著新時代所獨具的復雜況味,有著一種當代鄉村人,甚至是所有當代人精神深處扯不清剪不斷的糾結與困窘。正是在這一點上,曹多勇的思索有了新的開拓,他使得鄉土小說在精神包蘊上大大地豐厚了,具有了傳統鄉土文學所不具備的豐富性、新穎性與深刻性。似乎我們在以前的鄉村小說中,沒看到這樣一種表現方式。當然,有的作家也會寫到農村人想辦法離開鄉村,他們要逃避鄉村的苦難,但這類小說多半是從另外一種角度去反映現代化進程的,是寫城市文明對鄉村文明的擠壓,寫鄉村文明的崩潰,這種寫作思路蘊含著這樣一種觀念——城市文明肯定比鄉村文明要先進,城市文明終究要取代鄉村文明,現代化的進程必然走到這一步。而這個思路是以一種高亢的聲調來遮蓋逃離鄉土那挽歌式的懷鄉與離愁,這種歷史目的論支配下的鄉土敘事,其實是無形中賦予了逃離鄉村甚至是拋棄鄉村的某種歷史合法性。而在曹多勇的《淮水謠》,則有著更為深邃的思考和更為前瞻性與歷史深遠性的探究。《淮水謠》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切入鄉村歷史與現實的新思路:人與土地的關系不是簡單的追求更好生活的問題,脫離土地逃往城市,也不是中國農村的根本出路,更不是農民的理想歸宿。一句話,逃離與鄉愁絕不單單是先進與落后的問題。今天人們為什么還留戀鄉土,向往鄉村?為什么會有濃濃的土地情結?這是因為土地造就了一種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方式背后的文化定勢,這與先進、落后沒有關系。單純地局限在先進和落后二元對立模式上,有時候會走極端;從先進與落后角度看問題,我們就會走到這樣一個死胡同。《淮水謠》不回避這一點。小說告訴人們,其實鄉村的人知道什么生活更美好、更舒服。所以,《淮水謠》絕對不是寫兩代人的差異,也不是寫先進與落后的問題。絕不是說韓立海和吳水月留戀鄉土,韓立海的后輩才想去城市,不是要構成兩代人之間的對立關系。想離開鄉村是人之共性,小說在寫出這種人之共性的同時,還寫出了對鄉土的愛,對鄉土的懷念,對鄉土的堅守。這里面其實是有更深層的原因。《淮水謠》正是這樣寫出了土地造就的一種文化、人格與人性,當這種文化不僅鑄就了你的生活方式,更鑄就了真實的獨特的個體的人。這樣的人就會留戀這種生活方式,留戀這種生活方式所賴以存在的土地與鄉村,留戀其背后更為深邃、復雜與奇妙莫名的感受、記憶、情緒、身份認同、價值認同與生存體驗認同。所以吳水月死了都要葬在大河灣村,而韓立海那么窮都要養豬,使勁把孩子送往城市,但是他還留戀土地,留戀土地是因為他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他的文化性格。所以當孩子說把吳水月的墳遷到公墓里時,韓立海不同意,因為只有吳水月葬在這里,全家一年才能聚在一起。小說在這個層面上,又將對鄉土的懷念與堅守與“家”聯系起來,這就深深地觸及中國人精神深處的“根”。差不多百年前,民國的那些鄉土建設派就意識到:“蓋中國民族,立國于亞洲大陸,自有歷史以來,已四千余年,資以維持發展,歷久不衰朽,幾無一不家族是賴。”如此,我們說《淮水謠》里的一個個人物,最后其實塑造的是一個完整的形象,這個完整的形象就是“家”,它表達了曹多勇對“家”的理解,也表達了他對“家”的憂思。家,這個中國社會、鄉土文化中最基本的元素,這個中華民族精神與魂靈的居所,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其凝聚力在銷蝕,有著風雨飄搖的落寞感和荒涼感。而沒有家或者遠離家園的人是多么凄惶、迷惘與漂浮!《淮水謠》背后傳達的就是這樣一種憂思。這是一種源自血脈與骨髓深處的憂思,是發自“根”的期盼與召喚,是鄉土中國數千年情緒記憶與精神積淀的蘇醒、感應與喟嘆。所以,我們說《淮水謠》在鄉土敘事上有創新,不僅僅表現在形式上,也表現在思想主題上。
《淮水謠》作為鄉土文學的富有開拓性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扎實而厚重,是源自曹多勇對淮河的深厚感情,更是源自他多年來潛心鄉土文學的創作。幾十年來,曹多勇寫淮河的小說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很可觀。可以這樣說,曹多勇的小說創作已經形成了自身的獨有風格與特質。我以為曹多勇的鄉土文學創作,堪稱安徽鄉土敘事的標示性文本。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以曹多勇為代表的安徽小說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鄉土文學流派——皖派鄉土文學?講到鄉土敘事,首先會想到陜西,陜西的確是很強大的,但安徽的鄉土文學有自己鮮明的特點與獨特的美學價值。陜西是在黃土高原上形成的鄉土敘事,用一個“厚”字形容,就像厚厚的土,一吹就會揚起塵土。這種“厚”可能還和陜西鄉土敘事中生存的艱難,生命主體常常是匍匐在黃土地上有關。但我讀曹多勇的小說,我就要用“綿”來概括,綿軟的綿,它有一種水的滋潤,卻又有水的韌性與執著。以曹多勇為代表的安徽鄉土敘事里的生存也有艱難,但人與土地的關系是友好的。生命主體在安徽大地上往往是堅韌地頑強而樂觀地抗爭著的,是始終滿懷希望的,是直立在土地上的。像《淮水謠》,顯然也是一種現實主義傳統。討論現實主義傳統時,我們會從各個方面去討論,但《淮水謠》的獨特性就在于它是用積極、樂觀的姿態去面對鄉村、面對敘事對象。這是中國現實主義傳統很重要的一個特點。中國現實主義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詩經》的風雅頌。但后來我們談現實主義傳統,卻只談《詩經》中的風,好像風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傳統,其實應該把三者看作統一體。風,是土風歌謠,來自民間,曹多勇的《淮水謠》就是謠,就是來自民間真實而蒼涼的歌唱。同時,曹多勇的小說又是扎根于淮河大地的,寫出了淮河人家真實的生存,寫出了淮河養育的人們精神上的堅韌與倔強,本分與善良,深情與質樸……正是從曹多勇的小說里,人們開始真正接觸和認識到,為一條偉大河流——淮河養育的人們是怎樣在歷史與現實中生存的,他們的生存又體現出怎樣的精神與氣質、性格與情懷、精彩與苦難、沉淪與夢想……還是著名評論家劉颋說得好,她說“曹多勇以他的小說繪制了一幅淮河文學基因圖譜”。可以說,曹多勇的《淮水謠》是鄉土文學的新開拓,也是為安徽的鄉土文學做了開拓性與奠基性的工作。而這樣的開拓性與奠基性的文學書寫,理應受到更多的關注與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