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嶼山上賢風吹》董聯軍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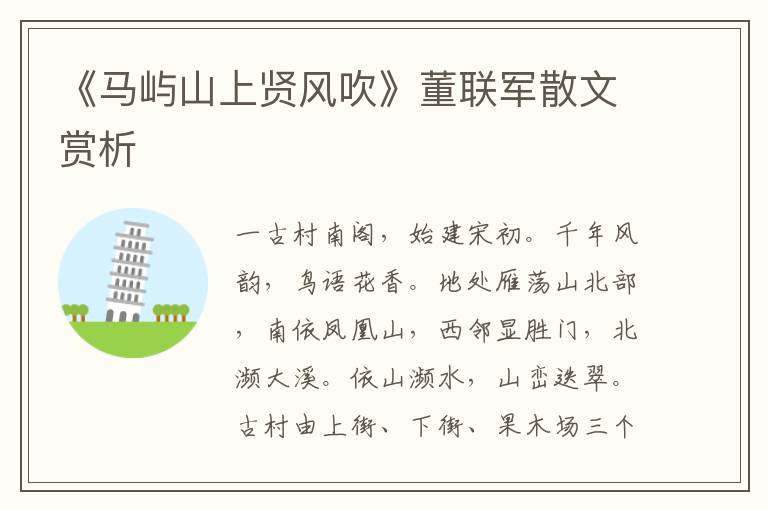
一
古村南閣,始建宋初。千年風韻,鳥語花香。地處雁蕩山北部,南依鳳凰山,西鄰顯勝門,北瀕大溪。依山瀕水,山巒迭翠。古村由上街、下街、果木場三個村組成,為章氏聚居之地,也是明代直臣章綸故里,2010年南閣被授予“中國歷史文化名村”。村有國家重點文物——“南閣牌樓群”,系明代古建筑,現存五座,規模宏大。
馬嶼山位于古村南閣,山小不高,孤峰屹立。當地俗稱嶼山。山上建有章綸弘塔,萬綠一素。灰磚素瓦,莊嚴肅穆,格外精氣神。
山不在高,有塔則靈。弘塔讓嶼山人文和靈氣起來。鄉人游客,見塔,俱知:南閣到了。塔為紀念先賢章綸所造,是古村自然與人文景觀互為輝映的地標建筑,也是一座地杰人靈的風水寶塔。
老家在嶼山東首,抬頭見塔,感覺機會多多。每回老家遠觀之,卻無近瞻。袁枚《黃生借書說》有言:“書非借不能讀也”。蓋萬物莫不如此。熟視無睹,熟了就易疏忽。
若非樂清市要出《古村、古塔、古橋、古井、古廊亭、古城堡》一套叢書,因寫作之需,近瞻弘塔,或許一拖再拖。
從嶼山東西兩側,皆可登頂。其西側巨巖當壁,巖多樹少,路稍陡,與村莊相鄰方便,村民多由此入。東側建有文化廣場,樹多巖少,路平坦,松樹修竹,花木綠蔭,游客皆由此上。
丙申炎夏,攜侄震宇,從東側上。山高百米,峰回路轉,出綠蔭道,豁然開朗。清風徐來,心曠神怡。山下美景一覽無遺,仿佛一幅嶄新水彩。青山連綿,白云飄蕩,房屋井然,田野山色,渾然一體,綠得生鮮。墨綠、濃綠、淺綠、嫩綠、草綠、黛綠……而或間隔,層次分明,仿佛綠色世界。久居城里,漸失本真。美景道不得,只緣此山中。此乃花木之鄉,水土養人。
前行數十步,野芳幽香,清流石隙而出,下筑水池。臨池建有飛檐涼亭,名為“勝覽亭”。亭聯:“嘯傲煙霞猶見當年雅集,扶踈花木何妨此日清游。”紫氣東來,鳥語花香,靜而生慧。閑坐涼亭,浮想聯翩。遙想章綸當年,告老還鄉,登嶼山,詠詩賦。煙霞閑骨格,恬淡清人生。無論高官達貴,抑或凡夫俗子,故鄉的云最能撫平滄桑。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64歲高齡的章綸第三次上奏乞求致仕獲準,終歸故里。章綸詩云:“恬然在安宅,俯仰可徜徉。消憂有琴書,協意如宮商。”卸錦歸田的章綸自稱“廣漠野人”,優游林泉,以詩書自娛。
二
沿山道盤亙而上,老家與南閣,盡收眼底。南北兩山,猶鳳凰展翅。兩山間狹長平坦,如鳳凰脊背,自西向東密密麻麻布滿了民居。村舍不斷向東西擴展延伸,東邊已突破南閣堡迎輝門,與老家相連。我無法肯定何處是老家。
震宇眼明手快指點:“爺爺家在那里,幾棵高大枝繁葉茂的松柏樹處。”對呀,我怎么能把標志性特征給忘了。
樹為全村之最,上百年,是震宇的太爺爺親手植下。老屋為百年老宅,廊檐大柱,道地很大。我的童年歡樂全在老宅道地里。看舞獅,玩彈珠,摜紙板,打雞毛球,有時球打上屋檐,就拿長竹竿挑下來,還把瓦片挑翻;晚上納涼,數星星,聽說書……歲月如歌,轉眼間震宇也做爸爸了。
對面馬家嶺,綠得認不出樣子來。蜿蜒而上的石階,全被綠蔭遮蓋。煤氣灶沒有興起時,山上光禿禿的,砍柴是農民謀取生活的必由之路。
馬家嶺是一條南閣通往雁蕩的民間商道。南閣的板栗、肖梨、花生等山貨,白溪的蝦皮、咸魚等海貨,都經馬家嶺到對方交易。
春游雁蕩,也走馬家嶺。山嶺石頭磨得光亮,赤腳走起也舒服。每到嶺頭看山下梨花盛開,花團錦繡,一片粉海,黛色村莊,炊煙裊裊升起,如入仙境。如今炊煙不再,梨花不現(梨樹砍了種花卉苗木)。
穿竹林,至山頂,欣見休閑廣場在茂林修竹、綠樹環抱中,靜靜敞開。天人合一,寵辱皆忘。廣場呈長方形,東西布局,約足球場大。南側一排石凳。北側一座石廊,雅致優美,設有美人靠。廊聯曰:“游目騁懷四面風光舒快意,捫心揣度一生善惡發深思”。賞景,修身,養性。
風輕云淡,萬籟俱寂。若練太極,別有洞天。文人墨客,揮毫潑墨,彈琴吟詩,不亦樂哉。邀友賞月,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此處觀塔,修竹翠柏,猶顯玉樹臨風。休閑廣場之妙,一是在生理上讓登山人稍作休養,氣定神閑;二是在心理上有美學之功,既有屏風之美,也具旗袍之韻。不讓弘塔一覽無余,猶抱琵琶,脈脈含羞,呼之欲出。
旁有曲徑通弘塔,修竹隨風,搖曳多姿,嫵媚十分。出林蔭道,見弘塔。塔素雅靈氣,渾身散發中華傳統文化的精氣神。塔高二十余米,七層八面,磚混建筑,飛檐翹角,古樸壯美,大氣精致。塔內通透,每層開有圓拱觀景窗,設有樓梯,盤旋而上,可極目遠眺,飽覽風光。
弘塔刻有門聯:“九曲溪千年誦名仕,百崗頂萬代蘊英才”。九曲溪為古村靈魂,百崗頂為古村根基。此塔為百姓籌款而造。弘塔助建碑記載:塔建于甲申年(即公元2004年),由南閣三村雙委、老年協會共同湊建。捐助者來自四面八方,有鄉鎮、村委、風景區及個人,金額幾千到數萬元。可謂眾人拾柴火焰高,尊賢弘德情不老。
登塔眺望,景色盡收。九曲溪碧波蕩漾,石柱擎天巍然屹立。章氏祖墓和章綸墓皆在石柱山下,村人謂石柱峰為風水石,心存敬畏。
石柱與弘塔,東西呼應,自然人文,相得益彰。如果說神圣 “石柱”,象征章綸“性亢直言,不能偕俗”的性格;那么文雅“弘塔” ,則彰顯章綸“德才兼備,為國為民”的品行。
古時南閣有“八景”,成于宋代,明有記錄。《溫州府志》載:“恭毅公里中八景:石柱擎天、西湖晚釣、仙巖落月、北薩春耕、桃林牧笛、柳港漁燈、馬嶼書堂、雁湖古剎。”現八景之中,除了“石柱擎天”、“西湖晚釣”、“仙巖落月”, 其余五景不復存在。
而“西湖晚釣”位于九曲溪中游,筑堤成湖,夕陽映照,碧波蕩漾。現為天然泳池、水上樂園,是村人納涼消暑最佳處。“仙巖落月”為自然景觀,夕陽西下,月上中天,群山連綿,層巒疊嶂,溪山云煙,朦朧夜色,猶入仙景。
三
從宋至明清,溫州科舉入仕者數百位,不泛有位高權重者。600多年過去了,當地百姓紀念章綸愛戴有加。他們敬仰章綸的忠節品行,還根據章綸事跡編成《拜天順》戲劇,數百年間久演不衰。近由湯琴編劇的越劇《章綸》在各地上演,并在中國第三屆越劇節上獲獎。
《左傳》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賢者若有“一立”或“半立”,后人皆會紀念。
與章綸同朝為官的于謙(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也是百姓愛戴的賢臣。章綸以“德言”聞名,于謙以“功德”著稱。兩者皆“忠心義烈,流芳百世”。然而一場明王朝的“土木堡之變”,讓他們各自人生,起伏跌宕,榮辱興潛。
明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聽信專權太監王振,御駕親征蒙古,被瓦剌俘虜,史稱“土木堡之變”。為抵御外侵,兵部侍郎于謙等擁立皇帝其弟朱祁鈺為帝,改元景泰。
于謙親自督戰,固守北京,破瓦剌之軍,力保大明王朝。次年瓦剌釋放英宗,被景泰帝軟禁于南宮,一鎖七年。期間于謙憂國忘身,自奉儉約,輔助景泰帝。清除閹黨,穩定局面,百姓安居樂業,吏治為之一新。
景泰三年,朱祁鈺廢除了明英宗之子朱見深,立自己兒子朱見濟為太子。然天有不測風云,朱見濟于景泰四年不幸夭折,東宮太子處于空位。景泰五年,章綸上《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中“復儲位”,定天下之大本。主張內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后宮不可盛聲色,并要求復汪后于中宮,還沂王朱見深之儲位(東宮太子),朔望率群臣朝見從瓦剌贖回之英宗。
“復儲位”是犯了景泰帝心中大忌,朱祁鈺好不容易撿到“帝位”,當然想讓自己后人繼承九五之尊萬萬年。章綸的“復儲位”簡直虎口拔牙,“不識時務”。觸怒景泰帝,入大獄,受盡毒打,九死一生。
同樣事關大明皇家的禮儀之爭。溫州的張璁“錦上添花”,他上諫支持明世宗朱厚熜,結果龍顏大悅,三度任首輔。
景泰八年(1457年),石亨等人發動奪門之變,英宗復位稱帝,改元天順。章綸與于謙的命運發生改變。
英宗復位,下旨釋放章綸,擢禮部右侍郎。但因生性亢直,不為當事者所喜,任侍郎二十年未升遷。十二年辭官回鄉,優游林泉,以詩書自娛。享年七十一歲。追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恭毅。
而于謙被明英宗以謀逆之名,處死。景泰朝結束。英宗聽信讒言,殺害救其于危難之際的大功臣于謙。這也成為他繼“土木堡之變”后的又一大歷史污點。而明代宗朱祁鈺,也成為了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唯一沒能葬入明十三陵的大明皇帝。
一部大明王朝的春秋,因宦官專權而改寫歷史。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這些權傾朝野的大宦官,結黨營私,貪污受賄,巧取豪奪,專橫跋扈,禍國殃民,使明王朝一步步走向末路。
假如九泉之下的章綸與于謙相逢,如何老淚縱橫話滄桑?一位為國殺敵保江山,竟以謀逆之名處死;一位為國忠諫佑黎民,竟受盡毒打九死一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愛國愛民,在封建皇權眼里,唯有“利益”兩字。“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好在歷史不是由權力書寫的。
紅塵滾滾,改朝換代。國君和社稷,豈能一成不變。唯有老百姓不可更換,是國之根本,最為重要。故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顯得那樣高大上,不愧為古代偉大的思想家。
觀當今,倘若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也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殊路同歸。愛民就是最大的愛國。愛國的核心就是愛民。
四
古往今來,真正英雄俊杰皆是“不識時務者”。甘受宮刑的司馬遷,堅信日心說的哥白尼,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林則徐,要留清白在人間的文天祥,冒死忠諫的章綸等。
世間的叛徒、漢奸、賣國賊、貪官污吏,無不以“識時務”為自詡的典型代表。
章綸自稱“戇夫”,一生鐵骨錚錚,憂國憂民。就是這股“不識時務”的戇勁與忠節,名垂青史。他不怕得罪權貴,有人勸其如此不好,他回:“在我者有義命,在彼者吾不知也。”
景泰四年,太監興安請皇帝到新建成的隆福寺去,章綸即上疏反對。明永樂年間開始,太監逐漸成為權力特殊階層,很多大臣為升官或保平安,走巴結太監之路。章綸很清楚,但他不怕得罪皇帝身邊紅人太監興安,正氣凜然,毅然上疏阻止。
他秉性耿直,還厭惡附炎趨勢之徒。對于自以為在英宗復辟事件中立了大功的權臣石亨、楊善等人的跋扈氣焰,不屑一顧。竟還當著石亨的面為于謙喊冤,因而遭到石亨、楊善的極力詆毀,于天順二年被調往南京禮部。
天順初年,山東自然災害嚴重,民不聊生,主政山東的官員上疏告荒請減租賦,戶部不僅不同意,連告荒的奏疏也被戶部尚書楊善扣壓不報。章綸得悉,立即上奏皇帝,終使皇帝同意減去山東當年一半租賦。因為“忠”和“節”,他不怕“得罪”人。
周恩來說得好:“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是最老實的人,因為只有老實人才能經得起事實和歷史的考驗。”譬如權臣石亨,官至太子太師,因發動奪門之變,擁立復辟,權傾朝野,但驕橫跋扈,培植黨羽,最后瘐死獄中。
現實生活中,利己主義窮盡百出。無論是陰陽兩面的貪官也好,還是阿諛奉承的文人、專家也罷,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與否,講真話的人群的多寡,是很好的風向標。
奧運會傅園慧的“洪荒之力”真心話,引燃了國人的無限喜愛與推崇。她動人的“洪荒之力”,也讓臺上豪言壯語、臺下偷雞摸狗的貪官無地自容。許宗衡承諾“不留敗筆,不留遺憾,不留罵名”;張宗海宣誓“發揚草鞋精神,心中時刻裝著人民”,玩起女人卻心裝三要求:本科、漂亮、沒結婚。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無論從尊賢崇德的現實歷史的角度,還是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出發,章綸忠諫為民的精神風格,都需大力弘揚。
震宇悄問:世上真有風水?能逢兇化吉,轉運騰達?我回:風水有善惡之報。福由心生,境由心造。其實最美風水在心田。
“風水”本為相地之術,古稱堪輿術,是一種研究環境與宇宙規律的哲學。其核心思想是人與大自然的和諧,勸人為善,順應自然,優化環境。古人認為,人的心靈與天地的靈氣是相通的,美好的心靈才能和美好的風水地同氣感應,才能獲得吉氣善待。反之,則受懲罰。
譬如泰安原市委書記胡建學,堅信一位“相學大師”說他有副總理之命,只缺一座橋,于是他絞盡腦汁,讓國道改線跨越水庫而修橋……結果橋未成,人倒了。
“世上幾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種善得善,種惡得惡。塔若倒了,后人會重建;名若敗了,豈能再重塑?章綸弘塔,尊賢敬德,崇文向善。精神不滅,日月同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