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的筆記》陸春祥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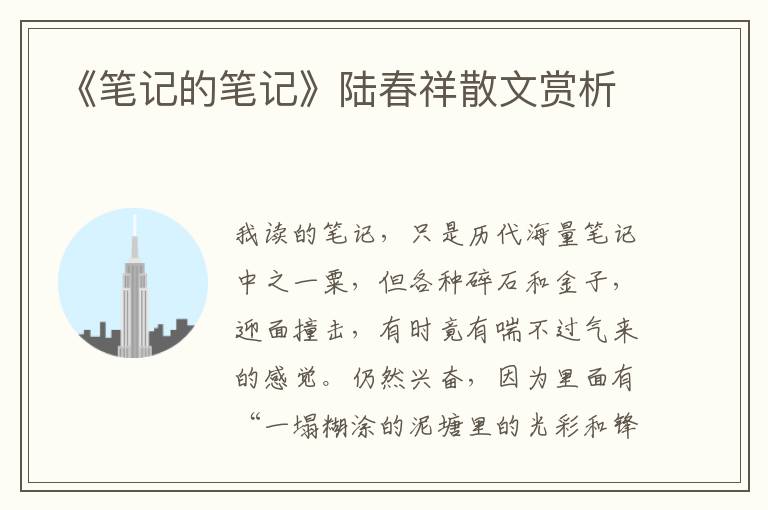
我讀的筆記,只是歷代海量筆記中之一粟,但各種碎石和金子,迎面撞擊,有時竟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仍然興奮,因?yàn)槔锩嬗小耙凰康哪嗵晾锏墓獠屎弯h芒”。
賀知章乞名
秘書監(jiān)官員賀知章,有大名,八十六歲退休,回浙江老家時,皇帝又重重地嘉獎了他,此前,他得到過皇帝的多次褒獎。
賀大詩人和唐玄宗告別時,一把鼻涕一把淚,傷心至極。
皇帝又問:老人家還有什么愿望嗎?
大詩人答:我兒子的大名,到現(xiàn)在也沒有定下來,如果陛下能為他取個大名,那我也是榮歸故里啊。
皇帝想了想回答道:為人處世,最重要的就是講信用、誠信,孚,就是這個意思,有信用才能行得遠(yuǎn),相信你的兒子也是誠信之人。那就取名孚吧,賀孚,如何?
還能如何?太好了!賀大詩人謝了再謝,拜了再拜,把孚字帶回了家。
過了好久,賀大詩人和人嘆苦:唉,不知道皇帝怎么想的,我是吳地人,孚字是爪下為子,那不是叫我兒子為孚(諧音無)爪子嗎?
賀大詩人,詩歌寫得好,官也做得好,至少正部級。他一生榮華,極盡瀟灑,從讓皇帝取名這個細(xì)節(jié)就可以窺全豹了。
他是多么有心計(jì)啊,請皇帝給兒子取名,這個兒子以后的前程肯定美好,有誰敢不重視皇帝?兒子也不小了,就是不給他取大名,如果隨隨便便找個理由向皇帝提要求,不合適,很不合適,那只有等,退休了,最后一個要求,順理成章,皇帝一定答應(yīng),而且很熱心。
他的目的達(dá)到了。
《說文解字》:孚,一曰信也;
《爾雅》:孚,信也。
孚,可作名詞,信用、誠信,《詩經(jīng)·下武》:成王之孚;
孚,可作動詞,相信,《曹劌論戰(zhàn)》: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這確實(shí)是一個好字,哎。
賀大詩人對這些,肯定知道,他卻鉆牛角尖,偏要從字形上鉆。
我特意咨詢了搞古文字的博士同學(xué)W。
他說,其實(shí),孚這個字,“信”已經(jīng)是引申義。“孚”本身就是“孵”的意思,一只成年鳥在孵化自己的孩子。甲骨文的“孚”上面確實(shí)是兩只鳥爪子,下面是一層草,中間是一只鳥蛋,意思是鳥在窩里孵小鳥。
我接著問:那是不是可以說,祝他兒子像鳥兒一樣快出殼快快長大成才呢。
當(dāng)然可以了。
有原義,再加引申義,唐玄宗還是蠻有水平的嘛,我取個名字,要你培養(yǎng)教育出一個誠實(shí)守信的孩子,報效國家。
呵,也許他當(dāng)爪子當(dāng)怕了,所以,想得特別多吧。
(唐·鄭綮 《開天傳信記》)
神也管人間事
泉瀑交流。松桂夾道。奇花異草。照燭如晝。
看一個兩神相遇的對話片斷。
一人駕鶴而來。王母娘娘表示歡迎:我老早就盼望劉先生來我處訪問了。
劉先生笑笑:剛剛碰到蓮花峰的道士匯報工作,需要立即拍板,所以來遲了些,望見諒。
王母娘娘好奇:那道士匯報什么工作呢?
劉先生答:浮梁縣長請求延長他的生命。我一查,這個縣長,是因?yàn)橘V賂而當(dāng)?shù)墓伲覍习傩找稽c(diǎn)也不好,工作也不努力,一天到晚只惦記怎么讓自己的財產(chǎn)增加,在官場上還陽奉陰違,擔(dān)心快要死了,就來求命。
王母娘娘很想知道結(jié)果:您批準(zhǔn)他延長生命了嗎?
劉先生答:唉,那道士估計(jì)是得了浮梁縣長的好處了,拼命說好話,但是,他報告得還是很懇切動人的,態(tài)度端正,頗入情理,我特批準(zhǔn),延長浮梁縣長壽命五年。
田璆問王母:這個劉先生是誰啊?
王母答:他是漢朝的天子。
對話有趣,是因?yàn)樗鞋F(xiàn)實(shí)的影子在。
什么樣的官是好官?按劉先生的描述,反面推斷就是了。
什么樣的官是壞官?漢朝的劉天子,判的卻是唐朝縣官的事,時間在演化,標(biāo)準(zhǔn)卻沒怎么變,走歪道,不利人,品性差,都讓人討厭。
漢朝的天子,怎么會斷唐朝的事?呵呵,神也管得寬嘛,神極忙。
漢朝的天子怎么會妥協(xié)呢?人都喜歡拍馬屁,神也喜歡拍馬屁,盡管他明察秋毫,但也經(jīng)不起馬屁。
(唐·李玫《纂異記·嵩岳嫁女》)
嚴(yán)防老公出軌
李相福的妻子裴氏,性妒忌,他小老婆雖然比較多,但裴氏看得很緊。
有次,李做鎮(zhèn)守滑臺的長官,有人獻(xiàn)上一個漂亮的女奴,李長官想親近,也沒有得逞。
一天,看裴氏還高興,李長官就將閑話說給裴氏聽了:某官員已經(jīng)做到節(jié)度使了,但身邊卻只有年老的傭人,他老婆對待老公,是不是太刻薄了些啊?
裴氏答:是的,但不知您指的是什么。
李長官就說:鬧,人家獻(xiàn)了個女奴給我,可以當(dāng)傭人嗎?
裴氏答:做傭人完全可以的。但是,只能服侍穿衣吃飯什么的,別的不行!
李長官看著身邊這個美人,沒有機(jī)會,下不了手。
李長官想出一計(jì),他對裴氏的丫鬟們講:假如夫人洗頭發(fā),你們一定要趕緊來報告我!
沒過多久,果然有人報告夫人要洗頭發(fā)。
李長官隨即就假裝自己肚子疼,立即將漂亮女奴喊來,想行好事。
丫鬟們回去,看著夫人在洗頭發(fā),想想洗頭發(fā)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不少時間,于是就向夫人報告說,先生剛剛突然肚子疼,我們還是先報告一下。夫人一聽,信以為真,立即披著濕發(fā),赤著腳跑來,問李長官哪兒疼。李摸著肚子,裝出極痛苦的樣子,裴氏擔(dān)心極了,她自作主張,將治肚子疼的藥倒進(jìn)童子尿中,要李長官趕緊喝下。
聽說長官病了,第二天,一幫下屬趕來問候長官。李長官就一五一十將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訴了大家,說完后自嘲:一事無成,還是守本分算了,只是那一大壺童子尿,味道真苦啊!
眾人笑倒。
這個裴氏,雖是妒婦,但還不是極端。
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卷八有:房孺復(fù)的妻子崔氏,忌妒心強(qiáng),對婢女們極苛刻,唯恐她們比自己漂亮,每月只給化妝品胭脂一豆、粉一錢。有次,家里新來一個丫頭,打扮得比較漂亮,崔氏妒性大發(fā),她假惺惺地說:“我?guī)湍阍俸煤么虬缫幌隆!庇谑恰翱唐涿迹郧嗵钪?燒鏁梁;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妝焉”,慘不忍睹。
中國的妒婦之母,應(yīng)該是劉邦的老婆:呂雉將戚夫人砍斷雙手雙腳,挖掉雙眼,弄聾雙耳,弄啞喉嚨,做成人彘,丟進(jìn)廁所中。
極端的妒婦還有,生前看牢丈夫,死后變成鬼,陰魂也在看守,不讓別的女人接近。
從李長官假裝生病可以看出,裴氏雖妒,卻是真心關(guān)愛老公,不僅立即停止洗頭,還積極尋找有效治療的方法。
一個很容易看穿的現(xiàn)實(shí)是,歷代筆記中的許多妒婦,無疑是男權(quán)社會的犧牲品,女人只能是附屬,只能是玩物,怎么能限止男人呢?一定要丑化她們,大大地丑化她們,丑一懲百,男權(quán)制度絕對不能動搖!
(唐·闕名《玉泉子》)
桂管布
夏侯孜做左拾遺的時候,常常穿著桂管布衫(桂管,唐朝行政區(qū),全稱桂管都防御觀察處置等使,領(lǐng)十三州,駐治桂林;桂管布,即木棉布)去上朝。開成年間的一天,唐文宗問夏侯孜:您為什么常穿這種品質(zhì)比較低劣的衣衫呢?夏答:桂管布是粗布,穿著舒適,冬天比較溫暖。
第二天上朝,皇帝對宰相講:我觀察夏侯孜,他一定是個正直可靠的干部。宰相經(jīng)過秘密調(diào)查,向皇帝匯報說:夏侯孜品質(zhì)真的很不錯,是當(dāng)今的顏回和冉求(孔子著名的學(xué)生)。皇帝很感慨,也穿起桂管布衫。于是,滿朝干部紛紛效仿,桂管布的價格一下子高起來了。
一個人的穿著,和他的性格有相當(dāng)大的關(guān)系。
夏侯孜看中桂管布,其實(shí)是一種境界的體現(xiàn)。衣食的標(biāo)準(zhǔn)和尺度是無限的,而那些所謂的低劣衣物,主要作用是果腹和飽暖。之所以便宜,是因?yàn)橹谱鞯暮喡痛植冢鸸懿季褪且焕∏∈沁@種棉布衫,夏天透氣功能好,冬天也溫暖。
當(dāng)然,也有裝出來的。
楊堅(jiān)想搶太子的職位,裝得很勤儉,天天粗布衣衫,吃得也一點(diǎn)不講究,還對老爹十二分的孝順,終于得到了太子位,終于當(dāng)上了皇帝,于是,他的本性一下子暴露,隋煬帝時代,僅江都的宮女就有數(shù)萬人。
現(xiàn)時代也有新聞報道,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長魏鵬遠(yuǎn),穿衣樸素,上班還騎自行車,家中卻搜出上億現(xiàn)金。執(zhí)法人員從北京一家銀行調(diào)去十六臺點(diǎn)鈔機(jī)清點(diǎn),當(dāng)場燒壞四臺。
桂管布的升值,也不是什么壞事,既能倡導(dǎo)一種作風(fēng),也能拉動一個地方的經(jīng)濟(jì),更能讓老百姓得到大實(shí)惠。
桂管布,無論在什么朝代,都是一面鏡子。
(唐·闕名《玉泉子》)
狗頭新婦
賈耽做滑州節(jié)度使的時候,他轄區(qū)的酸棗縣,有個新媳婦,對婆婆非常不好。
她婆婆年紀(jì)大了,雙目失明。早餐時,媳婦將早飯裹著狗糞給婆婆吃,婆婆吃了,覺得有異味。這個時候,兒子回來了,她問兒子:這是什么東西啊,剛剛你老婆給我吃的早餐。兒子一看,仰天大哭,突然,天上打下驚雷,就好像有人將他老婆的頭割去,用狗頭接上。
賈長官知道這件事后,命令兒子牽著狗頭媳婦,在縣內(nèi)游行,用來警告那些對父母不孝順的人,當(dāng)時的人,都叫那婦人“狗頭新婦”。
“狗頭新婦”,從科學(xué)角度看,顯然不可能,這是人們對懲罰不孝媳婦的美好向往。
惡媳婦一定是有的,對待婆婆百般不好,但不至于將狗糞拌進(jìn)飯中讓婆婆吃,難怪天雷要打。
本書卷八中有“吃便桶飯的媳婦”一節(jié),和這個“狗頭新婦”正好成鮮明對比,中國大地上,更多的是任勞任怨、替夫家養(yǎng)兒育女敬老的媳婦,這是傳統(tǒng)美德。
(唐·李冗《獨(dú)異志》卷上)
筷子代表正直
宋璟做宰相時,上下都有好評。
有年春天,御宴舉行。唐明皇一高興,將自己正在用的金筷子,賞給了宋宰相。
雖然接受了賞賜,但宋宰相心里并不踏實(shí),他弄不清,皇帝為什么要賞他一雙筷子。所以,在宴會上,宋大人不知道如何感謝皇帝。明皇見此,笑笑說:我賜給你的,并不僅是金子,而是用筷子,代表你的正直。
噢,原來如此,宋宰相愉快地叩頭致謝了。
筷子代表正直,估計(jì)在唐明皇以前,還沒有約定俗成,否則,宋大人一定知道這樣的習(xí)俗。
筷子本來就是直的,用筷子的直,來代表人的正直,也是恰到好處。
當(dāng)然,皇帝本來就是習(xí)俗或是時尚的創(chuàng)造者,漢武帝用夫人的玉簪搔搔頭,于是,玉簪就流行起來,甚至?xí)右粋€產(chǎn)業(yè)。
筷子天天要用,正直人人喜歡。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上,《賜箸表直》)
記事珠
開元年間,張說做宰相時,有人送了他一顆記事珠。
從外觀上看,此珠沒多大特別,紅色,發(fā)光,但如果人有什么遺忘的事情,摸一摸記事珠,就會覺得心神開悟,事無巨細(xì),非常清晰明了。
張?jiān)紫喟延浭轮楫?dāng)作寶貝,悄悄地藏起來,從來不給人看。
記事珠有這樣的功能,肯定是人的想像。
按我的猜測,張?jiān)紫嗟挠浶蕴貏e好,簡直超常,辦事也非常有條理,別人可能就以為他有這方面的寶貝。或者,某天,張?jiān)紫嘤幸庾R地放了一個風(fēng),讓人們認(rèn)為他的記性好,是借助于記事珠。
想像往往是美好的。如果有記事珠,我們做什么不會成功呢?特別是那些日理萬機(jī)的人,皇帝,宰相,國家大事每天得有多少要處理啊。
前些天,我看到一則新聞,說是三十年后,人們只要吃一顆藥,想學(xué)什么就學(xué)什么,英國人已經(jīng)在研究了。
呵,我唯一擔(dān)心的就是,什么事情也不忘,會不會帶來另一種痛苦呢,因?yàn)槿祟惒豢赡芴焯於寂龅阶屓诵腋6淇斓氖掳。?/p>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上,《記事珠》)
粉蝶使者
開元末,每到春分這一天,唐明皇都在宮中宴飲,從早到晚。
玩累了,去哪一房休息呢?那就玩?zhèn)€游戲吧:讓嬪妃們在頭上插滿各類鮮花,明皇親自捉來粉蝶放飛,那蝶飛到誰的頭上,就臨幸誰。
隨蝶所幸的游戲,后來因?yàn)閷櫁钯F妃才廢除。
唐明皇這樣玩,應(yīng)該是無師自通。他還沒有得到楊貴妃前,宮中那些想要和他睡的嬪妃,就有以投金錢賭博定人的,誰贏誰陪睡。
風(fēng)流從細(xì)節(jié)體現(xiàn),無需多言。
不過,唐明皇只是其中代表之一罷了。
風(fēng)流皇帝,要把日子過出味道來,就得要有刺激的方法,而方法往往因人因地而宜,對唐明皇來說,前輩漢皇就用羊車隨幸,這樣的方法太土,沒新意,他自然不會模仿。
敬業(yè)勤儉的皇帝,總是出現(xiàn)在王朝初創(chuàng)或者衰敗需要中興時,要指望唐明皇不去玩這些游戲,還真有點(diǎn)難。楊貴妃來了,讓唐明皇收心了不少,盡管楊是他的兒媳婦,但他是皇帝,他還顧忌什么呢?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上,《隨蝶所幸》;卷下,《投錢賭寢》)
記惡碑
盧奐做過很多地方的官,他任職過的地方,都留下了好名聲,因?yàn)楣芾韲?yán)格,地方上的官員百姓都畏懼他。
看一個細(xì)節(jié):如果有不良行為者,他一定嚴(yán)加處罰,不僅如此,他還將這個人所犯的罪,刻在石頭上,并將石頭立在此人的家門口,告誡他,如果再犯,就處以極刑。老百姓怕了,再也沒有人敢犯罪。
唐明皇為了褒獎盧奐,賜給他五千兩金子,還下詔表揚(yáng),要求官員向他學(xué)習(xí)。
盧奐搞的這個記惡碑,確實(shí)厲害,效果絕對好。
因?yàn)樗サ搅巳藗兊能浝撸瑦勖孀樱l想弄個記惡碑立在自家門口呢?門前有記惡碑,人家還會和你交往嗎?你的孩子從小生活在陰影中,你怎么在這個地方生活下去?
記惡碑,其實(shí)就是一種制度,檔案掛在門前,公開明白,它就是道德碑、德行碑。
當(dāng)然,記惡碑也有一個大大的壞處,就是不容許別人改正,一朝犯錯,終身罪人,而世上一輩子都不犯一點(diǎn)點(diǎn)錯的人有多少呢?
兩害相權(quán)取其輕,盧奐清楚這個道理,唐明皇更明白這個道理,讓百姓聽話,比什么都重要!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上,《記惡碑》)
唐朝嬉皮士
京城進(jìn)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沖、張道隱等,有十來個,不拘小節(jié),生活很隨意,做起事來也旁若無人。
每年春天時,他們挑選妖艷的妓女若干,坐上小牛車,到公園里,水池邊,借著草地,脫光衣服,一邊喝酒,一邊大呼小叫,他們管這叫顛飲。
其實(shí),這也就是一群有點(diǎn)個性的文藝青年。
相比那些正人君子,他們這些做法可謂驚世駭俗了,公開嫖妓,還在公共場合,裸身喝酒調(diào)戲,還唯恐別人不知道。
他們就是隨意生活,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做了,不藏在心里,不偷偷摸摸,前提是,警方不干涉不介入。
這也是一種表達(dá)方式,他們將苦悶、不滿、牢騷,一并發(fā)泄,往往才情縱橫,意氣風(fēng)發(fā)。
當(dāng)然,這樣的文藝青年,一般不會在政治上有什么前途,除非那至高無上的主兒有和他們同樣的愛好,就如后世的高俅一般,蹴鞠蹴得好,就會蹴出一片新世界。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上,《顛飲》)
唐皇帝的狀元情結(jié)
唐宣宗比較喜歡學(xué)習(xí),時常和一些學(xué)士議論前朝的興亡,在議論政事時,往往不知疲倦。他也極重視當(dāng)朝的科舉考試,曾經(jīng)在大殿的柱子上自題:鄉(xiāng)貢進(jìn)士李某。有大臣要外出任職,也時而賦詩贈送,專家客觀評論,宣宗的詩,具有相當(dāng)水準(zhǔn)。
他的孫子,唐僖宗,則喜歡踢球、斗雞、騎射。僖宗還沾沾自樂,認(rèn)為自己擅長跑步擊球,馬球技藝高超。他對滑稽演員石野豬說:我如果參加跑步擊球的進(jìn)士選拔,怎么也得個狀元。石演員笑著回答:如果碰到堯、舜、禹、湯作宣傳部副部長(主考官),那陛下您不免要落第。僖宗哈哈大笑。
唐宣宗李忱,是一個非常不錯的皇帝。他喜歡讀《貞觀政要》,勤于政事,史稱小唐太宗。他還比較謙虛,自題“鄉(xiāng)貢進(jìn)士李某”,學(xué)問肯定在一般的進(jìn)士之上,有這么一點(diǎn)點(diǎn)科舉情結(jié),實(shí)在是人之常情。
唐僖宗李儇,繼位時還是個孩子,在深宮長大,宮中的生活,帶給他的就是肆無忌憚的玩樂。他還想著要弄個狀元玩玩,這樣高的運(yùn)動水準(zhǔn),換成平民百姓,怎么也得是個狀元吧。
我有時想,那些個皇帝在殿試時,碰到有水平的考生當(dāng)然高興,但如果碰到那些水平一般的,一定有苦說不出,不選吧,有失本朝大好形勢,選吧,這些真不是好才,所以,有時會想,還不如自己當(dāng)狀元呢。
我料定,一定會有一些皇帝這樣想的。
歐洲那些要繼位的皇子皇孫們,讀書一定要讀出名堂,世界名校,總要讀個博士出來,否則,將來怎么做君主呢。
即便國內(nèi),少數(shù)已經(jīng)很高位置的高官,也要花些精力和時間,去弄個博士帽戴戴,有的還堂而皇之地兼起名牌大學(xué)的博導(dǎo)呢。
他們的知識有多博?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他們能導(dǎo)什么?也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第一,《宣宗稱進(jìn)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