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君《嵌入生活的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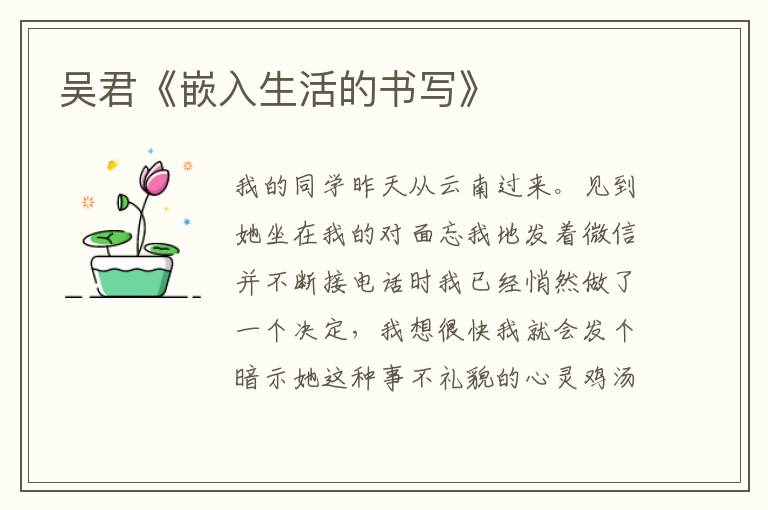
我的同學昨天從云南過來。見到她坐在我的對面忘我地發(fā)著微信并不斷接電話時我已經(jīng)悄然做了一個決定,我想很快我就會發(fā)個暗示她這種事不禮貌的心靈雞湯,除了教育,還想告訴她,我這個社交恐懼癥自閉癥患者能出門吃飯她應當百倍珍惜才是。可是當我們各自喝了一瓶啤酒后,我想法變了,因為她放下電話后告訴我,她破產(chǎn)了離婚了,如今孤身一人,正行駛在各種維權的大路上。
20世紀90年代后期她手持大哥大,腳踩小牛皮鞋與我見面,手指著新一佳百貨的方向對我說,那一片都是自己家的工程時,我除了恍惚而與她再無共同語言。那時候我甚至連自己到底有多么寒酸可能都不自知。
如今,當年他們這些張狂的有錢人藏身于何處,歸隱山林還是沒完沒了地站在時代的潮頭叱咤著風云呢?
記得《十七英里》發(fā)表后,有人曾對這個小說提出異議,認為二十年如何能出現(xiàn)一個富翁,顯然不可信。
可是如果他在深圳生活過,即會明白很多人的二十年,甚至更短的時間,人生都可能發(fā)生很大的變化,完成一個從富有到落魄的輪回可能只需一個錯誤的決策,一個瞬間的手指移動,一次心思的飄忽。例子比比皆是,簡直就是小菜一碟。
我已經(jīng)開始喜歡懷舊,過去懷的是故鄉(xiāng),而現(xiàn)在懷的是深圳的當年。
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我還是一名電臺的記者,有段時間每天都進出在名聲大噪的勞動村。勞動村作為一個著名的觀摩景點,每天接待客人成千上萬。村委書記的馬自達汽車傲慢地停在豪華的村委門前。統(tǒng)一的住房,統(tǒng)一的裝修,甚至于勞動村的村民茫然失措的眼神也是統(tǒng)一的。昔日的漁村村民,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發(fā)生了什么,也沒人告訴他們這從天而降的生活意味著什么。不久前,當我再次路過那里,看到了那里的破敗和蕭條。崗夏、蔡屋圍、白石洲,都已變成了魚龍混雜的城中村。曾經(jīng)的原住民風光不再,曾經(jīng)的外省人開始過上了優(yōu)渥的生活,當然,也有進不了城的農(nóng)民和回不去的故鄉(xiāng)。他們多是和我一樣無所適從的外縣人,衣著艷俗、表情混搭,哪怕久居深圳,其精神卻還一直游蕩在故鄉(xiāng)和深圳的長途車上。夢里不知身是客,他們在為自己和家人爭得美食華衣之時,付出的卻是整個的青春和全部的熱情。
千禧之年,我見證了深圳農(nóng)村城市化,土地換社保,改舊與違建,秧苗事件,房價的飆升,深圳與香港,土著與外省人,優(yōu)勢互換,欠薪,收容制度,新勞動法實施,關內外的行政阻隔,男女比例,移民的后遺癥等。深圳人的各種況味,被我收了滿眼滿心,已豐富成不寫不快。這一塊膠著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之美、中國之癢之痛的土地,無時無刻不牽動著全中國的神經(jīng)。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為寫作,我的目光不可能投向那里,投向我生活之外的人群,不可能與他們的生活產(chǎn)生交集,更不可能如此緊密地隨著這座城市的脈搏一起跳動,血脈賁張,愛恨交集,對人心挖地三尺不肯罷休。我從不認為這座特別的城市會帶來一成不變的人和故事,所以我從來沒有題材匱乏的焦慮。
我希望把中國最活躍的人群和他們所創(chuàng)造出的這個大都會,持續(xù)嵌入我的書寫之中,用一個個故事,串起深圳人的心靈秘史。而這,就是我的動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