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家園《柔軟而溫和的“反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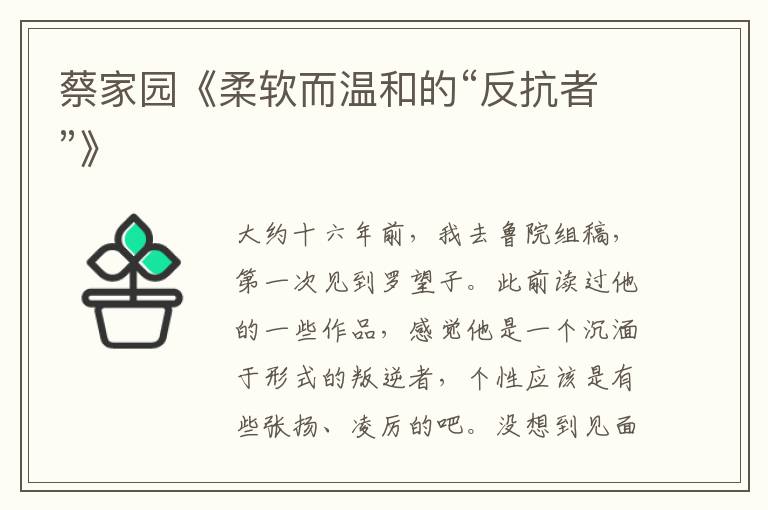
大約十六年前,我去魯院組稿,第一次見到羅望子。此前讀過他的一些作品,感覺他是一個沉湎于形式的叛逆者,個性應該是有些張揚、凌厲的吧。沒想到見面之后完全是另一種印象:他的話語不多,語調低低,聲氣軟軟,那眼眸縱然銳亮,目光卻顯得柔柔的,一副溫和、敏感的江南才子模樣。后來更多地讀他的作品,感到他的身上具有某種許多作家匱乏的東西——努力反抗的信念,只是因為他表達溫吞而不夠引人注目罷了。在這個信奉“選材要奇、出手要狠、口味要重”的文壇上,他難免會遭遇邊緣化。再后來,我漸漸對他關注得少了……直到去年開研討會再次相見,我發現,他只是頭發變白了,額頭的皺紋加深了,那語調、那眼神依然如昨。再看他的作品,除了題材、敘述偶有變化,寫作的總體調子還是烙著那個“羅望子印記”。在餐廳里凝視著他的那一瞬間,我突然想到,柔軟而溫和的“反抗”,大約正是他不變的姿態吧!
我們都知道,當下消費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快速發展,加劇了文化的大眾化、感官化和快餐化,嚴重削弱了作家的主體意識,也制約了作家進行藝術探索和創新的熱情,作家精神的慵懶化和寫作的慣性化已經成為常態。要想超越這種狀態,必須反抗兩種規約性的力量——一種是寫作者自己的思維慣性,另一種是寫作者之間對某種社會熱點或文學類型的相互模仿。羅望子顯然對此一直保持著警覺。他在一篇隨筆中曾這樣寫道:“一切原創皆先鋒……先鋒行走在歧路上。先鋒是一種氣質。先鋒觸及的是你的心臟。高山仰止,是先鋒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這也使得先鋒活化為最永久的傳說。”在他看來,先鋒就是一種“反抗”。他在談論萊辛時表達得則更為明確:“作家不能隨波逐流,做出一個公共的姿態。我認為每個作家都是不一樣的……”這無疑是自覺的文學清理,清晰地表明他選擇了走一條與眾不同的路。
和羅望子同齡的這一撥作家走上文壇的時候,都是通過反抗宏大敘事,以個人化敘事來標示自己的寫作面貌,在強調回歸文學本體的同時凸顯個體價值。羅望子最初也行走在這個群體之中,但是,沒過多久他就顯示出自己的一些特點來。在我看來,可以借用“微敘事”來描述他的寫作。“微”包含“小”的意思,但又不等同于“小”。就像我們常常使用小情感、小趣味、小感受、小境界這樣的詞語,“小”其實隱含著價值判斷,而“微”則是中性的表達。當今時代,微博、微信、微電影、微社區、微媒體、微信息等等構成了我們生活的重要內容。微,已經成為越來越碎片化、原子化、平面化的世界的表征。羅望子勘破了這個時代的秘密,總是從微小的角度切入現實,試圖撥開被宏大敘事所遮蔽的個體生存狀態,表現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微乎其微的場景、微瀾不驚的故事以及微妙復雜的情感和意蘊。無論是描寫農村生活的《墻》《向日葵》,還是描寫農民進城務工的《珍珠》《灰姑娘》《麥芽兒》,或是描寫城市白領的《非暴力征服》《大雁塔》,還有那些以童年視角講述的往事,如《我們這些蘇北人》《蔡先生》《色不死》《我是小強》等等,呈現出的都是一種非常微小、微妙的日常化生活情境、混沌的情感狀態和幽昧的精神空間,為我們認知這個時代提供了一種比較獨特的視野。
羅望子 “微敘事”并非一種平面化的敘事,而是以寓言化的方式對日常經驗進行隱喻式書寫,力圖超越能指層面而凸顯所指層面的“微言大義”。他的許多小說的標題就具有這種特征,充滿了隱喻性。譬如《墻》象征隔膜和自我禁錮,《珍珠》象征著經歷磨礪后的新生,《向日葵》象征現代生存的不安定和懸置性。他的作品中人物的命名更是耐人尋味:其中一類姓名的文化指向性非常明晰,像《珍珠》中的男主人公叫小水、女主人公叫水仙,前者象征外剛內柔的性格特點,后者則象征潔身自愛的生命形態;《麥芽兒》中的女主人公叫麥芽兒,男主人公叫高粱,他們的女兒叫穗子,這些充滿泥土氣息的名字象征著生命與活力。還有一類是完全符號化的,如《邂逅之美》和《連理枝》的主人公都叫K,《為學》和《修真記》中的主人公都叫小D,《陰謀》中的主人公叫B,這些極其抽象的名字不僅具有相應的哲學意味,而且宣示了小說的美學風格。他的作品中的不少事物也具有隱喻性,譬如《我是小強》中的圓形玉佩,象征母愛和詩意世界;《羨慕秋葵》中秋葵吃的“臉盲果”,象征著對現實的逃避。他的新作《邂逅之美》,則在整體上具有隱喻性,頗像一部向卡夫卡致敬之作。小說開頭寫到,“他徜徉在寧海路上,就像行走在擁有這條路的任意一個城市”,奠定了作品模糊、不確定的敘事基調,凸顯了文本的象征性。作家巧妙地將非常“實”的茫然姑娘的故事,也就是社會熱點新聞——學生打老師事件,嵌入“一次邂逅”的“虛”的敘事之中,表現世界的荒謬和人生的無奈,從而實現了對于我們所處時代生存困境的深刻隱喻。
羅望子的小說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反抗“二元對立”模式,著力狀寫社會和人性中混沌的“中間地帶”。
在他的小說中,流行的城鄉先進/落后二元對立模式遭到消解,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種關于 “中間地帶”的表達——鄉村以及城鎮的本相和人的混沌生存狀態。他反對把鄉村描寫成苦難之地,也拒絕將鄉村塑造成精神家園。譬如《墻》,從表面看講述的是農村兩兄弟之間因砌墻引發矛盾的故事,場景、細節都具有強烈的現實感,但是他著意表達的卻是帶有超越性的人性經驗,與我們慣常讀到的鄉村題材小說大相徑庭。在城市書寫中,他則有意背離現代性批判的慣常思路,試圖將鄉村經驗與城市經驗混融,表達一種混沌、微妙而復雜的生存體驗,譬如城市務工者、都市白領甚至城市邊緣人的小苦澀、小成就、小無奈、小空虛、小荒誕、小希望,等等。像《珍珠》講述進城務工男女的情感故事和人生體悟,男主人公小水的寬容、隱忍、善良,女主人公水仙對新生活的夢想以及迷途知返,都融在樸實而生機勃勃的生活流之中,充滿內在的藝術張力。小說敘述從容平靜,渾如涓涓細流,并沒有給出清晰的道德和價值判斷。像《麥芽兒》的主人公麥芽兒進城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實現文學夢想。然而,現實生活中的城市恰恰是反詩性的,這與她的初衷構成了悖論。經歷吊車事故之后,麥芽兒答應和丈夫一起回鄉,但是在小說結尾她逃離了丈夫,因為“她又想到那顆星星一樣的夜燈”。她并沒有完全背棄鄉村,當然也沒有放棄對城市的希望。羅望子總是像這樣,并不給出明晰的價值判斷,而是借助個性化的敘述,將日常生活本身的混沌性、豐富性細致入微地呈現出來,讓讀者去咀嚼其中的意味。
羅望子的大量作品書寫的都是底層小人物的故事,但與我們經常看到的關于底層生活的“殘酷表達、丑惡展覽”又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取消了人性善/惡二元對立模式,常常呈現出混沌而親切的溫情、美好而質樸的詩意。像帶有半自傳色彩的《我們這些蘇北人》,娓娓講述父親和叔叔之間的復雜故事,將親情、愛情、友情交織糅合在廣袤的鄉村原野上,還穿插了一些奇異的鄉俗民風,看似平淡無奇,其實淡而有味。其中,“我”和堂姐雯雯的情感糾葛,既朦朧、曖昧,又純潔、唯美,看不到絲毫的惡俗和頹靡,只有生命原始激情的勃發。小說字里行間洋溢著對于自然人性的贊美,別具感染力。《我是小強》講述的是智障兒小強的故事,選材比較特殊,表達了一種超越形而下的肉身而上升到對于理想人生狀態和生命境界——溫暖、純凈、信任的召喚。他還有一類作品是書寫邊緣人的“邊緣情感”。譬如《羨慕秋葵》,小說中的人物就像老朱所感嘆的,“所有的人,都過著想要的和不想要的生活”,“朝著溫暖的黑暗里走”;即便是黑暗,也都是“溫暖的”。譬如《如夢記》,講述白領葉小碗與副市長燕青、小偷安子的情感糾葛,通過亦真亦幻的描寫,揭示了現代都市女性寂寞、空虛而又充滿渴望的幽昧心靈世界。尤有意味的是,葉小碗的價值系統和情感世界并不像我們慣常理解的那樣是分裂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這無疑是作家對于當代人都市白領生存狀態的獨到發現。
羅望子的寫作持續了近三十年,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文學面貌。就總體而言,盡管他的文本常有變化,但基本文學觀念卻是一以貫之的,譬如立足個體,視點向內,通過挖掘自身獨特的、異質性審美經驗來闡發人性的種種可能,注重文本的隱喻性,試圖重構一種日常生活詩學。他的“微敘事”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80年代先鋒文學中習見的偏執形式和狹隘人性認知,以一種綜合而富有節制的敘述彰顯著一個寫作者既固守自我,又試圖與時代對話的頑強姿態。在先鋒寫作已經式微的背景下,他的堅持顯得尤為可貴。
但是,閱讀羅望子的小說,偶爾也會讓人產生倦怠——那種彌漫的混沌與柔軟,似乎削弱了文學應有的力量感。而這種力量感的缺失,是不是又源自恒定而清晰的價值觀的匱乏呢?這讓我聯想到薩特在《文學是什么》中的一段話:“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寫作。但緊隨而來的則是我是別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說,他必須回應某個要求,他被賦予了某種社會責任。”對羅望子而言,他是以“自由意志”在寫作,但是同時作為“別人心目中的作家”,他是否還需要對生活和歷史作出更有洞見的回應呢?所有偉大的作品都告訴我們,只有當一個作家在精神上豐滿和堅定起來了,他的“反抗”才會具有閃電般的光焰,才有可能穿透存在的迷霧而抵達本質。
有人說,羅望子是中國的卡夫卡;他自己說,“我要我是卡夫卡”。為什么一定要拿卡夫卡來比較呢?我希望羅望子成為“這一個”,他的寫作則成為“最永久的傳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