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華《遵義五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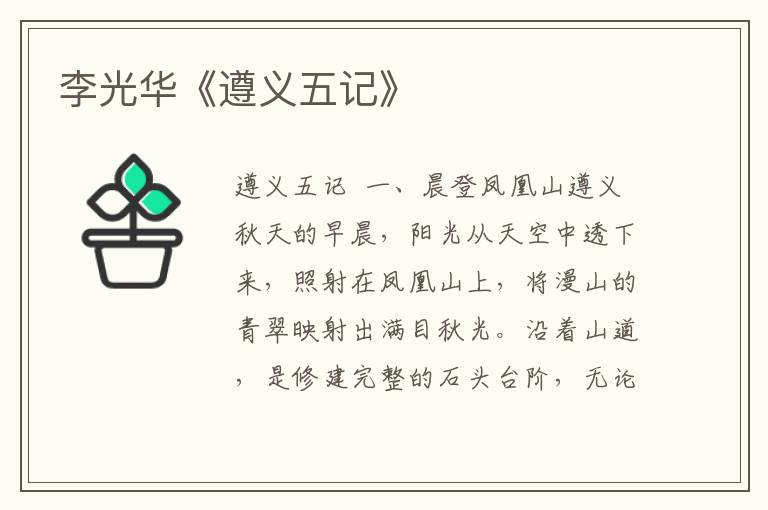
一、晨登鳳凰山
遵義秋天的早晨,陽光從天空中透下來,照射在鳳凰山上,將漫山的青翠映射出滿目秋光。沿著山道,是修建完整的石頭臺階,無論風雨,喜愛登山的人們都可以沿著臺階直上山頂。
沿著臺階走了不遠,一個小小的平臺出現在眼前。幾位老人緩袍輕袖,身形如如行云流水般打著太極拳。卻見一位老者在微寒的晨風中,只著短褲,赤裸上身,雙目微帶殺氣,腳下踢踏有聲,輾轉騰挪間動作剛勁有力,卻不是太極拳。旁觀者中有人詢問,老人自豪地大聲回答:羅漢拳!原來是以實戰威力強而著稱的少林羅漢拳,怪不得老者施展出來如此威猛。
平臺往上,路分兩條。一條往右,是石階鋪就的大道;一條往左,是窄窄的林間土石小道;游人往左而行。數十米外,嘈雜市聲穿過樹林,已經變得微不可聞;林間的鳥鳴清脆悅耳,仿佛在宣稱它們才是這批山林真正的主人。頭上不時有枯黃的樹葉落下,提醒游人秋天的到來。腳下的一塊平整石頭上,落滿了松枝。也許在以前的日子里,當游人來到此處,也許會停下腳坐在石頭上稍稍歇腳吧。回首四顧,山林間人跡罕至,只有鳥鳴相伴,落葉隨風。
忽然耳邊汪汪大叫,幾只狗兒從旁邊沖出,對著游人扯開嗓門,將游人驚嚇了一跳。仔細看,小道轉角處閃出幾間紅磚農家小屋,原來是看家的狗兒將游人當作了不速之客,于是呲牙咧嘴地表示不歡迎。當看到游人伸出手打招呼,狗兒們卻不約而同地掉頭就跑,到了遠處,繼續扯開嗓門喊叫,仿佛在用這種方式捍衛自己的家園。當然,游人只是路過,并無意去侵犯他們的家園。
小道越走越窄,兩側的荊棘草木越來越深,樹木與草葉上的露水也越來越重,不僅打濕了整個路面,也將游人的衣服打濕了小半。植物幾乎完全蓋住了路面,游人小心翼翼踏草前行,仍然幾度踩空,險些摔倒。幾個轉折后,一片小小的平地出現在眼前,草深至膝,草尖上一滴滴露水緩緩滑落。前面的緩坡上,滿眼是綠色的灌木,隨風飄搖。鳥兒的叫聲依舊悅耳,但怎么也看不到鳥的影子,露水濕透了游人衣角。
前方已無路。游人回頭。前方轉角處,一個身影彎下腰,將一個被丟棄在草叢中的礦泉水瓶撿了起來,放在手里的塑料袋中---那是一位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
一片綠色,一個身影。鳳凰山,的確是一座讓人心靈清靜的山。
二、夜聽湘江河
世上的風景,有的很美,適合用眼睛去看;有的很普通,卻在你用心認真感受之后,也會有別樣的感受。湘江河,就是這樣一條必須用心去感受的、流動著歷史的河流。
夜幕下的湘江河,河水靜靜流淌。石頭砌成的河堤上,不知名的植物從堤頂長出,延伸到了堤腳。河邊的人行步道上,夜游的人們從黑暗中悄然走出,靜靜地擦肩而過,又悄然消失在了黑暗中。鑲嵌在河岸兩邊的霓虹,如同湘江河的兩條彩色腰帶,映照著河水,散發出神秘的光芒,隨著流動的河水,光帶似乎也在緩緩流動。
忘記了在什么地方聽過這樣一句話:一座偉大的城市,必定有一條偉大的河流。其實,對任何一座偉大或不偉大的城市而言,在它身旁流過的那條河流,一定是偉大的生命之源。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依托河流而生的歷史。猶如黃河長江之于華夏,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之于巴比倫,尼羅河之于埃及。即使數千年后,依托這些河流而生的文明已經變成了歷史的光影,但這些河流依然在哺育著幾十億它的子民。
湘江河自然無法與這些源遠流長的江河相提并論。但對于遵義,湘江河依然是一條偉大的河,一條流動著歷史的河。
遙想千萬年前,一群衣衫襤褸的人們從山洞中走出。他們扶老攜幼,披荊斬棘,走了無數的路程。忽然有一天,人們歡呼起來,在他們的眼前,出現了一條小河,河岸是一塊山巒之間的平地,各種植物在陽光下蓬勃生長,動物們在草叢中露出身影,看了看人們,一個轉身又消失在了別處。德高望重的老首領一跺腳:不走了,這里就是我們的家!
從此,人們在這塊豐美的土地上男耕女織,生存下來。時光荏苒,祖先們的身影早已遠去,城市卻從茅屋木房,逐漸變換成了高樓大廈。而湘江河,則在千萬年的時光里目睹了城市滄海桑田般的變化。無論是戰爭與和平,生存與發展,遷徙與遠離,都在河流身旁發生。世上沒有任何一部史書,能比這條河流更深刻地記錄了遵義的歷史。
當代湘江河最為人所熟知的歷史,自然是紅軍長征的那段紅色歲月。巧合的是,有一條與遵義湘江河同名的河流,也與它一樣在這段歷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記,那就是湖南的湘江。
在長征史上,湖南的湘江與遵義的湘江河,都是有著極其特殊意義的河流,都以紅色著稱。不同的是,湖南湘江的紅色,是紅軍戰士的鮮血染紅。“湘江之戰,損兵過半”,從江西出發的中央紅軍,八萬六千人的隊伍在湘江戰役后,減少到三萬多人,是長征中紅軍損失最大的敗仗。生死關頭的中央紅軍,被迫轉兵通道,西進貴州,一路浴血,直至遵義城下,湘江河畔。
這里,河水輕緩,物產富饒,百姓熱情。舉著紅旗的隊伍長舒一口氣:就在這里歇歇腳吧,委實也太累了。更何況,出征以來,多有挫敗,下一步該怎么走,也該議一議了。
這一議,就議出了一個光照千古的遵義會議。從此,一支兵臨絕境的軍隊,埋葬了戰友的尸體,擦干了身上的血痕,鐵流二萬五千里,直向著一個方向。這塊地球的紅飄帶,在經歷了湖南湘江的浴血之后,在遵義湘江河又浴火重生,迎風飛舞,直到14年后,染紅了整個中國!
而遵義與湘江河,也從此用那面紅旗,為自己染上了一抹永遠的中國紅!
鳳凰山下,歌聲還在隱隱傳來。
鳳凰山又叫紅軍山,埋葬在以鄧萍烈士為首的紅軍烈士。遵義戰役,中央紅軍獲得全勝,卻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在發起進攻前親自潛伏在湘江河邊觀察敵情,不幸被敵軍冷槍擊中,犧牲在同行戰友張愛萍的懷中。紅軍山上的雕塑忠實還原了歷史細節:中彈的鄧萍倒在張愛萍懷中,右手似舉已落,眼中的神采漸漸消失;悲痛欲絕的張愛萍大聲呼喚中戰友的名字,卻再也無法挽回戰友的生命......
往事如同逝水,永不回頭。但歷史不會象流水那樣,消失無蹤。英雄的背影縱然遠去,而光榮永存。
英雄壯烈,遵義人善良。
紅軍山上有一座“紅軍女軍醫”雕像,遵義人稱為“紅軍菩薩”,是為了紀念一位在遵義因為百姓治病而掉隊被殺害的紅軍軍醫。雕像是女紅軍戰士的形象,而實際上這位紅軍軍醫卻是男性。這位軍醫叫龍思泉,是紅三軍團五師十三團二營衛生員。遵義戰役期間,龍思泉深夜出診,救治生病百姓脫險,卻因此掉隊,被敵人抓住殺害。當地百姓感其恩德,為龍思泉建立墳立碑。因不知龍思泉姓名,碑文刻為“紅軍墳”。當時的國民黨地方政府得知消息,多次派人前來毀墳,均被當地百姓拼死擋住。唯恐激起民憤,國民黨地方政府也只能放棄了毀墳舉動。百姓感念龍思泉救治百姓,將其當作“紅軍菩薩”時常祭奠。而菩薩在中國百姓心目中都是女性形象,久而久之,人們都把龍思泉當作了女性。后來在按照龍思泉的事跡修建紅軍軍醫雕像時,創作人員干脆根據這一傳說,將錯就錯,把龍思泉的形象雕塑成了女性。
一個故事,最后成為了一段傳說;一位英雄,最后成為了一座城市的神靈;而神靈前的香火,見證著這座城市人們的善良與追思。
湘江河的流水聲更大了。抬頭望去,河水翻過河壩奔流向前。回頭看去,河邊邊的霓虹依舊閃爍,卻已經沒有了行人的蹤跡。
這一夜,靜聽湘江河。
三、漫步遵義老城
一座城市,必定有自己的文化地理靈魂;城市的文化地理靈魂,必定有相應的載體,猶如王府井之于北京,徐家匯至于上海,夫子廟之于南京。沒有這樣一個的靈魂,城市就只是鋼筋水泥的聚合和一個地圖上的符號。城市的文化地理靈魂,是歷史積累的底蘊,因時光的流逝而更加芬芳,卻不因歲月的轉換而消磨了容顏。
遵義老城,就是帶著這樣一副不因時光流逝而消磨的容顏,進入了游人的眼中。
老城不大,房屋不高,街巷不寬。街上的行人,腳步不快不慢,目光平淡,行止里帶著一派從容。臨街的街鋪,無論經營的是什么買賣,少有聲嘶力竭的拉客之聲。老板們或是平靜地做著生意,或是淡淡地坐在門口,閑看人來人往。
老城的房屋,一看可知是經過現代手段處理過。但這種處理,沒有當代城市大拆大建的粗暴,而多了份小心翼翼的恭敬,又因這份恭敬,使得這種處理顯得溫柔了些,從而讓老城保留了古代建筑的特點。猶如一位古代佳人,在重新淡淡化妝后,依舊濃妝淡抹總相宜地坐在自家門口,把自己最美的容貌展現在世人面前。
老城不大,作為核心部分的紅軍街就更小。這里的建筑,保留了更多的古意,又因統一的規劃而顯得整齊有序。在這小小的街市上,集中了整個遵義的物產精華:仁懷的美酒,湄潭的茶葉,赤水的竹器,當然,還有遵義人耳熟能詳的雞蛋糕。青石鋪就的街道上,南來北往的游人在一家家街鋪中進出,或是提著遵義的特產,或是什么也沒有帶走,只是在臉上留下微微的笑意。
轉角處,一個小小的門面上,懸掛了兩塊牌匾,一塊寫的是“紅軍書屋”,一塊寫的是“遵義作家書社”。走進書屋,熱情的書屋女主人方竹未語先笑,熱情爽朗,讓人如沐春風。在商業化大潮洶涌席卷城市越來越少有人讀實體書的時代,在城市的一角,仍然有人在堅守著這一方文化水土,在克服重重困難堅守著自己的文化信仰。無論是幼時貧寒的家境,還是走上社會后坎坷的人生路程,方竹從未放棄過自己對于文學與書籍的愛好。還在一個20來歲的年輕女孩時,女主人就出版了自己第一本散文集,然后自己背著書到鳳凰山下簽名售書,遵義人就是從此開始認識到這個倔強而又堅強的女子。堅持文學寫作,傳承長征文化,如今,方竹已經出書九本,紅軍書屋也已成為了遵義一個響亮的文化品牌,書屋的名聲也已經走出遵義,無數喜愛文學和遵義的人們,在全國各地傳揚著書屋的名聲。
走出書屋的游人,手里多了幾本方竹的作品。也許她的文字不一定精美,但只一份堅守,一份堅強,就足以讓人去感受,去品味。
這份堅守與堅強,就是人間最美的作品。
四、苦難與輝煌
一支軍隊,因為一次會議而反敗為勝;一次長征,因為一次會議而起死回生;一座城,因為一次會議而名聞遐邇。在當代中國歷史上,一次會議能留下如此深刻記憶的,唯有遵義會議了。
“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館”,早已久聞大名。但是在人到中年后,才第一次走進這座建筑。那么,在這座建筑里,能讓我看到什么,能讓我感受到什么?
我看到了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與軍團政委楊尚昆和他們的下屬彭雪楓的臥室。出乎意料的是,彭德懷和楊尚昆的臥室里,只是一被一褥,一張木板搭在兩個長椅上,這就是他們的床。而隔壁彭雪楓的臥室,不僅采光擺設遠遠超過彭、楊的臥室,就連床也是一張實木雙人床。兩個臥室對比,讓人心有感概。作為下級的彭雪楓能有比上級更好的待遇,很顯然是因為他在長征前夕在戰場上受了重傷,從而得到了戰友們的照顧。在那個年代,紅軍隊伍里既有上下級關系,更有人人平等的原則和戰友情、艱苦樸素的奮斗作風。
多年后,在解放戰爭的西北戰場上,一位舊衣破履的解放軍軍人來到一位老農的水桶前要了一碗水,并與老農笑語交談。一位目睹了這一過程的被俘國民黨將軍在得知這位身著破舊的軍人竟然是解放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后,仰天長嘆:黨國不滅,是無天理!
從遵義到西北,從紅軍到解放軍,彭德懷那一代軍人,他們的本色一直沒變。
我看到了羅炳輝、董振堂、陳樹湘的照片。
羅炳輝,紅九軍團軍團長。這位著名的戰將,電影《從奴隸到將軍》主人公羅霄的原型,一生戎馬,身經數千戰。無論是國民黨軍隊還是日寇,都對他聞風喪膽。然而這位戰將,在抗戰勝利后不幸因病逝世。令人憤慨的是,內戰爆發后,將軍的遺體被國民黨軍隊從墳墓中挖出,百般凌辱。在戰場被將軍打的落花流水的國民黨軍隊,就是用這種無恥至極的方式發泄著他們對將軍的恐懼和憤怒。一代名將,虎落平陽被犬欺!
董振堂,紅五軍團軍團長。這位從國民黨陣營轉到人民軍隊的將軍,意志堅定善打硬仗。長征路上,紅五軍團為全軍后衛,以鐵的作風無數次地阻擊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確保了紅軍主力的安全,被紅軍戰士親切地稱為“紅軍的鐵屁股”。一次阻擊戰中,紅五軍團與敵拼死廝殺,傷亡慘重。但上級卻傳來命令:一位紅軍女戰士即將生產,紅五軍團必須抵擋到孩子安全生下。董振堂當即下令全軍死死擋住敵人進攻,直到母子平安的消息傳來。可惜這樣一位虎將,卻在長征結束后的紅西路軍河西走廊之戰中,奉命死守高臺城,與紅五軍團3000將士全部壯烈犧牲!將軍的頭顱被殘暴的敵人砍下,懸于城門!多年后,葉劍英元帥含淚揮毫為將軍題詩:英雄戰死錯路上,今日獨懷董振堂,懸眼城樓驚世換,高臺為你著榮光!
陳樹湘,紅三十四師師長。長征開始時,率全師為中央紅軍總后衛。湘江之戰,紅軍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中強渡,紅三十四師與十幾倍于己的敵人鏖戰,保證全軍渡河,自己卻被敵人包圍。陳樹湘在最后的時刻,已經身負重傷,扔推開保衛自己的警衛戰士,拔槍戰斗,最后彈盡被俘。不甘受辱的陳樹湘在敵人將他抬去請功的路上,從腹部傷口處掏出腸子絞斷,壯烈犧牲!和他一起犧牲的,是紅三十四師幾乎全師的6000名戰士!
我看到了紀念館里的文字說明:在紅軍長征轉戰貴州的日子里,有19400多名貴州人參加了紅軍。而這近兩萬貴州子弟,最后絕大多數沒有回到貴州。我還知道另外一個數字: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時有86000人,長征結束到達陜北的,不過7600人。
長征毫無疑問是輝煌的,但毫無疑問這也是一場苦難的征程。烈日狂風暴雨,山巒大河激流,敵軍圍困千萬重。長征的日子,每一天都在艱難中度過,長征的路程,每一里都是在艱難中跋涉。能走完全程的,真的是極少數。絕大多數的人,都倒在了路上......
大廳里,數十位遵義會議的參加者的塑像靜靜站立。他們神情沉默,靜靜地望著前方,望著后來人。在這幾十個人的身后,是數十萬人們看不到的紅軍烈士的身影......
時間在這里,似乎永遠靜止。
歷史的記錄是:1935年1月15日---17日,遵義會議。
五、播州城夜語
今晚,將是我此次遵義之行的最后一晚。明天,我將返回仁懷。
其實,這次遵義之行不是旅行,只是我在心里頑固地看作是旅行罷了。
因為劇烈的頭疼,來到遵義求醫。住院初期,頭疼折磨的我死去活來,茶飯不思,每天不是昏昏沉沉地在醫院輸液,就是在賓館渾渾噩噩地休息。外間的一切對我來說既沒有吸引力,也無力去感受。
直到來到遵義的第四天。
那天早上醒來,忽然感覺頭疼減輕了很多。推開窗戶,對面的鳳凰山上,萬木蔥蘢的秋光躍進眼中,清晨的風吹進房間,頓時精神一振。
我走出房間,朝鳳凰山走去。
從這天起,我開始行走和體會遵義。
清晨,我攀登鳳凰山,呼吸林間的新鮮空氣;中午,我走進老城,感受遵義的歷史文化;晚上,我在湘江河畔漫步,聽濤聲起落。
病痛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我無法控制。
但對于一個喜歡寫作的人而言,把自己眼睛看到的美麗景色、耳朵聽到的輕輕風聲、鼻中嗅到的淡淡芬芳用筆記錄下來,用文字描繪出來,是應該辦到也必須辦到的事情。而遵義,恰恰有著美麗的風景可以讓你去看,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讓你去感受,有熱情善良的人讓你去感動。
沒有人喜歡病痛,我也一樣。但病痛既然無法控制,何不讓這病痛的過程多少開心一些呢?
于是,就有了這篇《遵義五記》。
我與遵義,其實既近又遠,既熟悉又陌生。
近,是因為我居住的城市與遵義不過一個小時車程;熟悉,是因為每年都要來幾次遵義,對遵義的市容市貌大致是知道的;但畢竟不在遵義居住,這就導致對遵義多少還是有心靈上的距離。這心靈上的遠,又導致了陌生感。
仔細想來,冥冥之中,遵義與我有緣。
四歲時,全家從故鄉山東遷往貴州仁懷。人生中第一次見到的大城市,就是遵義;人生第一次盡孝,是十歲時陪伴父親在遵義住院;人生第一次單獨在外地長時間住院(就是這次),也是在遵義。
因為這種緣分,這次,我終于能零距離地呼吸遵義的氣息,感悟這座城市的靈魂。
每個早晨,我穿越林間石階,拂開飄落的秋葉,登上鳳凰山頂,沉醉在漫山的碧綠之中。每個中午,我迎著人流,走進老城,感受城市城市遠古至今的芬芳。每個晚上,我走在湘江河畔,聽取河流講述無數的城市故事......
愛上一個人,或許很容易,因為會一見鐘情。愛上一個城市,卻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鋼筋水泥的外表下,慢慢感受它的靈魂,它的歷史,它的文化,乃至于生活在這座城市中的人。正如在鳳凰山上那位拾撿垃圾的中年人,那位在醫院里輕聲細語告訴我如何保管自己健康檔案的老阿姨,那位在20年的時光里歷盡艱難仍然在堅守著自己對書與寫作理想的老城紅軍書屋的女主人......
我想,我感受到了遵義的靈魂。那就是我在這座城市里隨處可見的四個字:遵道行義。
猶如我在遵義的十多天里,隨處能感受到的遵義人的善良、溫和;猶如歷史記載的紅軍長征后,大量的紅軍傷員得到遵義人的救助的歷史;也猶如那位為百姓治病的紅軍軍醫龍思泉,在犧牲后百姓拼死保護其墳墓,稱龍思泉為“紅軍菩薩”的故事。遵義,遵義,遵道行義,多么絕配的遵義靈魂!
就這樣愛上一個城市,愛上遵義。
明天,就要離開遵義了。
生命是一個過程,而病痛,則是這一過程中最大的灰暗片段。好在這個片段,是在遵義度過。于是,灰暗中也能讓我看到亮光。
感謝遵義,賜予我的這點亮光。
再見,遵義,晚安,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