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西行日記》經典散文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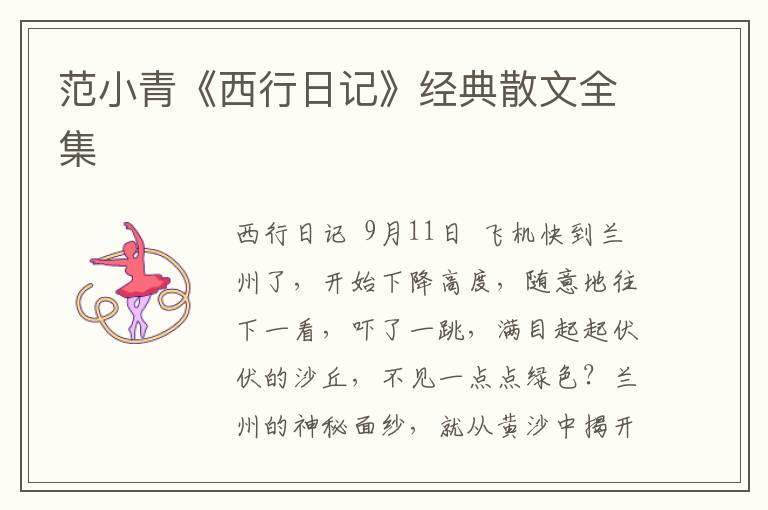
西行日記
9月11日
飛機快到蘭州了,開始下降高度,隨意地往下一看,嚇了一跳,滿目起起伏伏的沙丘,不見一點點綠色?蘭州的神秘面紗,就從黃沙中揭開了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經過了短短的兩個小時,一切都變了。從上海虹橋機場出發時,下著小雨,氣候濕潤宜人,遍地郁郁蔥蔥,這一種反差,這一種突變,來得太快,來得太突然,就在這突然的一瞬間,心里就明白過來:我到西部了。
從機場到蘭州的高速公路兩旁,也依然是黃土黃沙一片,遠遠近近高高低低的山上,種著星星點點的小樹,長得不滋潤,不旺盛,綠也是一種灰蒙蒙的綠,讓人懷疑它們最后到底能不能長大成材。初到西部,心里已平添出蒼涼來了,在我自己生活的江南水鄉,是產生不出這種感受的。
如果說這是到西部到甘肅到蘭州的第一個震撼,那么,第二個震撼仍然是來自蘭州,那是一片充滿生機的綠色的蘭州。這使得我再一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如此美麗滋潤的一座城市,簡直就像是天上掉下的一塊瑰寶,落在了一大片的沙土之中。但天上是不可能掉下一座城市來的,每一座城市都是這座城市的人民自己建造起來的。只是,當蘭州人民在建造蘭州的時候,所付出的努力和代價,恐怕是我們這些來自東南省份的人所難以想象的。每一個小學生,放下書本,騰空書包,到很遠很遠的河邊去,用稚嫩的肩膀背上一塊冰,來滋養一棵樹。就是這樣,蘭州人建造了今天的蘭州,創造了一個奇跡,創造了一個神話。
在蘭州寧臥山莊,在滿園的果樹和成熟的果子的陪伴下,度過西行的第一個夜晚。
9月12日
甘肅很少下雨,一年的降雨量,有時候都不及東部或南方的一場雨,但我們到蘭州的當天晚上,就下了一場雨。因為下雨,氣溫陡然下降,早晨起來就感覺到逼人的寒氣了,雖然是在九月份,卻已像家鄉的初冬了。出發之前,腰椎間盤突然出了點問題,到蘭州碰上變天,一下子更嚴重起來,幾乎不能行動了,心中十分焦急。同行的另一位女作家李蘭妮,也是位病號,我們兩人互相鼓勵,她怕我打退堂鼓,我也怕她打退堂鼓,便相約著,上午放棄了登白塔山,趕緊去商場買棉衣,去藥店買藥,又請推拿醫生來治療,希望不要影響明天的啟程西行。
下午壯行式,晚上甘肅省委馬副書記宴請采風團,大家興高采烈,斗志昂揚,我卻心下忐忑。因為腰的情況不僅不見好轉,反而愈加嚴重起來。去向我們的團長、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張健同志說明情況,言下之意,萬一明天好不了,恐怕是不能西行了。張團長說,我也有這個病,我知道這個病的麻煩,先休息,明天再看情況。
都已經到了蘭州,卻不能西行,那算什么呢,半途而廢?可是這連半途也算不上呢。
懷著沮喪的心情入睡。
入睡前,李蘭妮說,我替你禱告吧。
9月13日
早晨起來,寒氣逼腰,有好幾個人,像青島的季宇、金川集團的馬虎中科長都還穿著短袖,我卻連毛褲都穿上了,腰仍然是僵硬如鐵且不能動彈,但是大家鼓勵和期盼的目光,讓我的紛亂的心平靜下來,也做出了最后的決定:走!
我們的副團長、《飛天》雜志社主編陳德宏,給了我一張特殊的“臥鋪”——在面包車的第一排,空出三張位子,讓我躺下。
感謝陳主編,也感謝全團的人,沒有你們的幫助和鼓勵,我也許走不了這一趟。這是一輛中型面包車,除了最后排放我們的行李,其他位子都坐滿了人,《飛天》編輯部的女博士辛曉玲只能坐在后面的加座上,我卻一個人占了三個位子,躺在“臥鋪”上,腰是松弛些,心里卻十分沉重、愧疚,尤其碰上路途顛簸時,知道后排的人像在扭秧歌,心中更是不安,都是寫東西的人,長坐的職業,恐怕誰的腰也不好到哪里。
大家都笑言,我們買一張票,你要買三張票,又說,范小青是躺著走進西部的。
今天的日程是這樣的:中午到五涼古都武威,下午參觀海藏寺、文廟、銅奔馬出土地雷臺,晚上與武威文學界座談。與武威的作家李學輝相識。李學輝戴近視眼鏡,好像度數很高,話不多,有些深沉,也有些平淡,但我能感覺到他的內心是熱烈的,是奔放的,是細膩的。晚上讀他發表在《西涼文學》上的小說三題,跟他走過西部的田野,走過西部的冬天,更走近了李學輝。
《西涼文學》是武威市作家協會主辦的文學刊物,沒有正式編制,沒有正常經費,但是他一直堅持著,堅持著這塊陣地。為了感謝武威市領導對文學的支持,在座談會上,李學輝向到場的領導深深地鞠躬,感動了所有在場的人。我想,當時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愿意像李學輝一樣,為《西涼文學》,為西部文學,為文學,深深地鞠上一躬。
9月14日
昨晚住在武威,是一座比較老式的招待所,也干凈簡潔,就是聲音比較大,服務員、賓客都在走廊里大聲說話、走路,卡拉OK廳也和客房緊緊連在一起,聲音就更大了,我們的窗下,是一大片停車場,一直到后半夜,還有人在那里大聲吵吵嚷嚷,可能是喝了酒興奮。天不亮的時候,武威的空軍開始飛行訓練,轟鳴聲不斷。但就是在這樣在環境里,我卻睡得很好,一邊聽著那許許多多的聲音,一邊做著夢。早晨起來問武威的朋友,天天早晨飛機這么鬧,你們怎么辦?他們說,習慣了,哪天沒有了飛機聲,還睡不穩呢。
早飯后從武威出發,前往金川公司。金川公司是此次東部作家西部行活動的主要支持者,他們派出兩輛車和宣傳部的一位馬科長全程陪同。馬科長叫馬虎中,在路途中他片刻不停地講了一個小時,講甘肅的風土人情,講金川公司,我躺在“臥鋪”上,睡了一會兒,醒過來,他還在講,嗓門大,中氣足,口才好,怪不得長得那么結實,原來滿肚子盡是知識水平的分量。
沒來金川之前,甚至不太知道有金川,知道有一種化學元素叫鎳,但是不知道鎳是什么,只知道鎳跟我們的生活沒有什么關系,它離我們那么遠,遠得幾乎在我們的生活中從來不會有人提到它,想起它。
現在我們來到金川,金川是中國的鎳都,全國百分之九十的鎳在這里產出,鎳就這樣一下子擺到了我們面前。
下午參觀金川公司的各生產車間,讓我們切身感受到什么叫大規模,什么叫現代化,什么叫鎳都。
9月15日
鎳都的建設者給我們講了這么一個故事。五十年代,一位牧羊的老大爺,無意中揀到一塊綠色的石頭,大爺將它帶回來,交給了生產隊長,生產隊長交給了大隊長,又到了公社,輾轉地送到地質隊員的手里,一座稀有的鎳礦就這樣被發現了。
從那塊石頭開始,到今天金川公司年生產7萬多噸鎳,以及鈷、銅等,鎳的產量占了全國鎳產量的百分之九十,2004年,金川公司將實現資產總額和銷售收入雙百億。這中間,金川人付出的艱辛是難以估量的,在金川公司座談時,我用了一個蹩腳的比喻:爬山和爬沙山,爬山者的精神誠可贊,爬沙山者的精神更可貴,那是爬兩步退一步的,要有數倍的勇氣和耐力,要有數倍的犧牲和奉獻精神,金川公司的發展過程,就是金川人登沙山的過程,他們已經登上了一個又一個的山峰,但還是繼續地往更高處攀登。
下午是在金昌市內活動,與金昌市的文學界朋友座談,為記住這次難忘的文學活動,我寫了一篇文章交給《金昌日報》:
(一個人一輩子要走過多少地方,好像是沒有定數的。也許有定數,冥冥之中會有一種力量早就決定了人一生的行蹤,但是我們不知道。我們只是在歷史的某一個時間和空間的交叉點上,知道我們要出發了。于是我們就出發了。我們經過各種各樣的地方,有些地方以后還會再來,再來,一次一次地重復地到達,但是有更多的地方,我們這一輩子,可能只去一次。去過這一次以后,這個地方就成為我們的記憶,成為我們的精神享受,或者,我們在不多久以后就忘記了它。但是也許過了一些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以后,在某一天,我們突然地又想起了它,想起了那一年,那一天,我們走過那個地方,想起在那個地方待過的那一天,想起那一天里的每一個細節。
這一次我們走過了金昌。在到金昌之前,我不知道有個金昌,到了金昌,到了金川公司,才知道金昌和金川的重要和珍貴,也才知道在離我生活的地方很遙遠、背景差異很大的西部的中心,有一座讓人難忘的新興的城市——金昌。
同樣難忘的是在金昌的那個下午,在一個會議室里,文友們相聚一堂,談著我們共同的話題:文學。在金昌談文學,和在江南談文學,背景是不一樣的,主題也可能不同,但是有一點感受是一樣的,那就是文友之間的心靈的溝通和精神的交流。一坐下來,面對著金昌的作家們,就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更有一種親切親密的感覺。我知道,我們都是奔著文學的夢來的,老話道,千年修得同船渡,而我們坐到一起,完全是因為文學之緣。因為文學,本來不可能相交的人生軌跡,卻意外地相交了,相交在金昌,相交在金色的秋天。
我生活的江南水鄉,到處是水的文化,是細膩柔和的,而在金昌作家和詩人的筆下,我看到了西部的蒼涼和陽剛。也許無法把陰柔與陽剛合二為一,甚至不可能互相的滲透,但是我走過了西部,走過了金昌,讀過了金昌作家詩人們的作品,我的靈魂被震撼了,我的精神更富有了,我的內心更充實了,我的人生也更多姿多彩了。這是毫無疑義的,這也是我要感謝金昌、感謝這個原先我曾一無所知的地方,感謝這里的文人,在這個金屬和沙土的世界里耕耘著文學的事業,在粗獷和堅硬的土地上,做著細膩的直入人心最深處的工作,就像鎳礦上的工人,他們開鑿出最美麗最珍貴的礦石。金昌的文人們,也用自己的筆,開掘著另一座富礦,給世人留下寶貴的西部精神產品。
東部的文人和西部的文人,在這里相遇,東部的文學和西部的文學,在這里交融,時間匆匆而過,大家意猶未盡,但畢竟留下了一份屬于我們的記憶,留下了一段美好的時光。
晚飯以后,微醺的我們,站在金昌的市中心廣場上,看著一張張親切的笑臉,一時間,似真似幻,以為是在自己的家鄉呢。其實這時候,家鄉還在數千里之外呢。)
9月16日
今天一天,幾乎都在路途奔波,經過兩個古絲綢之路的重鎮:張掖和酒泉。張掖有大佛寺,大佛寺里有大臥佛;酒泉有酒泉公園,酒泉公園里有酒泉。
皇帝圣旨: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陜西甘州臥佛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贊揚,上為國家祝厘,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諭。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李白詩: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
晚上看了看《絲綢之路圖》,回頭看看,我們從蘭州出發一路西行的足跡在哪里。
在酒泉遇見二十年前一起參加《人民文學》筆會的詩人林染,我已經記不起他來了,但是見了面,說起當年的事情,仍是添出了一份歲月匆匆的感受。
9月17日
西行的另一個重頭在今明兩天——去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這是在沙漠深處了,廣渺浩瀚,從進入基地的地界,到我們要抵達的10號(機關所在地),車就走了一個小時。劉慶貴副司令員親自給我們做導游,笑稱為全國級別最高的導游,負責宣傳的王艷梅干事,一路替我們拍照,還碰到兩個江蘇老鄉,是發射中心電視臺的,來采訪作家團。一問,原來是揚州人,我們的團長張健祖籍也是揚州,加上蘇州的我和常州的葛安榮,就有了五個江蘇人,老鄉見老鄉,格外親切,一起合影留念,背景就是高入云霄的發射塔。
劉司令員給我們說了六個“神”:神奇的土地,神奇的部隊,神圣的事業,神速的發展,創造了神話般的奇跡,建成了令人神往的航天城。這六個“神”字,高度概括了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近五十年的發展過程,在“地上不長草,天上不飛鳥,風吹石頭跑”的沙漠深處戈壁灘上,建成了一座展示我國軍事、經濟、科技等綜合國力的航天城,就是在這里,中華民族實現了自己的飛天夢。
9月18日
在首飛航天員住的問天閣看到楊利偉在2003年10月15日凌晨3點寫下“首飛航天員楊利偉”的字跡,內心深處再一次噴涌出對這位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興奮激動,心跳加速。而楊利偉之所以能夠成為“第一人”,恰恰是因為他的心跳正常,正常,永遠正常。了不起的心理素質,了不起的素質!
下午離開酒泉發射中心,直奔嘉峪關,路途中,馬虎中科長開始了他的個唱會,把大家樂得忘記了顛簸,也忘記了路途的遙遠。
在嘉峪關文聯的接待晚宴上,我記住了兩件事情,是文聯的李主席告訴我們的。一是文聯一年有四千元的經費;二是有一位業余的書法家,或者還稱不上是書法家,只是一個書法愛好者,他用四種小楷字體,抄寫了全部的《紅樓夢》,宣紙卷起來,幾十斤上百斤重。他的計劃是抄完全部的四大古典名著。可惜沒有記住他的名字。
在西部,在經濟不太發達的地區,基層文聯和作協的同志,就是憑著對文學對藝術的執著的追求,干著一份默默無聞的卻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不由又想起在武威的那天晚上,李學輝的那一躬,其實,我們都應該向李主席、向李學輝們再深深地鞠上一躬。
9月19日
西部讓我忘記了我的腰,但腰還是在的,數天奔波勞累,它的抗議又升級了,到天下雄關嘉峪關時,幾乎已經走不動了,但實在還是被雄關的氣勢折服,邊觀賞,邊贊嘆,邊拍照,結果被落下了,和同樣掉隊的葛安榮、趙劍云一起,還有武漢的董宏猷,他因為喜歡拍照,單獨行動的時間比較多,四個人追不上大部隊了,干脆在后面拖拖拉拉的,看了個夠,也拍了個夠。
中午在玉門鎮,王新軍和姜興中兩位文友請吃飯,也許是受了“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的詩句的影響,王、姜二位,尤其是王新軍,酒興大發,一一地輪流著敬大家,然后又被大家一一地輪流敬過,仍不過癮。我們因為前邊的路還長,不能耽擱太多時間,硬是狠著心腸撲滅掐斷了他的熱情,走的時候,看到王新軍和姜興中依依不舍地在車下向我們揮手,真是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在心頭。
下午經過橋灣古城,晚上到達此次西行的終點站:敦煌。
天已擦黑,抵達鳴沙山時,能在黃昏的光線下看到沙山的輪廓和山腳下成片成片的駱駝,好大的規模,好大的氣魄。我們已經沒有時間騎駱駝進山了,坐上現代化的電瓶車,進去的時候,恰好有一支駝隊出來,男男女女的游客,面上蒙著頭巾,露出疲憊但卻依然興奮的眼睛。我的腰已經在發出最后的警告,艱難地在沙地里跋涉了一陣,天馬上要黑下來的時候,來到了月牙泉。神奇的月牙泉,是被圍在沙山沙漠中的一泉清水,千百年來,鋪天蓋地的沙埋沒了多少生靈,卻偏偏埋不掉這一汪并不大的月牙泉,說是因為山貌的地理的原因,是角度的關系,但我更愿意相信,上蒼的惻隱之心,也眷顧了這一片荒漠。
9月20日
今天是西行的最后一天了。到蘭州是11號,已經過去了9天,似乎是在不知不覺中就這么快地過去了。出發的時候,擔心自己挺不下來,心情郁悶,現在看來,這擔心是多余的了。當然,也為自己產生出一點驕傲。董宏猷說,你是躺著進西部,站著回家去。我有同感,走過西部,讓自己的腰也挺了起來。
今天的項目也是此行最重要的項目之一:參觀莫高窟。
因為莫高窟太深奧太博大太沉重,使得我不能多說什么,我覺得我說不出來,我只能說出一句話:莫高窟為我們的西行畫上了一個足夠分量的圓滿的句號。
(注:所謂日記,并不是在路上的每一天里寫下的,只是一路寫在心里,回來后補記的。這只是一份流水賬,記下自己的感動,也記下西行中大大小小的一些事情。為不忘西部之行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