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彩》季大相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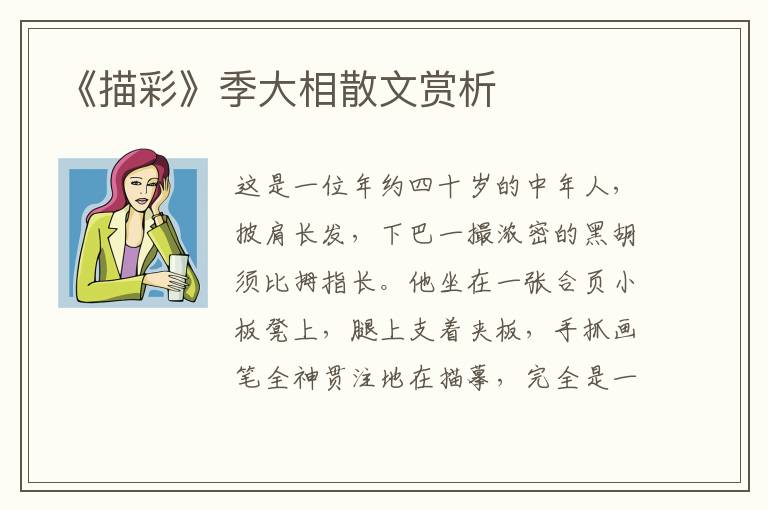
這是一位年約四十歲的中年人,披肩長發,下巴一撮濃密的黑胡須比拇指長。他坐在一張合頁小板凳上,腿上支著夾板,手抓畫筆全神貫注地在描摹,完全是一副藝術家的派頭。初見之下,以為是大畫家在寫生。
他手中的畫筆,左點右涂,卻是在給黑白照片描彩。
那是1992年秋的一個周末,我在京城的一條小胡同旁見到他。他聚精會神,目不斜視,旁若無人,揮舞著手中的畫筆,好像在創作巨幅作品,略作停頓的攪擾,便會打斷思路和靈感似的。可他面前,明明是一張黑白照片。
我和旁邊站著的幾個人一樣,與他素不相識。不同的是,其他人手里都抓著三五張黑白照片,等候他加工描彩。而我,純粹的是瞧熱鬧的看客。
一張黑白照片夾在夾板上面,照片上的一位十七八歲的姑娘,風姿綽約。旁邊是一位五十開外的大媽,我掃了一眼,判斷出照片上的姑娘就是那大媽的少女時代。他大腿的右側擺放一張小方桌,桌面上有序地碼放著一只只小碟子,碟子里是紅、黃、黑、綠等各色顏料,碟子邊沿還搭支小畫筆。看得出,他很講究運筆用色,絕不讓顏料混雜。
他一筆一畫,不時地挑換著畫筆,在臉頰上輕點幾下,原本黑白分明的臉蛋,瞬間變成紅撲撲的嬌柔羞態。格子襯衫上的碎花,紅綠相映,照片上的人,在他的筆下漸漸地生動起來。終于,他抬起頭,放下了手中的畫筆,將照片端詳了一番,面露一絲得意之色。那位大媽從他手中接過照片,兩眼立馬放光,帶電似的,猶如穿越時光隧道,一片紅暈涂抹雙頰,徜徉回少女時代,陶醉怡然。
大媽將照片包裹在一塊白色素凈的手帕里,再將手帕夾進一本舊書中間,小心地將書放進布質手拎包里,仿佛那不是一張舊照片,而是歲月靜好的風景佇留心房。她掏出一塊五毛錢遞給他,說:“謝謝畫家。”轉身離去。走出約二十米開外,她又停下腳步,從包里掏出書,從中取出手帕,一層層地打開,將照片托在手中仔細端詳,像是欣賞大明星玉照般虔誠。
“看把那老大媽美的。”有人沖著她的方向調侃,逗得大伙都笑起來。
朋友車子過來,載著我按預約去辦事。待我返回再次路過時,只有一位中年女士坐在他身旁的一只合頁小板凳上等候,盯著他面前夾板上的照片,嘴里嘀咕著,他一邊點頭,一邊揮筆涂抹,似在接受大考般莊重。
他的周邊,清靜了下來。
黑白照片在他的筆下,破繭成蝶,搖身一變成為華麗的彩照,變魔法般的神奇。我再次站在他的身側,畫板上的老照片斑駁陸離,頭部剝離掉一小半,衣服部位有幾個黃色斑點,殘缺不全。根據女士的描述,他運筆圍繞原線條勾勒,頭發、眉毛、衣襟……照片上的人慢慢地生動起來。
“媽媽,我媽媽就是這個模樣……”女士“霍”地站起身,端詳著照片,兩行清淚從面頰滾落。
那女士是客居京城的四川人,多年未回家鄉。前不久母親病故,只在家里找出這么一張殘缺的黑白照片,經他的描摹,母親的形象又栩栩如生地呈現在面前,這是心靈的救贖,更是一份親情的珍藏財富。“丹青圣手”、“妙手回春”等等的贊美之詞,現場送給他皆不為過。
那女士離開后,暫無客人。他站起身,舒展雙臂,活動筋骨。
他向我一笑,點下頭,主動地招呼:“您好!”
我忙不迭地回應,“您好!”
他并不像工作時那般刻板,且是位十分健談的人。通過簡單的交流,我得知他畢業于A省的一所美術學院,回家鄉當了四年中學美術老師,可他的理想是成為一名有所建樹的畫家。他報考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連續兩年皆以微弱差距名落孫山,成績卻遠超其他美術院校的錄取線。有人勸他務實一些,他卻索性辭掉工作,當起了“北漂”,自費參加某知名教授舉辦的晚間書畫高級提升班,積極備戰再考,終極目標鐵定為中央美術學院,他認為,在美術界要嶄露頭角,起點絕不能低。
“北漂”在京城,輔導費、租房費、生活費等等,支出龐大,很快便面臨經濟窘迫的狀況。他無法向家人開口,唯自食其力,初始靠打零工補貼費用。一次,一工友拿出張黑白照片,說照片上的女人是自己的妻子,是家鄉有名的大美人。可惜,黑白照片難顯風采。他接過照片看了看,說我給照片描彩。工友將信將疑,反正就是一張照片,讓他折騰去,等著戳破他的“牛皮”。他看出一群工友“壞壞”的笑,并沒多言,同樣報以一笑。
第二天上班,他將照片遞到那位工友手中,一瞧之下,工友驚呼起來,“出神人了……”把工地上的人嚇了一跳,以為其神經出毛病了。不過,待看過經他描彩后的照片,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出兩個字“神了”。大家瞅他的眼光,滿含敬佩之色。
此后,又陸續有工友拿來陳舊的黑白老照片請他描彩。再后來,工友們勸他去擺攤,給黑白老照片描彩,不要在工地上枉費了一身神技。他笑笑,對他來說,給照片描彩只是小兒科的技法。不過,他接受了大伙的建議,攜帶一套繪畫的工具,經營起給黑白照片描彩的行當。那幫工友真給力,通過各種途徑找來黑白老照片,讓他描彩,幫他吆喝宣傳,漸漸地,他給照片描彩的名聲傳出去,來找他描彩的人漸漸地多起來。有的人偶然路過見他給照片描彩,亦怦然心動,下次再來時,手里便會多出幾張黑白老照片。京城太大,人員流動太頻繁,有做不完的生意資源。
他不但在原有的基礎上描彩,還會主動征求顧客的意見,依據老照片的環境,運用技巧添加上山水、花草、小動物之類的背景,自然諧和,更具立體感。他的收入,是做工的幾倍,維持支出綽綽有余。
因為工作關系,我多次路過他擺攤的那條小胡同,先后幾次與他作了簡短的交流,彼此很投緣。我試探性地詢問他姓名,他只是笑笑。有一次他主動告訴我,又要考試了,如果順利的話,他會與我交換聯系方式的,言下之意,姓甚名誰屆時揭曉。如此相約,也是他激勵自己的一種方式吧。
后來,我因工作調動,走得匆忙,未能去與他道別,從此失去了音信。
時光一晃,二十余年過去了,不知他當年是否如愿踏入了中央美術學院殿堂,前途是否順暢?也不知中國當代知名書畫家的群體里,有沒有他的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