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曼《川北院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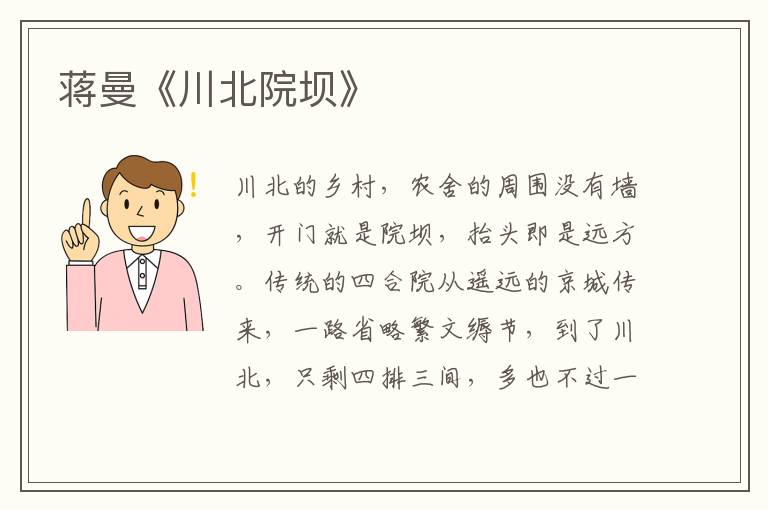
川北的鄉村,農舍的周圍沒有墻,開門就是院壩,抬頭即是遠方。傳統的四合院從遙遠的京城傳來,一路省略繁文縟節,到了川北,只剩四排三間,多也不過一兩間耳房,院落和天井也省去了,只剩下院壩——平整空蕩。
院壩不是院落,院落與院落相連,不過是高墻林立,庭院深深深幾許,深的不僅是庭院,更是連接它們的小巷。院壩與院壩相連,則是大大小小,寬寬窄窄的通衢。院落是嚴肅的防御,院壩是真誠的邀請,是率性的展示,信任和接納。一舍一戶,一戶一壩,戶戶相挨,也就壩壩相連,村子還沒有公共道路的時候,院壩就是馬路,一路走過來,雨天腳不會沾上泥。
在云南、甘肅、河北、浙江,無論是高原或平原,山地或水鄉,高墻大門是院落的標配。在墻與墻的對峙中,有了幽深的小巷和寬寬窄窄的街道。就是深山中孤獨的院落,也在柴扉與籬笆中沉默地表達著拒絕和不容打擾。川北的院壩,如此坦白直率,沒有圍墻,連籬笆也沒有,即使三五家聚集而起,各有各的院壩,你從我的院壩邊抄近路,我的雞鴨時常到你家院壩里散步啄食。這種對隱秘的犧牲以及對安全防御的淡漠讓人好奇。
是因為我們的山太多嗎?小山也是山呀。云太多嗎?日光稀少,蜀犬也吠日,不是見識少,是連狗都會雀躍的歡喜,人會不知道?川北的農舍,圖的就是一個敞闊和亮堂。推門即見山水,見云霞,見莊稼,見天地眾生,方覺心里踏實。坐北朝南也好,坐西朝東也好,院壩和屋門一定要向著陽光。陰沉的日子太多,人們不想再看到墻的陰影。
以前,院壩用青石板一塊一塊拼出來的,現在是清一色的水泥地:晴天不起塵,雨天不粘泥。院壩的四周種菜、種樹,種點閑花,草自會見縫插針地長。樹有大有小,葉茂的站外邊,樹小的靠廂房。竹林常在院壩外的土坎上,路從中蜿蜒而來,跨過排水溝上的青石板,幾個大步,人就到了院壩中央。狗照例要叫幾聲,雞側著頭無所事事地張望。房門上了鎖,來的人和狗說幾句就走了;廚房敞著門,就對著院壩四周喊幾嗓子,菜園里、豬圈旁、屋后山坡上,就有人站出來答應,一邊教訓著狗,一邊招呼著客。人一站到院壩里了,人就是客,甭管認不認識,客總是要招呼的:一口茶,一根煙,一雙筷子而已。鄉下人守著院壩大的天,路過的人都是讓人心生疼惜的游子,“不容易喲,不容易喲,走到我們這鄉壩頭了,再忙,也要歇個腳,喝口水呀。”
“小扣柴扉久不開”是院落的禮儀,在我們的院壩里,只需左一嗓,右一嗓,隔著河溝都能聽到。當然也有是非口角:你的狗攆了我家的雞,我的貓蹭掉了你家的瓦,夫妻吵嘴,娃兒打架,喁喁,竊竊的私房話,都在院壩里高高低低地響,痛快淋漓,潑辣而鏗鏘。
院壩是客廳,接人待物,親近厚道。院壩也是寬綽的工作間,一年四季的活計,都可以在院壩里做,屋是用來安放疲憊和困倦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作在院壩里,息在房屋中。活計好多,疲憊很少,所以院壩好大,屋舍很小。
院壩里,常年是打谷曬糧,曬各種各樣,雜七雜八的物件,是一種古老的祈福與炫耀,讓賞飯的老天爺看看莊稼人的勤勞。女人在暖日的下午,仰仗著那明亮,暖和得剛好的日光,縫補漿洗;小孩子的作業也在院壩里做完,風來的時候,剛好翻過一頁,讓人歡喜的巧。
砍回來的青竹,橫在院壩里,剖成長長短短的竹片,再劃成細長柔軟的篾條,竹片在懷里穩穩當當各守一方,篾條在手中騰挪,一個筐,一個籃,筲箕,簸箕,源源不斷。
熱鬧是大家的熱鬧,忙碌是一起的忙碌。你忙著曬包谷,我趕著洗紅苕,彼此提醒著。一家人的活計總有忙不過來的時候,鄰里之間常常要搭把手:我剛上房翻瓦,你就能從院壩那頭跑過來扶梯子。這樣互相依傍的勞作非要在院壩里才自然通暢。
生老病死,院壩也能承擔這樣莊重的交接:十八臺的花轎要落地,紅漆黑漆的壽木要上山,嬰兒的第一盆洗澡水,過年過節鞭炮的銳響。院壩托著鄉下人的生活,堅實又穩定。
我喜歡從一個又一個的院壩前經過,看他們的狗茫然地起身,威武地亂叫,看他們的人自由的忙碌,在院壩里一個轉身,又一個轉身。冬天燒一堆柴火,夏天候幾襲涼風,春天桃花寂寞地落下,秋天里,橫七豎八的孩子躺著看月亮。川北的院壩,習慣這樣安放人間的繁雜與斑駁——光明正大的瑣碎,坦蕩率直的哀樂。平平整整,井井有條。
作者簡介:蔣曼,女,1975年出生,四川省南充市順慶人,熱愛閱讀和寫作,默默生活,堅持創作。近年來已在《羊城晚報》《短篇小說》《華西都市報》《工人日報》《天池小小說》《長春日報》《教師報》等國家級、省市級報刊上發表小小說、散文、隨筆上百篇。《留守鄉村的爺爺》被廣西賀州選入2017年中考試題,部份作品被《讀者·校園版》《故事會》《課外閱讀》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