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常《我的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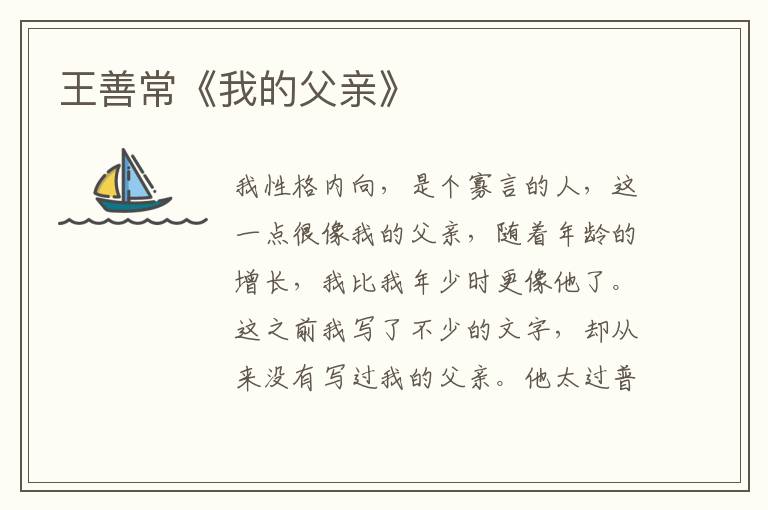
我性格內向,是個寡言的人,這一點很像我的父親,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比我年少時更像他了。
這之前我寫了不少的文字,卻從來沒有寫過我的父親。他太過普通,普通得像浮塵中的一粒灰塵,甚至不值得用文字去記錄他的言行事跡。
父親是一個苦命的人,他一生遭受了太多的磨難,對生活只有招架之功。他的身體曾經堅硬如鐵,硬過鐮刀,硬過鋤頭,硬過犁鏵,卻始終硬不過命運。到今天他已經七十一歲了,早已放棄了對命運的抵抗,頭發白了,腰彎了,臉上布滿了皺紋。他的表情是麻木的、謙卑的,帶著一絲歲月積存下來的苦味,我知道,那其實是對命運的服帖。
我祖父去世得早,他剛剛三十多歲就被疾病和苦難硬生生地拖離了人世。那時父親只有十六歲。十六歲在現在來說還是一個孩子,但那時他卻已經是一個男人了。因為我的祖母身體不好,又加之我父親的身下還有四個未成年的弟妹,因此父親別無選擇,必須義無反顧地接過祖父丟下的生活重擔,壓在自己稚嫩的肩上,咬著牙繼續前行。
祖父去世的第二年,父親為了多掙些工分,毅然決然地跟隨著生產隊里的許多大人,一起去了遙遠的地方,成了一名修鐵路的民工。當時正是初冬,天冷得要命,時常會下起雨夾雪。鐵路要在一片沼澤地里穿過。由于要搶工期,所以不等泥土凍實,筑路人就開工了。父親每天都要在刺骨的泥水中工作十多個小時,鞋和褲子都濕透了,腳和腿被凍得常常是麻木得不知道疼痛,再加之晚上民工住的又是沒有任何取暖措施的簡易工棚,所以父親竟落下了嚴重的風濕病。直到現在,父親走路時還是直不起腰,而且一到陰雨天氣就腰酸腿疼得下不了炕。
父親是地地道道的農民,一生與土地和莊稼為伴,他的時間有一大半都被玉米田吞噬掉了。我以前一直以為他把土地和莊稼當成了他更親的親人,甚至超過了他的妻子和三個兒子。我能模糊地記起童年的事。他很早就要下地,走的時候我們還沒有醒;他晚上回來的時候月亮已經升上了天空,我們兄弟三個也都睡著了。但我知道,他每天早晨走的時候都會挨個地摸摸我們的頭,從大哥的頭摸起,然后是我,最后是我的三弟。他回來的時候也會這樣摸我們,從三弟的頭摸起,然后是我,最后是睡在炕梢的大哥。他摸完我們,就默無聲息地接過母親遞給他的飯碗,坐在黑暗里吃飯。我睜著迷糊的睡眼,卻看不見他的身影,只能聽見他吃飯的聲音,像從遙遠的過去傳來的一樣。
由于活太忙,父親中午很少回家吃飯,莊稼一個勁地瘋長,絆住了他的腳。他在無邊無際的玉米地里干了一上午,又干了一下午。每天中午都是母親將飯送到地里。我十一歲的時候獨自給他送過飯。他也許太累太餓了,躺在地壟溝里,頭枕著鋤把,身上全是玉米蔥郁的綠色。一只螞蟻把他當成了土地,從他的褲腳往上爬,一直爬到了他的臉上,他卻渾然不知。
父親只上過幾天學,不識幾個字,勉強能歪歪扭扭地寫出自己的名字。沒有文化在他的一生中是最大的遺憾。他知道,只有讀書才能扭轉家庭的命運,因此對我們的學業就要求得分外嚴厲。記得小時候,我和弟弟逃學去山里玩耍被他知道了,他很氣憤,罰我倆跪在地上,并且把我倆的每個膝蓋下面都放了一塊帶有棱角的小石子。他警告我倆不準起來,然后就去了地里。等他走后,我和弟弟相互一使眼色,爬起來又去玩了。等到晚上,他要回來的時候,我倆又重新跪在了地上。父親看見我倆依舊跪著,心中十分不忍,問我倆以后還逃不逃學了。我和弟弟異口同聲地說不敢了,于是他就叫我倆起來。他綰起了我倆的褲腿,用粗糙的大手摩挲著我倆的膝蓋。我看見他眼中隱約閃著淚光,可是我和弟弟當時只是為成功地欺騙了他而暗自高興,其他的什么都沒有多想。
我小時候喜歡畫畫,在廢紙上畫出來的東西常被村里的大人夸獎。一次村里來了一個畫匠,能用油彩在立柜和被櫥上的玻璃上畫出各種花鳥山水。畫一塊玻璃五塊錢,他一天能畫出十幾塊。父親知道后就跑去問他,想讓他收我做徒弟。畫匠當然沒有同意,只告訴父親說市里的青少年宮有一個美術班,教畫畫的張老師水平很高,如果能去市里跟他學,一定能學到真東西。父親于是下了決心,把我送到了市里的青少年宮。市里離我家很遠,每天只通四趟客車,車票四毛錢。但我那時很不懂事,嘴又太饞,總是曠課在街上玩耍,有時甚至抵擋不住美食的誘惑,把車票錢買了零食。有一次我花兩毛錢買了一根麻花,吃完后車票錢就不夠了,我于是不得不獨自步行往家走。路途太遠,我又記不太清道,最后累得躺在了一個水泥管子里睡著了。那天父親發動了許多村里人找我,直到半夜才把我找到。我免不了挨了他的一通巴掌,從此也不再學習美術了。那之后許多年,父親一提起這事還很愧疚,似乎沒把我培養成為一個畫家是他的過錯一樣。
父親木訥而不善言辭,但我知道他是心腸最好的人。有一年,我家的一個鄰居因為生活的逼迫,不得不搬家到別處去。但他家卻窮得連路費都沒有,于是苦著臉,央求父親給他作擔保借些路費錢,并發誓過一個月就回來還錢。我父親當時就相信了他的話,于是給他擔保借了一千塊錢。可是后來這個鄰居卻一直不曾回來,且一點音信都沒有。最后債主還是上門來了。每天債主都是晚上來,我趴在被窩里,聽著債主用嚴厲的口氣數落著父親,而父親卻總是憋紅了臉一言不發。最后,父親終于是拿出了家里僅有的一點錢,又變賣了兩頭豬才把錢還上。父親還不知道被騙,他常說這人不是沒良心的啊,他一定會回來還錢的,八成現在他太困難了吧?我的父親就是這樣地有著一副善良而愚昧的心腸。
父親雖然一生簡樸勤勞,但我家的生活還是十分拮據。那時候親友們的生活大都過得比我家強,所以他們都不愿意和我家來往,唯恐沾了我家的窮氣,更怕父親張口管他們借錢,但父親從不巴結他們。他說人再窮也不能窮志氣。無論在我家多困難的時候,父親都沒有向親友們借過一分錢。
一次我的三爺過六十大壽,父親本是同輩中的老大,因此他就和其他同輩人坐在了我三爺哪一張桌上,但他剛一坐下,我的三爺就說話了,他板著臉說,你也不會喝酒,就去別的桌吧。當時父親半天沒有說出話來,他最后悻悻地離開了飯桌,回到了家里。他越想越覺得憋屈,這哪里是因為不會喝酒,分明是自己太窮的緣故啊!于是他竟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了一瓶白酒,從來滴酒不沾的他一仰脖咕咚咚全喝了下去,然后他就大醉了。他躺在炕上,淌著眼淚和鼻涕不停地重復一句話:“誰說我不會喝酒?誰說我不會喝酒?”親友們勸了他一會,可他還是不消停,最后親友們似乎都怨他多事,是小題大做,就又都到二爺家喝酒去了。那天我聽見父親不停地在炕上用哭腔重復著那一句話,誰說我不會喝酒?誰說我不會喝酒?
父親六十歲時,還在不停地為生計奔忙。那年,他在菜園子里種了許多蔬菜,每天都要起大早用自行車馱著到城里去賣。有一天在回來的途中,剛一拐彎,他就被一輛飛馳而來的小轎車刮到了裝蔬菜的竹框,自行車一下子被甩出了很遠,他摔在了地上。車上下來了好幾個人,他們先是查看自己的車有沒有刮傷,然后才來到父親身邊,訓斥父親說你會不會騎車子,你沒看見我們的車啊?你就拐彎?父親似乎覺得自己很是理虧,就急忙爬起來,連聲賠不是,很怕被人家訛去了錢財。然而圍觀的人不愿意了,許多人都譴責司機,司機最后只好問父親用不用去醫院檢查檢查。當時父親試著甩了甩胳膊,踢了踢腿,雖然有些疼痛,但似乎也不礙事,于是就連聲說不用。于是那幾個人就上了車,揚塵而去。圍觀的人很是氣憤,紛紛責備父親的膽小怕事,父親卻說,沒被人訛上就萬幸了。那次父親回來后竟一連臥床一個多月沒有起來,其實車禍當時就傷了筋骨,只是他沒有感覺到。我們埋怨父親為什么沒有叫他們看病。父親說人家有錢有勢,最后吃虧的一定是咱們。我那膽小怕事的父親,就這樣自己獨自承受了傷痛的折磨。
父親越來越老了,也越來越固執了,他執拗著不肯離開村莊一步。他像其他所有的老人一樣,雙腳已經在村莊里扎了根,血脈已經與村莊相連。他們就是整個村莊的心,被包在了村莊的深處。
這些年父親忽然開始信仰了耶穌。他篤信只要信了耶穌,死后就可以免下地獄,升入天堂。他戴著老花鏡,每天起早貪黑地捧著一本圣經看。他之前并不認識幾個字,但現在卻能把《圣經》通讀下來,這令我十分驚嘆。我總希望父親的心再虔誠些,更希望在我們的頭上真的有一個天堂,這樣,在父親把人生之路走完的時候,就能灑脫地切斷對我們的牽掛,徹底地忘記塵世給他帶來過的磨難,輕松地進入一個令他愉悅的世界。
作者簡介:王善常,男,黑龍江作協會員,作品見于《北方文學》《延河》《廣西文學》《連云港文學》《佛山文藝》《北方作家》《遼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