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亞龍《遙望敦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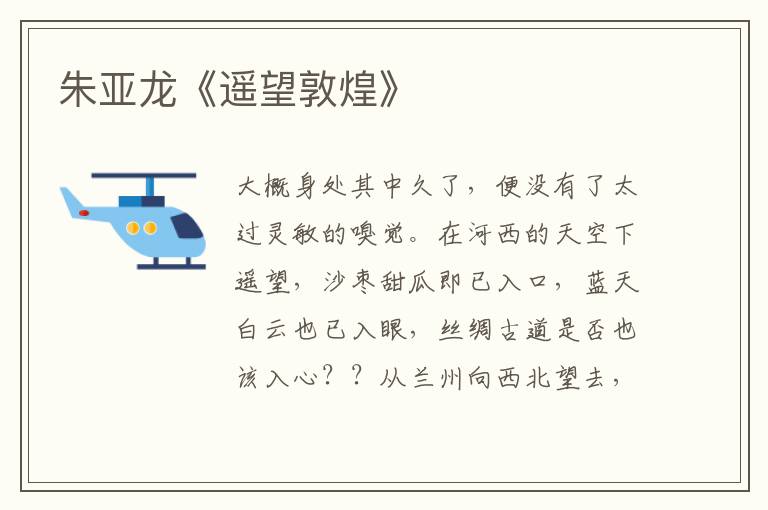
大概身處其中久了,便沒有了太過靈敏的嗅覺。在河西的天空下遙望,沙棗甜瓜即已入口,藍天白云也已入眼,絲綢古道是否也該入心??
從蘭州向西北望去,用李白的眼光遙望:青海長云暗雪山,一片孤城玉門關。四下再望,鳴沙山金光照耀。似乎是一種安排,讓我長久的生活在祖國的西部,讓我離他近一點,好看的清楚一些,但又不要太近,好保持一點距離,好產生一點美。向西北望去,用目光丈量,敦煌不遠,三百公里,驅車不到半日,但我卻很少去過。僅有的兩次敦煌之行,也是行色匆匆。大多與敦煌的情愫,都是想象著那兩次的打馬而過,那兩次的欲語還休中開始的。
我站在三百公里之外的河西古郡,對敦煌久遠的追述沒有停止。作為河西走廊上的土著居民,與敦煌的交談,始終保持著必要的距離和姿態:遙望敦煌。
向西北望去,遙遠的時空傳來英雄無奈的嘆息。自秦始皇修長城開始,到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衛青霍去病北擊匈奴,唐宋元明清歷朝歷代,南北方的相互攻伐從未停止過。戰爭不止,身居中原的統治者面朝西北遙望的決心不止,國家成一統,西出玉門關成了他們不變的志向。中原的老百姓,沒有停止過面向西北的遙望,駐守西北邊疆的戰士中有他們的兒子、丈夫與父親。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是擔憂也是等待,鏤刻在老百姓的心中。中原的士大夫們,更沒有放下過對西北邊塞長久的遙望。蘇東坡西北遙望,欲射天狼;辛棄疾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聲;陸游垂死病中驚坐起,鐵馬冰河入夢來。是的,西北望,望的是君王政客們山河一統的千秋功業;西北望,望的是普通百姓們合家團聚的迫切等待。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遙遠的西北遼闊之外只剩蒼茫,時空因此而聚集到一個焦點,所有的家國情懷、所有的金戈鐵馬、所有的英雄意氣、所有的離愁別緒,都指向那個蒼茫的西北,蒼茫的敦煌。遙望敦煌,我看到氣脈嘯聚,蒼茫天地間升騰起大氣魄。
面向西北,似乎成了幾千年來中國人永恒的身姿。遙望敦煌,遙望本身就成了華夏民族心中持久的牽絆。
我在敦煌毗鄰的小城玉門蟄居多年。如實的說,很多次把遙望的目光,都投向了煙花三月下揚州,投向了斜暉脈脈水悠悠,投向了舊時王謝堂前燕,投向了滿眼風光北固樓。太多的目光交匯在南方濕漉漉的氣息里,交匯在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的江南美景里。我遙望著一種自身不曾身處的環境,不能涉足的疆域。作為北方人,向往大海多于大山,這應該是人之常情吧,多少年來,卻忽視了身后的美景,錯過了身邊的繁華。
隨著成長,踏過了西湖的婉轉蘇堤,領略了秦淮的槳聲燈影,聽完金陵的軟語輕靈,甚至,感受一遍京華煙云的厚重與動蕩。之后,我才忽的回過頭,發現,還有一處世界的敦煌,文化的圣殿就在我的身后。我何須跋山涉水踏上遠方呢?是啊,那些地方山水俱佳,處處流淌著自然景致與人文景觀相互交融的妙趣,然而敦煌,那個吸引了千里之外、他鄉異國游客的敦煌,正在我的身后,默默的守望。
似乎是召喚。我尋聲向西望去,依然是我熟悉的時空。第一次走向敦煌,仍然被他宏闊的氣勢折服。我站在鳴沙山腳下,玄黃天地一色,熱浪滾滾,沙山連綿而有氣韻,完全是身處在了另一個時空維度,這對一個土生土長的西北人來說實在難得。這不是我所見所聞的日常感受嗎?因何還會有一種闖入異邦他域的感覺呢?
是啊,敦煌的風來的太酣暢了。這雖然也是西北的風,西北的陽光,卻只有身臨其境的去感受,才會知道,這風和光只有敦煌才有。如果將西北的風比作塞北秋風的話,那敦煌的風就是天地玄風。怎么說是天地玄風呢?當你赤腳向鳴沙山高處攀登時,這風時而旋急緊迫,掀起女游客長長的裙擺就消失不見;時而絲絲縷縷,如沐春風夏露,愜意涼爽;時而昏天暗地的卷來,像劍客舞劍、張揚肆姿、劍招之間密不透風,這種變換之間毫無轉折,切換自如,讓人感覺玄而又玄。
而敦煌的光來的坦蕩,毫無保留,毫不遮遮掩掩,像君子、像漢子。置身在敦煌的光里,渾身的細胞好像被激活,他熱辣的撲向你的全身,內心久積的陰霾瞬間蒸發,恍惚間,神清氣爽,整個人都像河西的天空,燦爛透明,也像腳下的黃沙那樣灼熱潔凈。
當你酣暢淋漓的爬上鳴沙山的峰頂,放眼望去,月牙泉正躺在山腳,身姿柔媚、波光漣漪,千年以來,泉水不絕,周身又有綠樹環抱,古跡樓閣蹺繞其間。你再看看這月牙泉周圍連綿的沙山,隨風游動,隨物賦形,而地處群山環抱的月牙泉,竟能長久的在這里波光繾綣,與鳴沙山千年守望,相互點綴。相攜相映,相互成輝,世間恩愛的情侶也無過于此了吧。這真是大自然創造的奇跡。
遙望敦煌,我們再來循著時間的經緯一眼望去。
漢武帝的漢帝國經高祖、文景幾代皇帝接力賽一樣的精心建造,已初具規模,正走向鼎盛。此時的帝國仍然累受匈奴的騷擾,屈辱地和著親。每年,照例送去大量的財物和美女。
在漢武帝年幼的記憶里,漂亮的漢朝公主帶著幽怨的神情離開長安。遠嫁塞北荒蠻之地時,他就已經學會了遙望。長安的宮墻層羅密布,接向天邊,而天邊的天邊,就是敦煌。漢武帝成年獨掌權柄后,他第一次看到漢帝國疆域的全圖,就發現了敦煌。是的,那是他魂牽夢縈之地。他突然間冒出一個想法,派人穿過這里,打通敦煌之外廣闊的西域之地,聯合他們共同抗擊匈奴。這是宏闊的戰略家眼光,歷史證明了他此舉的英明,不止實現了南北夾擊匈奴的目的,更讓他始料未及的是,從此打通了中原通往中亞、歐洲、北非的通道,讓世界因為這條路連通起來了。
張騫的鑿空之舉使后來亞非歐大陸互通有無,走出了一條舉世矚目、千年不絕的“絲綢之路”,史書載此盛況曰:“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如果說孔子的出現讓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指路明燈的話,絲綢之路的開鑿,則徹底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和胸襟,讓他們意識到世界的廣闊遠非之前所理解的那樣。
中國人在歷經了上千年獨立于世界之外自成體系的發展與輝煌之后,與世界的文明聯系起來了,中華文明成為了世界文明的一支,并深刻的影響了世界文明。
此時的世界版圖中同時樹立著幾大文明相互輝映的格局。地中海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印度文明以及古羅馬文明,這五大文明之間相互走動起來了。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糖、蠶絲、紙張、銅、明礬、金銀、絲制品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出敦煌,走向非洲、歐洲,傳向其他幾大文明。其他文明經大秦,進西域,到敦煌,將棉花、羊毛及制品、鐵、鉛鋅、鉆石、雕像、珊瑚、琥珀、魚翅、珍珠、米等商品傳到長安。于是,五大文明終于在敦煌,交融交匯了。這是前所未有的盛況,敦煌成了當時少有的會萬邦使臣于城下的國際大都會。翻遍世界史籍,有此盛況的地方,敦煌之外,再無其他。
遙望敦煌,我知道,在我西望的同時,全世界的目光或向南望,或向北望,但焦點,都是望向敦煌的。距今一千七百年的樂僔和尚不遠萬里,朝西而來,他像神話傳說中的夸父一樣,追逐太陽西落的盡頭。在古人心中,敦煌算是西境之極了吧。莫非晝伏夜沉的太陽,就在這兒早出晚歸,按時起落,主宰人間宇宙、四季昏晨?樂僔和尚終于走到了敦煌的三危山。我猜想正是某個八月的正午,陽光盛極,大地之上黃沙漫卷,天地一色,陽光和沙礫相互投射、反照之下,三危山中一派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的如夢似幻之感。接下來不管是海市蜃樓也好,還是萬丈佛光也罷,都是可以想見的了。
片刻清醒,陽光西斜,紅彤彤一片火燒云掛在西空又西。樂僔和尚如有所悟,雙手合十,閉眼默誦,當即發下宏愿,要在這里開鑿佛窟。在修行的和尚看來,這是佛的暗示,這里盛產了一種大光明,這是佛陀永恒的國度。
神話往往不乏后人傳誦。經歷代不斷的開鑿修建,洞窟不斷增多,到七世紀唐朝時,莫高窟已有一千多個佛洞了。“千佛洞”在唐朝時就已經形成了。唐朝,正是這三危山上正午的太陽,一種宏大文明的形成,正趕上了一個最鼎盛的王朝,這似乎是歷史的呼應。
后世因一部《西游記》家喻戶曉的玄奘法師在長安的夜空中遙望。他一定將目光長久的停留在敦煌上空的月亮上。這是中原版圖最后的驛站,也是西來東土的前哨。他在這月亮的倒影中看到了將要踏上的西行路途。這路途的兇險,但凡心中有一絲游移不定,都行不通。他甚至看到了鳴沙山上死神的光顧,在極度的干渴中,望著周邊無跡的沙漠,絕望漫頂。恍惚中他看到佛光閃爍之處雨露瓢潑而下,絕處逢生后定然如有所悟。這一份西行的執著與普度眾生的悲憫之心定然能得佛祖庇護吧,還有什么能阻止他萬里的求佛之路呢?玄奘不那么怕了,如果說他曾經對此行還有猶疑和怯懦的話,想到這些,他就變得堅定無比了。
于是,他辭別了孟郊一日看盡的長安花,辭別了故土。從此八千里路云和月,寂寞西途十七載。就這樣,上路吧!
東來西往、起點終點、商旅駝隊、烈車戰馬、將軍文士、貶官逐臣,他們的腳印與敦煌的駝印逐漸重合,他們的靈魂在敦煌上空的皓月上互訴衷腸。王維說西出陽關無故人。無故人又何妨呢,且把他鄉當故鄉,同是天涯淪落人。分什么故人他人、故鄉他鄉呢?在敦煌、在塞外,有緣相見即是親人,擦肩而過都是鄰里。天涯若比鄰,說的不正是此時此地、此情此景嗎?包羅萬象、兼容并收,這是敦煌容納吸收的精華所在。
千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敦煌的輝煌與苦難在一次次的興佛滅佛中經歷波折。終于,敦煌隱匿了自身巨大的文化氣象,暗藏在一個叫王圓箓道士襤褸的道袍中。古老的敦煌神情黯然、疲態盡顯。在八國聯軍洗劫了中華民族的國都北京城,毀壞了圓明園后,終于,一個叫斯坦因的匈牙利考古學者造訪了敦煌。大廈將傾,獨夫何為?斯坦因連哄帶騙的從王道士手中竊取了大量莫高窟中的經卷、壁畫、佛像……。
有人說,是王道士發現了莫高窟,也毀了莫高窟。是的,有“人類文化史上的珠穆朗瑪峰”之稱的莫高窟,區區一個窮道士說毀就能毀掉?也有人說敦煌壁畫與唐經正是由于斯坦因在歐洲的研究、出版、傳播、弘揚,才讓它的光芒照耀世界的?
塞翁失馬,焉知福禍。敦煌學散布全世界,吸引了無數才華橫溢的頭腦為其奉獻一生,真是因禍得福呀。
“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見王道士轉過臉來,滿眼困惑不解。”余秋雨先生憤怒的站在莫高窟的門口,仇視著王道士和列強的無恥。“斷臂的維納斯才是最美的維納斯,因為其殘缺。失盜的敦煌才是完美的敦煌,因為她是人類的敦煌。”徐兆壽先生則不住的搖頭,若有所思。
遙望敦煌,不管歷史如何喧囂,圍繞世界文化圣地敦煌的討論將永無休止。今天,在中華民族重提復興,重鑄中國夢的時刻,敦煌已經做好了準備,拾起了往日的榮光與輝煌。遙望敦煌,世界遙望的目光,將重新匯聚于古老的敦煌、新生的敦煌、未來的敦煌、人類的敦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