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麗娜《重陽菊色勝春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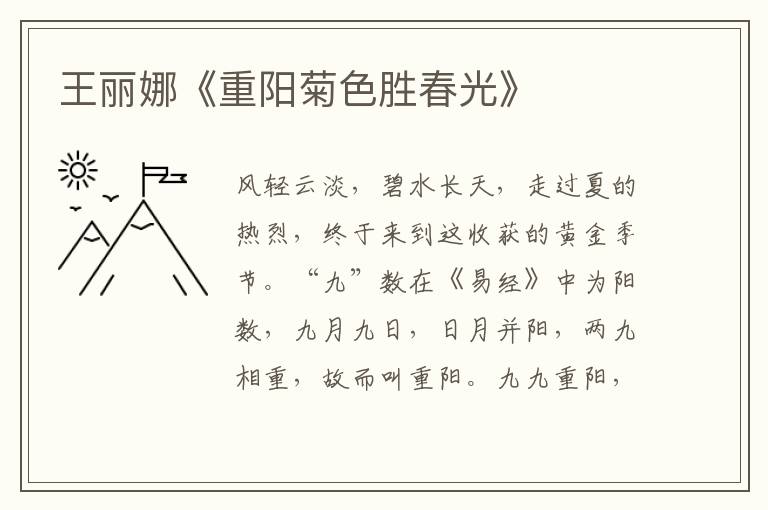
風輕云淡,碧水長天,走過夏的熱烈,終于來到這收獲的黃金季節。“九”數在《易經》中為陽數,九月九日,日月并陽,兩九相重,故而叫重陽。九九重陽,與“久久”同音,九在數字中又是最大數,寓意長久長壽,古人認為是個值得慶賀的吉利日子,這個節日便很早就確立了。
重陽遇上詩詞,充滿著絢麗的色彩。三國時,魏文帝曹丕《九日與鐘繇書》中曾這樣描述當時的重陽節:“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并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魏晉之時,節日氣氛漸濃,菊花和酒見之于文。唐朝賞菊已成氣候,孟浩然在《過故人莊》中寫道:“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重陽那天,文人墨客吟詩作賦,不吝筆墨。他們在重陽節登高望遠,暢享清氣,他們對詩詞一往情深,他們對菊花獨具青眼。“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那是對自己漂泊在外的感觸,“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
秋山無限,賞菊品酒,重陽節頭戴菊花的風俗從唐代開始流行,在宋代盛行。黃庭堅有詞云“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白發簪花不解愁。”菊花之愛,可謂眾矣。
詩詞里的菊花,含蓄優雅,小說中的菊花,描繪備至。《水滸傳》其中第七十一回寫重陽節菊花會:“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會眾兄弟同賞菊花,喚做菊花之會……忠義堂上遍插菊花,各依次坐,分頭把盞。”書中所說的遍插菊花,也指的是鬢邊插菊花,后文中宋江在席上就做了首《滿江紅》詞中就有兩句“頭上盡教添白發,鬢邊不可無黃菊。”于是簪菊習俗在此篇回合中,和黃庭堅的詞相互有了印證。
重陽與菊花是絕配,不僅簪菊,人們還會飲菊花酒。《夢粱錄》說:“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飲之,蓋茱萸名‘辟邪翁’,菊花為‘延壽客’”,飲此酒旨在驅穢逐惡,延年益壽。那時候釀酒,菊花方才含苞待放,人們便將花蕾莖葉盡數采摘下來,和黍米一起釀制,等到第二年九月初九重陽節的時候才開壇飲用。菊花在一年中醞釀著清冽心事,在秋日冷霜中開放,氣味芬芳,豈止佳釀,也是瓊漿,是延年益壽的佳品。
正因世人在重陽那天對菊花的偏好,李白不禁要為菊花抱不平,“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即便如此,菊花情懷,不為俗世所累,燦然傲立,滿院馨香彌漫。它那昂首的姿態,任憑風霜肆虐,總是將這份美好展現在人們眼前。
重陽這一天,游子若能歸家,洗去滾滾紅塵,與父母一同分享這大半年的忙碌與收獲,共飲菊花酒,同食重陽糕,那么是這個敬老節最好的禮物。如果在外,現在的通信科技如此發達,一聲問候,言語可親,一次視頻,面容可親,也是一份安慰。人雖千里外,菊花兩地同。
在大地寫上色彩斑斕,菊花是天地對人們的饋贈,向金風舉觴,聽冬天近了來時的腳步,不妨沉醉,不妨酣暢。歲歲重陽,菊色霜華,每年不負此約,年年勝似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