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地上》趙宏興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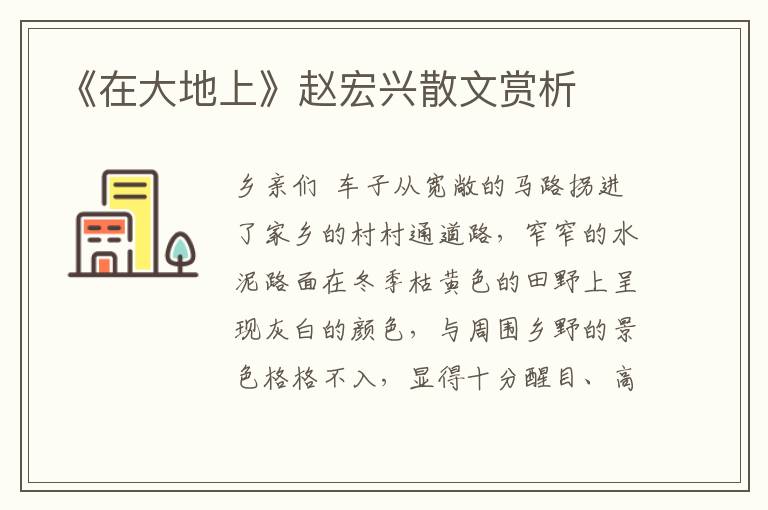
鄉親們
車子從寬敞的馬路拐進了家鄉的村村通道路,窄窄的水泥路面在冬季枯黃色的田野上呈現灰白的顏色,與周圍鄉野的景色格格不入,顯得十分醒目、高貴。路的兩邊是白楊樹林,現在白楊樹落光了葉子,光禿禿的枝頭密密地排列在半空中,一輪彤紅的夕陽在密密的枝頭隨著車子快速地移動。
路過兩個村莊,就到家鄉了。在家門前停下,只見幾個小侄子蹲在門口下象棋,我們一下車,他們停了下來,起身迎接我們。
進到屋子,沒有看到母親,以往這個時候,總是母親最先笑哈哈地出來迎我。我問母親去哪里了,父親說可能挖薺菜去了。過了約一個時辰,母親果然挎著籃子回來了。母親把薺菜從籃子里倒出來,籃子已有些年頭了,底掉了用幾根塑料帶子纏著。冬季里的薺菜透著營養不良的枯黃,并沒有春天里的碧綠。我問母親是什么原因,母親說,一冬天沒有下雨,干旱的。想想,我們在城里,還真不關注雨水,但雨水對植物的影響卻是這么的大。
昌其二哥來了,出來和他打招呼,讓我吃驚的是,他剪著時下年輕人流行的二分頭。頭型從兩邊的鬢角直直地推上去,頭頂上留著長長的頭發,然后,往兩邊分開梳,中間留下一條涇渭分明的溝,甚至能看出頭皮的白來。他瘦削的臉上滿是皺紋,上面頂著這樣一個時尚的頭型,讓人怎么看都覺得別扭。他都六十多歲的人了,一生都是剃著鄉下的茶壺蓋頭,風塵仆仆地在田野上勞作,老了,怎么趕起了時髦,讓我想不通。
晚上,去昌其二哥家吃飯,朝桌子上一瞅,滿桌的鄉親都剪著二分頭,他們真誠的笑容在這二分頭下讓我感到很陌生。坐在我對面的一個男子還戴著一副墨鏡,他很少說話,一支接著一支抽煙,二分頭的長發垂到眼鏡的框上,墨色的大眼鏡蓋住了半個臉,讓我感到不舒服。現在的農民,在城里打了幾天工,就變成“假洋鬼子”了。
幾杯酒喝下去,大家話就多了起來。昌其二哥笑呵呵地對我說,大宏興耶,這次得了你的地了,要不然,工錢就要不到了。昌其二哥善談,話還沒說出口,爽朗的笑聲就先起來了。我聽了,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并沒幫他們要過工錢啊。昌其二哥大概猜到了我的心思,望著我繼續笑著說,大宏興,你肯定不知道,我從頭說給你聽。
我們都在合肥站塘那個地方做勞務工。合肥搞工程的人,沒有不知道站塘這地方的。到站塘來的,都是干粗活的農村人。另一個勞務市場是小義烏,那是有技術的人去站的,如鋼筋工、木工、油漆工等。在站塘賣自己,早晨四點多就要到。冬天呵,一出門天黑乎乎的,北風就像小刀一樣割著你的臉,城里人都在睡覺,但我們要出門呵。站塘是兩條馬路的交叉口,沒人管理,都是自發去的。早晨到那里一看,黑壓壓的一片,人人都一手拿兩根油條或一個饅頭,一手拿著茶杯,邊吃邊站在馬路邊等老板來挑。如果有一個老板開車來了,人就轟一下子圍上來。
站塘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在這里不能說老。如果你說人家老了,人家會罵你,說,放你一嘴狗屁,我怎么老了,我看你還老了哩。因為年齡大了,就沒有人要了。一般見面了,要說人家年輕,本來是六十多的人,你也要說,哈,大哥,剛五十出頭吧。人家就會高興地說,哈,你的眼力好,一下子就猜準了。穿衣服也有講究,不能穿那種二五大衣,干干凈凈地站在那里像個城里人,那樣,老板會搖搖手說,請不起請不起。衣服要穿緊身一點,身上要臟一點,是一個干活人的樣子。平時,還要練練跳躍,這是上車時用的,要不,你一上車,拖腿不動爬半天,老板一看,你就是一個老人,也不要你,你要像一個年輕人,手按車幫,一跳就上去了。頭要剃成二分頭,這樣顯得年輕。昌其二哥說著,用手捊了一下自己的頭發。才剃二分頭時,在理發店的大鏡子里,自己都看不順眼,但沒法子,在城里掙點錢不容易,不怕你笑話,樣子都給我們玩盡了。
我恍然大悟,再看看眼前這些剪著二分頭的鄉親,不再覺得他們難看了,而是有了諷刺和幽默。
昌其二哥說,老趙六十多了,去站塘他最怕天亮,天一亮就送命了,因為,他一頭白頭發,滿臉都是皺紋,沒人要,天沒亮前,黑乎乎的,老趙戴一個笆斗帽,蓋著臉,人家看不出來。所以,天亮前一定要被帶走,要是走不了,一天就完蛋了。老趙每次上到車上,都往里面拱,在角子里縮著身子,不作聲,這樣老板不注意。有一次,他沒擠到車角里,蹲在車門口,老板注意到了,一把就把他拽下來,說,我的娘呀,你這么大年紀了,想去害我啊。老趙哭喪著臉,求情求半天,老板根本不買賬。
站塘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在這里不要說自己不行。老板問你可會開飛機,你要說會開,老板問你可會開坦克,你要說會開,沒有不會的,只要把你拉去了,這一天的工錢就有了。到了工地,真的不行,就給人家打下手,反正工地上雜活多,有活干的。有一次,老板問我會不會開攪拌車,我說會。可是攪拌車我見都沒見過,心里直打鼓。到了工地,就帶到攪拌機前一站,瞅瞅眼前這堆黑乎乎的家伙,上面有字,什么倒轉、順轉,一看就猜個八九不離十。拿人家的機子學手,還不敢學么?試著轉兩轉,真的就會了。還有一次,老板問我會不會開電梯,我說會。可是電梯什么樣子我也沒見過,到了里面一看,12345……標得清清楚楚的,上下箭頭一看就懂了,用手按按,會了。科技的東西好學,人家設計得好好的,最簡單。
在我們當中,小劍子是第一個上電視的。打工的人,工錢一般是一天一結,不存在拖欠。那天,小劍子他們在中綠廣場要不到工錢了,打電話把電視臺第一時間找來。記者扛著機子對著人照,其他人見了就嚇得跑沒影了。小劍子讀過書,膽子大、嘴會講,他對著機子說,我們掙的都是血汗錢耶,好傷心呀,你老板怎么跑了呢?說著說著就用手揉自己的眼睛。據說,電視放了后,城里一個當官的看了,當時就打了電話。工地把欠的工錢一分不少地付了,還賠了他們誤工費。現在國家好啊,都為窮人講話,要不然到哪要錢去?
大家又開始喝酒,我悄悄問昌其二哥那個戴墨鏡的人是誰。昌其二哥哈哈一笑,指著他說,你不認識他了吧?老表,把黑眼鏡取下來,讓大宏興看看。
戴墨鏡的人尷尬地笑笑,不情愿地把眼鏡從臉上取下來。我一看,這不是王老表嗎?怎么一只眼眶紅紅的,凹了進去,瞎了?!王老表年輕時,在村子里是一個帥哥,初中畢業后,因為家里窮討不起媳婦,鄰村的一個姑娘看上了,和他私奔,成了家。
王老表不好意思地搖著頭對我說,大宏興,我的這只眼瞎了,年前剛動的手術,現在還沒好清,所以要戴著眼鏡,要不然難看。說著,又把拿在手中的眼鏡戴上了。
昌其二哥嘆口氣說,大宏興,王老表這次可慘了。
王老表原來在環衛掃馬路,可他文乎文乎的,掃到一張報紙,都要坐在馬路牙上看半天,路也忘了掃,后來,環衛不要他了,他和我們一起在站塘賣自己。一次,被一個工頭帶去干活了。工頭是一個年輕人,他喜歡軍事,每天電視放軍事節目,都要棍打不動地看。他自己帶了一個隊,起了一個名字叫海豹突擊隊。王老表干活肯出力,加上有點文化,兩個人一談導彈大炮、伊朗伊拉克,滿嘴白沫,忘了干活。這個年輕工頭喜歡上了他,王老表成了海豹突擊隊隊員。成了隊員后,有一個好處,就不用天天去站塘站街了,工頭接到活,打電話直接過去干就行。我們都羨慕王老表了。可王老表命不好,那天他在工地上開卷揚機,一不小心,鋼絲繩上的一根斷絲甩到了他的眼上,一只眼瞎了。
我去醫院看他,王老表要死要活的。我勸他,你瞎了一只眼就不想活了,人家瞎了兩只眼都還活著哩。你死了容易,你一大家老小誰養活?我一罵,他想通了。
王老表住了一個月的院,工頭花了不少錢,但王老表成了殘疾人。
大家又喝了幾杯酒,可我幫他要工錢的事還沒有說,我問是咋回事,昌其二哥一聽,哈哈大笑起來,用手抹了一下嘴角說,現在,我要說你幫我要工錢的事了。
我們在一家工地干了幾天活,結工錢時,工頭找不到了。怎么辦?晚上,睡在四周看見亮光的工棚里,我愁得直撓頭。這個事,我們祖上就遇到過。解放前,有一年春天,一個外地人來我們村子賣犁頭,一個在田里干活的人,上到田埂來,把他的犁頭賒下了。賣犁頭的人問他叫什么名字,他說叫田耕玉。賣犁頭的人不知道這是個假名字,就記下了。午季結束了,一般人家賣了莊稼就有了錢,賣犁頭的人到村子里來找田耕玉討錢。問了全村的人,都說沒有這個人。賣犁頭的人說,沒這個人,我就找這個田埂要。他拿了一把鍬,到當時田耕玉賒他犁頭的田埂上挖了起來。田埂被挖了一大截,事情搞大了,這個人就自己出來,把錢給了。田耕玉是誰,老輩的人都知道,我就不說了。
過去我也聽說過工頭跑了、工錢打水漂的事,沒想到也給我們碰到了。我們幾個人在一起商量怎么辦。大家都沒主意,我就想到田耕玉的事,一拍屁股說,誰也不要找,就找這幢樓要錢,這樓就是那條田埂,它會有主的。他們不相信,我說,小劍子,我在前面唱黑臉,你在后面唱紅臉,不要搞露了。第二天,我們找到項目部。項目部的人不理我們,說,你有條子嗎?我把條子拿給他看。他看了后,又說,這個包工頭子工地多了,怎么證明你們就在我們這兒干的呢?這下可把我難到了,我想了想說,我可以找你們食堂炊事員,我們這幾天可是在他這兒吃飯的,如果沒有在他這兒吃飯,說明我沒在你家工地干活。項目部的人不作聲了。我看他心虛了,要再燒把火,不知道為什么就想到了你。我說,我們村子不出人,就出了一個大記者,你要是不給錢,我打一個電話,他就來了。其實,大宏興耶,你的手機我都沒有。但我知道,現在,這些老板們最怕記者,記者只要一曝光,他明年接工程的資格就沒了。
對方一聽說能找到記者,就趕緊打電話找工頭子,在電話里罵他。原來,這個工頭好賭錢,賭輸了十幾萬,把我們的錢結去還債了。好家伙,你對賭鬼守信用,對我們就欺騙了。項目部的人雖然找,但那工頭不見人。項目部的人手一攤說,你們看到了,我也幫你們找了,他不來怎么辦?我看事情要黃了,內心很急,生氣地說,你們是想上報紙還是想上電視,我打個電話,我們家記者半個小時就到,如果不到,這個工錢我就不要了。這話一出口,我自己也嚇了一跳,我心中沒底啊。對方聽我敢拿工錢來打這個賭,更信了,趕忙說,他不給,我們給。小劍子見機就對我說,二爺,你就不要添亂子了,人家不是在給我們想法子么。項目部的人也跟著喊,二爺你消消氣。天晚了,見我們還沒吃晚飯,就說,二爺,我們先去吃晚飯。我記著,從工地到小飯店,一路上喊了我十幾聲二爺,給了我九支香煙。其實我不吸煙,但他給我煙,我就接了,晚上給王老表吸。王老表是個煙鬼,快活得很。
到了小飯店,項目部的人說,你們點個菜吧,看是吃羊肉火鍋還是吃牛肉火鍋。我說,我們干活的,需要力氣,不吃羊肉火鍋,就吃牛肉火鍋。
火鍋吃完了,錢送來了,我們就回去了。我們敢在人家面前吹,就是因為有你,我們心里不怕,你到場不到場,都敢。
我聽了,心里咯噔了一下。其實,我不是記者,我是在省文聯工作,是個作家,是沒有記者證的。故鄉的人,不知道作家是干啥的,反正能發表文章的都叫記者,我這些年回家,他們都是這樣叫的。現在,我不好給他們把真相說了,我要是說我不是記者,他們再遇到討工錢的時候,就沒有底氣了,腰桿就不硬了。我對昌其二哥說,下次遇到這種情況,你們只要打個電話,我就過來。
話漸漸地說得多了,我和鄉親們在桌子上推杯換盞,酒越喝越多,滿桌的菜卻少有人動筷子。我有了醉意,滿眼晃動的都是剃著二分頭的鄉親們。
到了年初三,我要回城里了,有幾個鄰居過來打聽,他們想跟我的車子。母親私下里不想讓我帶,怕他們暈車把我的車子弄臟了,我沒有同意。
車子上路了,穿過那片楊樹林就上省道了,家鄉在身后越來越遠。偶爾從車內后視鏡里看到后排坐著的三個剃著二分頭的鄉親,他們的面孔木木著,他們在奔赴城市,城市在給予他們,但也在損害著他們。
討 賬
別的不說,單說討賬。
我家生意做得不大,賒賬的人倒不少,沒辦法。
慣了,俺到人家一站,人家就明白十有八九是來討賬的,他差俺錢,心里亮堂著。
人家越知道俺是來討賬的,俺越不好意思直說,那樣,顯得多薄氣。
大姐哎,今年收成不錯吧,地里的活干得咋樣啦?俺滿不在乎的樣子,先摸摸人家的底細,熱火熱火感情,這很重要。
熱火不能忘了討賬。時機成熟,就要見機行事說,這次又從外面進了一批貨,比上次的貨好,價格還便宜,要的人很多。這是給人家送一個想頭。人家大多會問,還有么?孬好給俺留一點。俺滿口答應下來,行。誰家不給也要給你家留點,這么多年的老伙計了。只是最近手頭緊,要盡快銷掉,再去進貨。人家會馬上反應說:是哎,俺家上回拿你的貨還沒給錢哩,現在就給你。你來正好,省得俺送去了。錢要到了,雙方臉上都有光,還把貨推銷了出去。如果人家確實困難,俺說,先給一半吧,幫幫俺的忙,下次手頭寬時再給。如果你要貨,盡管去俺家搞。人家聽后心里熱乎乎的,晚上睡覺都會摳著肚臍想法抓錢還你。因此,賒賬的人,是一個角子也少不了的。
做生意最怕賒賬,在農村不賒賬不行,熟人熟地的,相互敘敘都沾親帶故的,不像城里人八輩子不沾邊。有的人,只會做生意不會討賬,把生意做砸了,還落了個臭名聲,不值得。
村里老五賒賬很多,他整天在外跑,讓老婆去要賬。女人風風火火的,又不會說話,一到人家就手拿著賬本扯著嗓子喊怨地說,你家差俺的錢要給了,少一個子也不行。欠賬的人,還愛面子,怕壞了名聲。你這樣一喊,人家一聽就不入耳,給錢也不自在。有一次,她去一戶人家討賬,人家故意為難她說沒錢。三言兩語就搞翻了。她往人家地上一躺,又滾又罵,人家沒有辦法,喊幾個婦女把她從屋里架出去,又把錢給了她,丑得能拿褲頭套臉。
有時討賬,人家明知道還不上錢了,俺大老遠跑來,他又不好意思直說沒有,就陪俺啦呱到中午,死活留俺吃飯。燒幾個熟菜,打幾斤水酒,伢大老小一齊給俺敬酒,鍋不熱臉熱,客氣得不得了。睡半天,一覺醒來,吐一地,人還笑著問長問短。要錢的事不好再張口了,錢沒要到,心里還熱乎乎的。這樣的人家是聰明的,下次還會賒給他的。
討賬還得講良心。有的人,做生意時臉皮厚,討賬時心腸黑。俺有一個做生意的朋友,他有次要賬,人家也確實著急,滿戶借,借不到,恨不得給他磕頭,說,明年莊稼收上來,一定還清。他還不行,把人家幾只老母雞捉回來了。在鄉下,老母雞就是小銀行啊。你走了,人家還怎么過日子。俺知道后,對他說,你這樣討賬太惡了,有點像舊社會的大惡霸。鄉里鄉鄰的,抬頭不見低頭見,只要人家不賴你的賬,就要給人家一個松手的機會。最后,在俺的擔保下,他又把幾只老母雞給送了回去。
家門口的人賒賬,一般都能摸清底細,不怕。有時遠地見面熟的人來賒賬,不大了解,會碰到賴賬的人。這樣的人不能硬要,得罪了他更耍賴的,就得想點法子。年關討賬,俺碰到一位賴賬的,叫二狗。后來別人跟俺講,他是附近有名的賴子,你的賬要不到了。怎搞?俺想了一個點子,找來伙伴一道去,讓他幫俺說話。到他家后,俺向二狗介紹,你差的錢,俺還是借他的,給你頂賬這么多天了,現在他緊盯著俺屁股要,年都沒法子過,你我孬好得想個法子。伙伴叼著煙,刀條臉陰沉著,半晌冷言冷語地說,俺也沒法子,老媽病重,屎尿都在床上,眼看年關都過不去了,俺起碼要給她弄身壽衣。你家不也上有老下有小的嗎?伙伴這話是咒人的,俺吃了一驚,怕把事情弄翻了,沒想到二狗卻被鎮住了。他私下里和老婆商量,磨蹭著,從箱子里拿出錢還給了俺。
農村人最講迷信,認為在臘月年關里咒人是最靈驗的,伙伴敢咒自己的老媽也太難為他了,可他老媽早幾年前就去世了。








